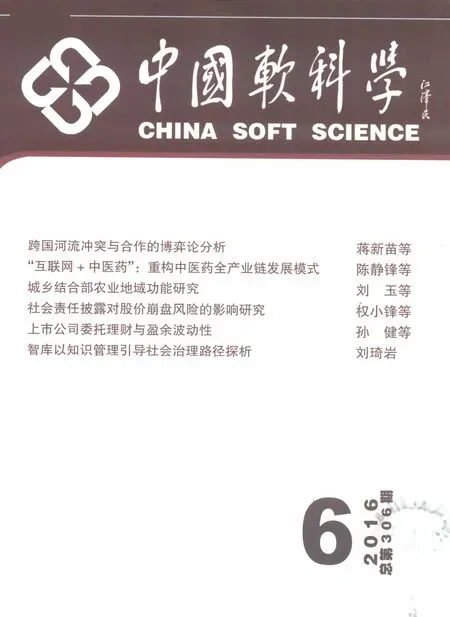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再就業”
張洪潮,王 丹
(太原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600)
?
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再就業”
張洪潮,王丹
(太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西晉中030600)
摘要:解決失地農村勞動力“再就業”是中國新型城鎮化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面臨的突出現實問題。本文依據1985—2012年的面板數據,基于修正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剖析新型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演化軌跡及三者的互動規律,進而從新型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兩方面,提出了應大力發展與區域相適配的第三產業、應著力推進地方特色明顯、產業基礎扎實、城鎮規模適中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農村勞動力轉移;VAR模型
一、引言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使得“土地城鎮化”日益加速,其引致的農民失地、農民失業、“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等問題不斷累積發酵,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新農村建設、可持續發展及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因素。黨的“十八大”和中央經濟會議多次將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點而提上日程,充分把握現階段我國經濟“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戰略機遇期,以新型城鎮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為抓手,促進農村勞動力合理轉移,破解農村勞動力失業與再就業困局,實現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合理轉移的協調科學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來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城鎮化過程中的重要伴生現象,產業結構升級和城鎮化發展都是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誘因,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國外關于城鎮化、產業結構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配第—克拉克定理[1](1940)最先提出產業結構變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西蒙·庫茲涅茨(1966)[2]深入的研究了三次產業產值比重變動帶動勞動力比重變動規律。錢納里等(1986)[3]研究了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協調發展問題。保羅·克魯格曼(1998)[4]分別從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生產要素的空間聚集等角度闡述了就業、產業和城鎮化三者之間的關系。邁克爾等[5](2000)從社會學的細分市場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亞歷山德羅等(2009)[6]研究了城鎮化效應與農村勞動力市場之間的聯系。國內關于城鎮化、產業結構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景普秋,張向陽(2005)[7]從城鎮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互動關系角度進行研究,認為城鎮化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動因;薄艷萍、吳永球(2005)[8],葉琪(2006)[9],程名望、史清華(2007)[10]等學者從產業結構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互動關系角度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認為產業結構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存在雙向互動關系;馮尚春(2005)[11],肖功為、賀翀(2013)[12]從城鎮化與產業結構互動角度進行研究,認為中國城鎮化道路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互動效應,但二者之間還存在一定偏差。何景熙,何懿(2013)[13]對中國產業結構變動、就業結構變動和人口城鎮化趨勢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實證研究;曾湘泉等(2013)[14]對中國各區域在不同城鎮化模式、城鎮化水平和產業結構分布條件下的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效率進行了研究。
綜上所述,既往對城鎮化、產業結構以及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多偏向于定性研究,并且多數從城鎮化或產業結構單因素入手,對于三者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本文從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兩個方面,結合中國城鎮化和產業化的實際發展進程,以1978—2012年統計數據為基礎,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對城鎮化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探尋兩者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動態演變關系,并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互動機理
進入“十二五”以來,基于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發展,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成為我國穩定經濟增長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美國經濟學家蘭帕德、地理學家貝里都論證了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國內眾多專家學者結合我國經濟實踐,也證明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及農村勞動力轉移等之間存在相互支撐和相互約束作用。
依據世界發達工業體的經濟發展規律,產業結構升級和城鎮化發展都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誘因。本研究發現,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存在一種持續互動演變規律,三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和相互制約。三者之間的互動演變機理如圖1。
首先,城鎮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城鎮化發展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受物質利益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和非物質利益因素(如生活條件、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水平、基礎設施建設等)兩個因素影響。從中國現實情況看,由于城鄉之間在以上兩方面均存在較大差距,導致農民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而向城鎮發生遷移。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會帶動人口、資本、信息等資源要素向城鎮聚集,資源聚集為城鎮化提供了基礎與保障,促進城鎮化演進升級。
其次,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存在互動關系。隨著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迅速發展的現代農業和非農產業都會產生大量就業崗位,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產生巨大的“拉力”作用;再者,由于技術進步帶動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使得農村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又會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產生巨大的“推力”作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所產生的“推拉力”共同作用,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另外,農村勞動力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在非農產業的投入增加會促進非農產業發展,進而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圖1 互動演變機理
最后,城鎮化與產業結構之間持續互動共同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城鎮化不是“房地產化”,不是簡單的將農民從農村搬遷到城市的“住房城鎮化”,城鎮化必須以產業結構升級為前提,使進城農民得到合理的就業安置,擁有穩定的生活收入,保障農民“搬得出、住的住”,推動“事業城鎮化”與“住房城鎮化”有機結合,以產業升級帶動人口向城鎮聚集,實現城鎮化健康發展。同時,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了生產要素流動聚集、技術水平提高和創新能力提升,加快了產業聚集與集群的形成與發展,為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特別是城鎮化會推動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和協同集聚,推動產業升級[15],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三、實證分析
(一)指標設置及數據來源
1.指標設置
城鎮化率指標。該指標通常用市人口和鎮駐地聚集區人口占地區總人口百分比來反映。城鎮化率反映了人口向城市的聚集過程和聚集程度。
產業結構升級指標。產業結構,是指經濟系統中產業構成以及各產業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比重關系。本文以第二、三產業產值比重,即第二、三產業產值與總產值的比值,作為衡量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程度及合理性的指標。
農村勞動力轉移指標。農村勞動力轉移包括產業轉移和空間轉移兩種形式,但無論是哪種形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其最終結果表現為勞動力由傳統的農業生產部門向現代化的非農產業生產部門轉移。由于在中國非農產業部門中第三產業勞動力吸納效率較高,本文以第三產業勞動力比重,即第三產業勞動力數量與總勞動力數量的比值,作為衡量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指標。
2.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城鎮化率、產業結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指標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3》。由于對時間序列取對數不會影響序列本身的平穩性和系列間的協整關系,而且還能消除異方差影響,所以對所有整理的數據取自然對數。
(二)平穩性檢驗及向量自回歸(VAR)建模
傳統的經濟計量回歸模型在描述變量關系時需要事先確定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但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的識別過程是十分困難的,并且有些內生變量可以出現在方程兩端,這使得推斷變得更加復雜。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便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種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其作為處理多個相關經濟指標的分析與預測的有效模型之一,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工作者的重視,并被廣泛應用于經濟研究工作中。
為了避免非平穩序列出現“偽回歸”現象,我們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數據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由表1檢驗結果可知,LLAB、LSTR、LURB三個序列在90%的置信度下均為平穩序列,故可建立VAR模型。
VAR模型建立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模型滯后階數p的確定,本文運用赤池信息準則(AIC)、施瓦茨(SC)準則等方法確定最佳滯后階數,根據表2 確定最佳滯后階數為4,因而建立VAR(4)模型。

表1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表中(c,t,k)中的c、t、k分別代表單位根檢驗方程中的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

表2 VAR滯后期選擇標準
注:*表明該準則下選擇的滯后期。
建立VAR(4)模型,三個方程的擬合優度分別為0.997、0.991和0.999,因而方程的整體擬合度較高。同時,VAR(4)模型是否穩定取決于該方程的特征根值。圖2為VAR(4)模型的穩定性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全部特征根包含在單位圓內,因而該模型穩定性較強,可信度較高,在此模型基礎上得到的脈沖響應函數結果是可靠的。
在前文基礎上,對LLAB、LSTR和LURB三個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明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由表3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知,城鎮化、產業結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農村勞動力轉移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產業結構是城鎮化的格蘭杰原因。

表3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圖2 VAR(4)模型穩定性檢驗

圖3 脈沖響應函數
(三)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本文采用脈沖響應函數,進一步分析當對隨機誤差項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時,內生變量農村勞動力轉移量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受的影響。
由圖3可知,農村勞動力轉移量受到自身沖擊影響最大,當農村勞動力轉移量受到自身一個標準差沖擊時,農村勞動力轉移量立刻產生一個正向響應,大小為2%,并呈逐漸上升趨勢,在第2期達到最大值3.5%,之后呈逐期遞減,在第8期以后趨于穩定;當農村勞動力轉移量受到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標準差沖擊時,農村勞動力量轉移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在第4期達到最大值2.5%,之后呈逐期遞減,在第9期以后趨于穩定,這表明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對農村勞動力轉移驅動影響具有長期性,但這種驅動影響強度較低;當農村勞動力轉移量受到城鎮化水平的一個標準差沖擊時,農村勞動力轉移量立即產生一個1%的正向響應,并呈逐漸上升趨勢,在第3期達到最大值1.8%,之后呈逐期遞減,在第8期以后趨近于0,這表明城鎮化進程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驅動影響短期作用明顯,但長期驅動力不足,且驅動影響強度較低。
(四)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用于分析VAR模型中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并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表4的方差分解結果給出了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升級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貢獻度。

表4 方差分解分析結果
由表4可知,勞動力轉移對自身的影響最大,第一期為100%,雖然隨著滯后期增大其貢獻率在不斷減小,但在滯后10期時仍維持在66.85%的水平;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轉移的貢獻率呈逐期增加的趨勢,且增長勢頭強勁,由第一期的0增加到第10期的31.82%;城鎮化水平對勞動力轉移的貢獻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綜上所述,產業結構升級是勞動力轉移的最主要推動力。
四、政策建議
理論與實證研究表明: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是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種主要驅動力,其中產業結構升級是主要推動力。研究進一步顯示,上述兩種模式對農村勞動力轉移驅動特征存在差異: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效應明顯,但強度偏低;城鎮化的短期效應突出,但長期驅動乏力且強度偏低。
從“標本兼治”的戰略目標出發,聚焦當前因城鎮化而加劇的失地農民“再就業”這一突出問題,科學調配“產業結構調整”和“新型城鎮化”兩個戰略抓手,本文從政府視角,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改革嘗試“股代補”農村土地征用機制
我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土地征用多采用“一刀切”式補償機制,即向被征地農民一次性發放生活補助,其弊端在于:一次性補償資金只能解決農民城鎮化的短期生活消費,但長期來看,失去土地且未能找到穩定工作的農民就會失去生活的基本保障。土地是農民生活的“命根子”,政府應進一步創新農民土地征用模式,由“一刀切”向 “持續用”轉變,以農民土地入股代替一次性補償,嘗試“股代補”式改革,使“城鎮化農民”能夠共享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土地增值效應,獲取“農”轉“城”的穩定保障。
(二)引導構建多元化農民教育投資渠道
各級政府是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中的主體力量。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城鎮化區域的相關企業,不僅是農民教育培訓的受益主體,還應成為投入主體、實施主體和需求主體,政府應合理運用立法以及政策制定權,引導企業加大教育培訓投入,注重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工作,這既是企業發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同時,我們應充分重視培育社會力量,社會力量包括非盈利和盈利型組織,是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專業技術等教育培訓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政府應通過減免稅收、財政補貼等政策支持,為其投入農民教育事業創造環境。通過創新驅動,構建包括政府、相關企業和社會力量等多元化農民教育培訓投資渠道。
(三)著力加強農民專業定性培訓體系
農村勞動力專業技能水平高低,不僅關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質量,而且決定著新農民的就業及生活。一是地方政府應牽頭組建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等多方面多層級的專業技能培訓師資體系,形成適應不同需求的農村勞動力專業技術培訓師資隊伍;二是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村勞動力培訓規劃機制,基于不同地區經濟特色、產業優勢、勞動市場等具體情況,設定勞動培訓課程,并不斷動態調整勞動培訓計劃;三是構建定向培訓機制,通過與勞動用工單位的常態化規范化合作,根據當地企業用工需求,開展農村勞動力和在職人員的專業技術人才定向培訓。
(四)鼓勵發展現代生產型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具有資本投入少、技術門檻低、發展速度快、就業容量大和發展潛力足等特點,是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現實渠道。從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的現實背景充分,各級政府在制定第三產業發展規劃和政策制度時,既要關注物流倉儲、批發零售、餐飲住宿等傳統第三產業,進一步挖掘提高其勞動力吸納效率。另外還要著重開拓電子信息、技術孵化、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第三產業,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帶動“新農民”就業增長。
(五)倡導發展城鎮依托型產業化模式
注重與城鎮特色、區域特色、資源特色相結合,規劃產業結構、產業發展規模等。產業發展不是無源之水,需要良好的政治、經濟、科技、社會等外部環境的堅實支撐,需要人力、資本、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大量投入。長期以來,中國產業發展與城鎮化之間發展不協調,不僅制約二者各自發展水平,同時造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障礙。促進產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必須堅持以城鎮化為依托,結合本地區城鎮化規模、城鎮化水平與城鎮化特點開發具有區域特色的產業發展新模式,最終實現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發展間的良性互動。
(六)推動形成產業導向型城鎮化建設
結合產業發展,規劃城鎮功能,界定城鎮容量,完善建設布局;優化產業發展環境,提供完備的公共基礎條件,促進產業與城鎮化融合發展。以產業發展為依托,通過促進城鎮產業集群發展,提高城鎮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的承載能力,帶動城鎮化進程,同時注重不同規模城鎮化間的協調發展以及城鎮對周邊農村的帶動作用,引導農村勞動力轉移向城鎮非農產業部門長期合理、穩定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協同演進。
參考文獻:
[1]配第經典著作選集[M].陳冬野,馬清槐,周錦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KUZNETS S.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structure and spread[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3]CHENERY H,ROBINSON S,SYRQUIN M.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KRUGMAN P.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1998(2):122-145.
[5]MICHAEL C Seeborg,JIN Zhenhu,ZHU Yiping.The new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causes and implications[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0(1):39-56.
[6]ALESSANDRO Alasia,FONS Weersink,RAY D Bollman,et al.Off-farm labour decision of canadian farm operators:urbanization effects and rural labour market linkages[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9(1):12-24.
[7]景普秋,張向陽.中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計量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5(1):1- 4.
[8]薄艷萍,吳永球.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轉移[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5(9):20-30.
[9]葉琪.論農村勞動力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互動[J].財經科學,2006(3):80- 85.
[10]程名望,史清華.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農村勞動力轉移[J].經濟學家,2007(5):49-54.
[11]馮尚春.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與產業結構升級[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5):130-134.
[12]肖功為,賀翀.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致的城鎮化效應研究:一個省級面板分位數模型的實證檢驗[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3(5):90-94.
[13]何景熙,何懿.產業—就業結構變動與中國城鎮化發展趨勢[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6):103-110.
[14]曾湘泉,陳力聞,楊玉梅.城鎮化、產業結構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吸納效率[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4):36- 46.
[15]FARHANA K M,RAHMAN S A,RAHMAN M.Factors of migration in urban bangladesh:an empirical study of poor migrants in Rajshahi City[J].Bangladesh E-Journal of Sociology,2012(1):63- 86.
(本文責編:海洋)
收稿日期:2016-02-05修回日期:2016-06-01
作者簡介:張洪潮(1967-),男,河北肅寧人,太原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區域經濟、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
中圖分類號:241.2;F2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6)06-0136-07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Rural Labor “Reemployment”
ZHANG Hong-chao,WANG Da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ai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Jinzhong030600,China)
Abstract:To solve the “reemployment” of landless rural labor is a prominent practical problem faced by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Based on panel data of year 1985 to 2012 and the corrected VAR model,this paper analyzes evolution track and interactive law among China’s 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and rural labor transfer,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proposes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third industry which adapt to the region and promote local-featured,industrial-based and moderate-scaled new-typ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rural labor transfer;VA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