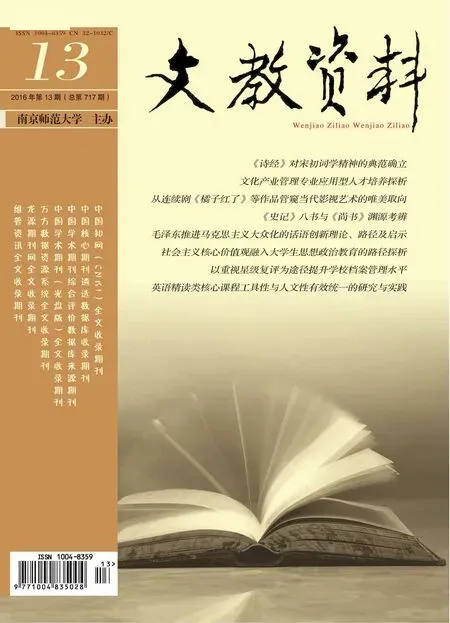《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曲折發展》專題教學中易犯的錯誤
徐長友
(揚州市第一中學,江蘇 揚州 225000)
?
《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曲折發展》專題教學中易犯的錯誤
徐長友
(揚州市第一中學,江蘇 揚州225000)
摘要:本專題教學時有些問題容易混淆出錯,如對一些重要概念的解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快時期和最高峰在什么時期、一戰后民族資本主義是否蕭條、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有沒有民族資本主義。平時聽課和教輔資料中,經常碰到分歧、錯誤,所以有必要對這些易混點進行整理。
關鍵詞:中國資本主義歷史教學易混點
《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曲折發展》這一專題是必修二中的重要章節,是整個高中歷史教學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教學中學生經常對一些概念混淆,對一些史實認識錯誤,甚至連一線教師對本專題的個別問題也認識模糊。教材編寫時,有些知識點未能說清楚,或仍然采用史學界陳舊觀點。通過查閱資料,仔細分析,現將本專題容易混淆的知識點做一整理。
一、對一些重要概念的解釋
本專題中,“民族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萌芽”、“民族工業”、“近代工業”等概念眾多,區別不清,容易張冠李戴。對這些概念,教材并沒有過多解釋,有必要加以準確界定。“(中國資本主義)包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也包括外國在中國的資本……官僚資本……即從清政府的官辦、官督商辦企業到國民黨國家壟斷資本這一資本主義體系;而它的實質……就是在這些不同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繼承明清以來資本主義萌芽而來的民間企業,即民族資本義”[1]。《2012年江蘇省普通高中學業水平測試(必修科目)說明》與2011年的說明相比,有一變動,即“認識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刪除了“民族”二字,教學時應能洞察這一變化,也就是說這里不光要讓學生掌握民族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還包括外國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產生背景。
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經濟現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生過程,而不是指一種內含的因素或發展趨勢。萌芽狀態是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質逐漸增長,舊質逐漸消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經濟實體就不能不具有過渡性和兩重性,也就是說,在考察萌芽的存在的時候,不能要求它純粹的資本主義性質,必然包含或多或少的封建性東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備資本主義的全部機能,而只是主要機能。
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與鴉片戰爭后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關系是什么?林增平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一文以為,中國封建社會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過于微弱,鴉片戰爭后因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絕少,因之“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就缺乏原來的手工工場作為發展的基礎。中國新興的近代企業,絕大部分是從無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業成套地移植過來的”。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同樣強調,中國近代工業是鴉片戰爭后“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創辦起來的”。
吳承明對此持異議。他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一文中詳細考察了鴉片戰爭前后手工業變化情況后指出: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大機器工業這一過程,同樣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形成一個工場手工業時期而已。鴉片戰爭前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十幾個手工業行業中,只有踹布和刨煙業兩個行業在鴉片戰爭后被外國商品替代了,其余都維持下來,并有九個向機器工業過渡。因之他認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是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得以產生的途徑之一。所謂鴉片戰爭后西方工業品對傳統手工業的破壞被夸大了,“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并未中斷”。
汪敬虞選取一般論者公認最有可能由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的福建茶園、云南銅礦和四川鹽井三個行業進行了具體考察,則提出對資本主義萌芽的估計應當注意避免兩種傾向。他在 《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中說:“割斷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聯系,認為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出現,這是一種極端。反之,不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歷史條件,強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聯系,把它看成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這是另一個極端。”
近代工業是一個較大的概念,它不是特指中國的,而是指近代使用機器從事生產的企業,包括外國資本主義企業、官僚資本主義企業和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等。而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含義應該是一致的。
二、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快時期和最高峰在什么時期
“19世紀下半葉,中國近代工業化開始緩慢起步……1912年至1920年中國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3.4%,1923年至1936年為8.7%”[3]。可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最快時期是在民國初期。
發展最高峰在什么時期,從以下材料可以得出結論。
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設立了62家商辦企業,資本總額達1240多萬元。這遠遠超過了中日戰爭前20多年民族資本的總和……從1912年到1919年的8年間,中國民族資本建成的廠礦有470多個,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至少有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了過去50年投資的總和[3]。

1920年和1936年中國產業資本投入[4]
從這兩則材料不難看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1927-1936年)在民國初期短暫春天的基礎上繼續得以較快發展,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使得民族資本主義受到沉重打擊。所以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時期是在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最高點則在1936年。
三、一戰后民族資本主義是否蕭條史學界新觀點
傳統觀點認為一戰期間,民族資本主義出現了“短暫的春天”,一戰結束了,由于帝國主義卷土重來,民族工業又迅速蕭條。但史學界也有新觀點,如薛偉強、高景龍在《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學術研究與中學歷史教學》一文中認為:一戰期間民族工業進入“春天”不假,但絕不短暫。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至少從甲午戰爭后已經明顯,民國肇始,趨勢未變,一戰期間,風頭更健。一戰后,中國民族工業并未“立即萎縮和蕭條”。據劉佛丁先生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私人資本投資的研究,1919~1922年期中國私人資本的工礦交通業投資年增長率為13.94%,是這一時期中增長最快的階段。陳爭平的研究認為,從棉紡織、機制面粉、機器繅絲等民族工業主要行業的資本增長、生產能力增長、年產量、年利潤率,及整個工業資本年均增長率及工農業總產值等指標的比較研究來看,1920~1936年間并非如有些學者所說是 “不斷陷于危機和蕭條”。而是可以稱之為中國民族工業繼“黃金時代”之后的“白銀時代”。王玉茹《中國近代的經濟增長和中長周期波動》一文的計量研究證實,由物價變動指標、對外貿易指標及反映生產的三大類指標來看,所有數據指標都顯示——一戰結束后的1918年至1936年,中國的經濟不但沒有銳減,反而呈明顯的增長趨勢。從總體上看,1914~1936年,中國經濟確有較大發展。國民收入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45%,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1%,年均增長速度達到7%。這些結論與以往多位專家的研究結果也是一致的。因此。所謂“一戰期間短暫的春天”中的“短暫”二字盡可去矣。所謂“民國時期(1912—1949年)民族工業發展的曲折歷程”中的“曲折”二字亦盡可去矣。在1937年之前的民國時代,民族工業一直都是 “春意盎然”,只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才遭受了唯一的一次重創。
四、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有沒有民族資本主義
民族資本主義在“三大改造”中,國家采取和平贖買,公私合營,被改造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遂走向消亡。其后的二十多年間,民族資本主義銷聲匿跡。改革開放后,中國步入嶄新發展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黨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需要其他經濟形式作為必要的補充,民族資本主義應時而生,蔚然成風。尤其是“十五大”后,掀起“改制”熱潮,民族資本主義蓬勃發展,蒸蒸日上,成為我國經濟騰飛的強勁翅翼。
以上幾點是教學中容易模糊,甚至出錯的地方。由于我才疏學淺,如有不當之處,望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5.
[2]摘編自劉佛丁.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白壽彝.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整理自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中華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