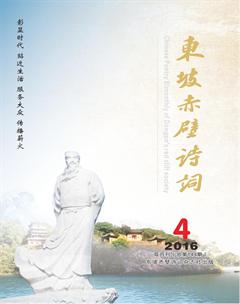當代新田園詩的尷尬
熊文祥
讀罷黃春元先生的《新田園雜詠六十首》,很為他的的寫作才情所折服。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過:“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黃先生的詩,不掉書袋,不說枯燥道理,以其才、其趣、其對生活的觀察,生動地描摹出了當代農村的一幅現狀生活圖。
詩題《新田園雜詠六十首》,顯然有仿效宋代詩人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之意,篇數趨同,手法亦趨同,都是捕捉農村生活轉瞬即逝的鏡頭,用詩的思維將其記錄下來,定格成藝術。與范成大相比,雖然有高下之分,但稱之為“詩”則應沒有異議。
黃春元先生《新田園雜詠六十首》組詩的價值,體現在一是描寫當代農村生活的寬泛性,二是其中不少篇目確有詩味。說生活的寬泛,是組詩觸及到了當代農村生活的諸多方面,雖然不是全部。如標志農民生活富裕的新建樓房,如推廣新興種植技術的大棚蔬菜,如改變傳統燒柴做飯方式的沼氣,如體現公民權的民主選舉村官,如體現時興營銷觀念的網上銷售和網上購物,以及鄉村婚嫁、喜娶洋妞、回鄉創業、倒發壓歲錢財的兒女、日晚歸來跳“蹦嚓嚓”的大媽,等等,目之所及,五花八門,生動有趣,生活面之廣,只怕宋代的范成大也自嘆弗如。不過做到這點并不難,只要關注農村生活,或是關注一下時下的報紙或網絡,熱心于寫作的人都能做到。難就難在我要說的第二點,你得把這些東西寫成詩。這就不只是憑借素材豐富,而是考驗你的藝術感覺和詩歌思維了。黃春元先生有才情,基本做到了,這就不得不佩服。
六十首雜詠中,其中不少篇章是寫得有詩味的。如雜詠之一:“修路填平臭水溝,挨家挨戶起新樓。舊時王謝堂前燕,錯認朱門直犯愁。”借歸燕錯認“朱門”而“犯愁”的藝術手法來表現農民生活的富裕,這種不直說而“曲說”,就是藝術手法。此詩的后兩句從劉禹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演化而來,雖然少了幾分滄桑,但也道出了當代農村的真實。如雜詠之三:“留住春天趕走冬,垂垂草莓醉顏紅。推醒瓜果搖籃夢,一望無邊塑料棚。”采用擬人手法,將草莓比作嬰兒,以嬰兒夢醒象征草莓成熟,而推醒嬰兒美夢的則是大棚虛擬的春天,層層轉折,愈轉愈深,耐人尋味。如雜詠之二十五:“科技人員到地頭,稻花香里說豐收。田間管理編程序,氣煞當年老鐵牛。”詩寫科技種田,以“氣煞當年老鐵牛”來反襯科技的力量和受人歡迎的程度,折射出農民思想觀念的轉變,很有當代氣息。如雜詠之二十八:“豐乳肥臀老大媽,稻場日晚蹦叉叉。搭肩把臂團團轉,割谷歸來舞伴夸。”寫農村大媽豐富的精神生活,神情畢肖,諧趣十足,讀之令人捧腹。如雜詠之三十一:“爆竹喧囂炸破天,全家團坐過新年。天涯歸客糊涂也,倒發爺娘壓歲錢。”寫外出務工青年的富足和孝心,不直說,偏以“倒發爺娘壓歲錢”出之,可謂別出心機。如雜詠之四十:“夫妻結伴走天涯,數載奔波未返家。小女天天看電視,錯將主播當親媽。”此詩表面看是個小喜劇,實則是悲劇,隱含著留守兒童缺失親情的社會問題,可謂小詩不小。詩人采用的是“以樂景寫哀,倍增其哀”的手法,詩作亦因此而倍增感染力。如雜詠之四十一:“青磚紅瓦二層樓,飽食三餐亦不愁。偏是冷清揮不去,相親只有老黃牛。”詩寫農村空巢老人的孤獨感,生活富足帶來的對親情的漠視,很值得人們深思。以“老黃牛”作為老人的陪伴,很有農村生活的特色,亦與老人身份相符,如果放在城市老人身上,那就不對了。如雜詠之四十九:“明三暗六屋誰稀,時下新樓九級梯。家什全都更換過,打鳴還賴老公雞。”詩寫變與不變的矛盾,住房變了,家俱變了,都現代化了,唯有聽公雞打鳴的幾千年的習俗難以改變。詩于萬變中寫出一點不變,愈見出主人公固執得十分可愛。這就叫典型性,寫詩就得要善于捕捉這些帶典型性的東西,這樣詩才生動,才愈見生命力。
從以上所舉詩作可以看出,詩人在謳歌當代農村變化的同時,并沒有回避存在的諸如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問題,由此亦可見出,詩人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
下面,我要說的問題是新田園詩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當然,這是針對整個田園詩創作而言,并非特指某個作者。它代表著新田園詩的一種創作傾向,也可以說是時下新田園詩普遍存在的問題。
其一是題材、手法雷同,寫農村富裕必是樓房、電腦、手機、沼氣、摩托,寫農民豐富的精神生活必是唱歌演戲跳舞,等等。不是說這些東西不能寫,而是怎樣寫出新意,寫出不同詩人的不同感受。在這里,內心的感受、體驗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個人獨特的感受,寫出的東西必然大同小異,雖然也是詩,但說不上是好詩。與其強寫,寧可不寫。手法更是千篇一律的七言絕句,連七律都少見,更別說排律、古風或樂府。當代新田園詩之所以寫不出有影響、震憾心靈的作品,除題材千篇一律外,手法、形式也是制約它發展的原因。
其二是缺少感情投入,或者說是感情投入不夠。田園詩由陶淵明首創,然后繼乏人。陶淵明生于晉、宋官場黑暗的戰亂時期,為了潔身自好,歸隱田園,并構筑了一個烏托式的桃花源,以與昏濁的外部世界抗衡。更重要的是,他將自己整個靈與肉溶進了田園,全部情感投入了鄉土,因此創作出了一批獨具風格的田園詩。至唐代的王、孟,雖然繼承了陶詩的傳統也寫田園詩,但重點在山水而不在田園,史稱山水田園詩。他們的詩作既可視作對陶淵明田園詩的發展,也視作對陶詩傳統的背離。至南宋范成大,雖然也想恢復繼承陶詩傳統,但他終究是士大夫,不能將自己整個身心、情感投入田園,所以,他的田園詩作與陶詩比,就顯得浮光掠影,缺少陶詩那種出自心靈的對田園的歌吟。至于當代的新田園詩,基本上是沿續了范成大的創作思路和藝術表現手法,少有突破,更有甚者,以士大夫的情懷把玩田園。相當一部分作者對農村生活并不熟悉,素材大多來自報刊或網絡,憑寫作經驗敷衍成篇。這種不是向生活要素材而是向報紙網絡討素材的作品,當然談不上什么感情投入。如雜詠組詩中的“二娃單騎別雙溝,千里追尋小莫愁。夢醒邯鄲成好事,帶回一個俏洋妞”,就未必是作者親眼所見,素材很可能來自報紙、網絡。還有一種情況,作者僅憑經驗記憶,想當然地描寫當代田園生活。如農村自從推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以來,早已改變了傳統勞作模式,插秧改為撒播,收割改用機械,可我們的新田園詩,仍在不厭其煩地描寫早已過時的人工勞作的插秧、割谷。這只能說明新田園詩的作者對當代田園多么陌生,“不知有漢,焉論魏晉”。
其三是思想膚淺,內容蒼白。當代的中國田園正處于轉型的陣痛期,各種隱憂逐漸顯現。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對土地喪失了熱情。田園的主體是農民,沒有主體,何來田園!有資料顯示,中國的農民正從土地上逐步消失。大量的農二代拋棄土地,想改變身分涌入城市,但他們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農村人,而是游蕩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人。現在堅守田園的多為孤寡老人,最后一代農民也都六十歲左右。即使是他們,也并不熱愛土地而出外打短工。國家實行種田補貼原意在鼓勵農民種田的極積性,不想事與愿違,農民拿了補貼照樣不種田,任由大片土地拋荒。照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的田園著實堪憂。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一時還真難找出答案。對于文學作品而言,說不清無答案即是深刻。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新田園詩往往避開深刻,表達膚淺;避開崎嶇險徑,慣走輕車熟路;避開實質難題,刻意追求“亮色”……這樣做的結果,作品就難避內容蒼白,美學價值不高。更可慮者,我們的評論一味唱響這類作品,不去引導作者對現實田園作深層次的思考,致使田園詩詞庸作、偽作充斥期刊,令讀者厭倦。
新田園詩是近年詩詞創作中涌現出來的新品種,曾經給詩壇帶來一股清風,形成詩壇一道靚麗的風景。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生活底子欠厚,作者隊伍不精,一哄而起,加之評論過分揄揚,導致作者感覺良好,滿足于現有的寫作狀態和水平,不斷地重復自己,模仿別人,至使新田園詩步入目前的尷尬處境。如何走出新田園發展的瓶頸,是到了認真反思的時候了。
(作者系國家一級劇作家、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理事、湖北省戲劇家協會理事。曾任黃岡市作家協會主席、本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