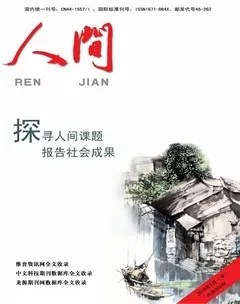不同民族背景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狀況的比較研究
——以重慶市彭水縣和湖北省羅田縣為例
余蒙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不同民族背景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狀況的比較研究
——以重慶市彭水縣和湖北省羅田縣為例
余蒙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100081)
近年來,“三農”問題成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其引發的“農民工”、“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留守婦女”……社會問題牽動著億萬人民的心。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農村適應改革開放、社會發展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也是專家學者研究“三農”問題的重要載體。本文通過對重慶市彭水縣和湖北省羅田縣的勞動力轉移狀況進行實證調查,并基于民族的視角對兩地的勞動力轉移狀況進行比較,希望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相關的政策制定提供可供參考的建議。
農村;民族;勞動力轉移
引言
“三農問題”是我國的社會熱點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村整體發展的改善,但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社會問題,比如老年人的贍養、幼齡兒童的撫養、教育,農村農業的荒廢、新農村建設的滯后問題等。此外,城市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如何協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新農村建設人力資源不足、發展滯后的矛盾;如何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后艱難、尷尬的生活處境,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如何因地制宜、科學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些都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需要解決的典型社會問題。不同民族地區,文化習俗、經濟發展產業模式、社會治理結構不同,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也存在著差異,探究不同民族地區的弄滾勞動力轉移現狀,對更好地理解我國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現象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文獻綜述
國外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較早,也比較成熟;中國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放開戶籍就業限制以后,農村人員才大量涌入城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現象也逐漸被學者、社會各界關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國內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基本狀況描述的研究,主要分為階段劃分,轉移規模,地域特征,行業和職業分布等。如崔傳義的《中國農民流動觀察》[1]和蔡昉在《中國流動人口問題》里面的四階段說;[2]蔡昉(2000)、王光棟、李余華(2004)等人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向當地非農產業、省內城鎮和省級跨區域轉移三種方式。何英華(2004)對省際非戶口農村移民的流向研究;[4]Hare(1999)按照農村勞動力就業人數的多少分別依次為:建筑業、制造業、采礦業、飲食服務業、商業等。[5]何英華(2004)的調查發現,商業、服務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及有關人員,建筑材料生產、加工人員及其它三類職業就業總計超過75%。[6]二是關于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三類:一是個人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等;二是家庭因素,如家庭老人、兒童、勞動力的人數,經濟情況,家庭負擔等;三是其他因素,如就業情況、遷移成本,政府政策等。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研究主要包括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城市工業發展和農村留守問題三方面。如駱友生、王劍文認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對城市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壓力、犯罪等。[8]胡蘇云和王振利用對安徽霍山縣和山東牟平縣農戶的調查資料發現,無論在相對發達還是相對不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對于家庭收入的提高均有很大的作用。[9]
綜合以上研究結論,學者研究的較多的是集中針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某一個方面進行實證和分析研究,但沒有人將不同民族地區放在一起比較分析,因此本研究能夠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二、基于不同民族地區的比較研究
重慶市彭水縣(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是典型的少數民族地區,而湖北省羅田縣主要是漢族。實證研究以調查問卷的方法為主,分別在調研地發放問卷100份,收回有效問卷96份。依據統計數據,彭水縣49份,羅田縣47份。其中彭水縣有4名土家族,44名為苗族;羅田縣47份均為漢族。
(一)性別差異。
如圖1所示,羅田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女性略多于男性,而彭水縣男性略多于女性。由于調查樣本有限,無法明顯體現兩地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性別差異。但可以預期,隨著樣本的擴大,兩地差異會越來越明顯。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女性少于男性。
(二)年齡結構差異。
依據調查數據,羅田縣18-28歲之間的有18人,31-40歲之間的有7人,41-50歲之間的有16人,51歲以上的有6人;彭水縣在17-20歲之間的有14人,41-50歲之間的有24人,60歲以上的有3人。彭水縣農村勞動力轉移集中在青年和中年,而羅田縣集中在青壯年以及中年。
(三)文化水平差異。

圖1:性別

圖2:文化水平
(四)轉移地點。
兩地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是外市或外省。區別之一在于羅田地區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外省工作時更傾向于浙江、上海、廣州、北京和新疆等地,而彭水縣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外市的多為鄰近的省市,如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區別之二在于,與羅田相比,彭水縣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在本市工作。總體而言,彭水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多集中在家周圍。
(五)動力因素。
表1:農村勞動力轉移動力

羅田縣 彭水縣頻數 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農村推力在家收入太低 39 44.32% 44 23.40%家里勞力多,在家沒事干 10 11.36% 8 4.26%農村太窮,生活太苦 11 12.50% 32 17.02%農村稅費太重,種地不合算4 4.55% 12 6.38%農村發展空間小,機會少 24 27.27% 40 21.28%農村生活單調、乏味 20 22.73% 52 27.66%城鎮拉力進城務工收入高 45 39.82% 44 35.48%外出開開眼界 20 17.70% 16 12.90%除外學習技術、增長才干 6 5.31% 32 25.81%城鎮生活方便,生活條件好17 15.04% 16 12.90%向往、喜歡城鎮的生活方式10 8.85% 16 12.90%別人都外出,受其影響 15 13.27% 0 0.00%
(六)制約因素。
1.不舍因素。
不舍因素分析如圖3所示,彭水縣主要集中在農村的親鄰鄉情、生活習慣和農村寬松的計生政策,傾向于感性思考;羅田縣主要集中在惠農政策、農村的住宅地和承包地,傾向于理性思考。
2.不適應因素。
不適應因素是現實、普遍存在的,如眾所周知的身份歧視、社會保障、風俗習慣差異、孩子的教育問題、戶籍制度限制等外出的不適應。與不舍因素相比,兩地的不適應因素總體差不多,表明這些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共性問題。如圖4所示。

圖3:不舍因素

圖4:不適應因素
三、對策建議
(一)發展地方產業,擴大就地轉移就業。要解決農村居民不得已外出務工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發展好地方產業,要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村居民就地轉移就業提供條件;要依據地方需求和特色,因地制宜,開發可供利用的土地、礦產資源;并形成地方產業鏈,建立農村專業合作社,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土地是農村資源開發的一大優勢,農村地區產業建設既要因地制宜,發揮農村地區特有的優勢,并與時俱進。
(二)增加農村投入,改善農村教育、醫療和養老條件。改善農村勞動力轉移狀況,必須增加農村投入,完善農村教育、醫療和養老保障體系。如對留守兒童的教育實行專業化管理,安排專門的看護人員,隨時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豐富他們的課余生活;完善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異地就醫醫療保障體系,為農村生病患者盡可能提供及時有效的醫療救治;適當提高農村的養老保障水平,改善養老保障機構的服務條件。
(三)加強農村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的綜合素質。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開展農業種植的技能培訓,宣傳和普及現代農業的發展的科學技術,提高農戶的農業生產能力,促進農村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二是針對外出務工人員,開展的各種專業技能培訓,如設立專門的農技和職業技能培訓學校,讓有需要的居民入校學習。
(四)支持農村勞動力回鄉創業,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吸引農村勞動力回鄉創業,首先政府要加強引導,提供必要的技術、人才、資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免除創業人員的后顧之憂,為創業者營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然后,政府要對創業成功人員進行表彰,對創業艱難人員給予指引和必要的資金支持,并廣泛宣傳創業的好處和意義;其次,政府有責任為大家普及創業有關的知識,引進專業人才供大家咨詢。
(五)加強農村地區文化產業建設,豐富鄉村文娛活動。農村由于地處偏遠,文化設施建設落后,文娛活動少而無法吸引年青人員,這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和新農村建設人力資源不足的原因之一。農村處在經濟發展落后和全球化的雙重夾擊之下,古老的傳統文化得不到傳承,現代性的文化建設有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文化感一點點被剝離殆盡。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豐富鄉村文娛活動,為恬淡、安逸的鄉村生活添姿添彩。
(六)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維權機制,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面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嚴峻現實,作為政府,首先應加強法律知識的宣傳,向民眾普及法律知識,養成法律維權的意識;其次,政府要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維權機制,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政府部門要及時了解農民工的工作情況和心理狀態,為他們排憂解難。
四、結論
湖北省羅田縣和重慶市彭水縣都是中部國家級貧困縣,民族差異大。處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彭水縣農村勞動力轉移性別差異明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是男性;羅田縣和彭水縣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整體文化水平均處于較低的層次,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能培訓,在外地工作只能從事“臟、累、苦”的機械性工作;少數民族地區受家庭傳統文化影響較深,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集中在市內或靠近家庭所在省市的臨近省市工作,存在一定的局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主要是農村可獲得經濟收益低,生活條件整體落后、單調;而城市掙錢機會多,生活方便,文化豐富多彩。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對家人的依戀,農村一些惠農政策,寬松的計生政策,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及社會環境的限制,如孩子的教育問題,老人的贍養問題,社會保險的轉移續接問題等。因此,在解決各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應在發展地方產業,出臺農村勞動力轉移保障配套的政策和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的基礎上,從思想上進行引導農村勞動力轉移,轉變貧困地區的受傳統束縛的文化習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維護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
[1]崔傳義:《中國農民流動觀察》[M],山西:山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2]蔡昉:《中國流動人口問題》[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4]何英華:《1995 -2000年戶口遷移和非戶口遷移:描述與分析》[Z],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 2004年.
[5]Denise Hare:《“Push”versus “Pull” Factors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 's Rural Population [J]. Journal of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
[6]何英華:《1995 -2000年戶口遷移和非戶口遷移:描述與分析》[Z],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2004年.
[8]駱友生、劉劍文:《農村勞動力跨區域轉移:現狀、成因與對策》[J],中國農村經濟,1994年第8期.
[9]胡蘇云、王振:《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就業及其對農戶的影響——安徽省霍山縣與山東省牟平縣的比較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年第1期.
C913
A
1671-864X(2016)05-0037-02
余蒙(1991—),女,漢族,湖北黃岡,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