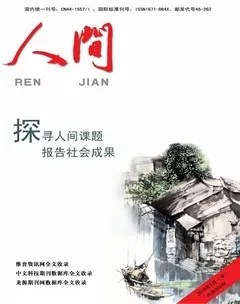結構現實主義理論視野下的東北亞格局解讀
李青青(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8)
結構現實主義理論視野下的東北亞格局解讀
李青青
(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250358)
結構現實主義視權力為國際體系的核心變量,其決定因素是單元(民族國家)權力的分配狀況,其終點在于體系條件下的單元行為。東北亞地區主要有六個分析單元,權力分布呈現出一種多極化的結構,中國的崛起、美國重返亞太、朝鮮半島局勢不穩等等,都成為影響東北亞格局的重要因素。
結構現實主義;東北亞;體系結構
引言
20世紀70年代后期,傳統現實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兩大理論都遭到了極大的挑戰,都無法解決現實政策調整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為適應現實的需求,不少學者敏銳地抓住新形勢的轉折點,逐漸開始對傳統現實主義進行“修正”,由此產生了新現實主義。1979年肯尼斯·華爾茲在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中提出了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為新現實主義提供了一個更有力的理論基礎,成為西方國際關系學中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的開拓者。華爾茲還曾提到,“只有通過理論的指導,才能在無限的材料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1]。
一、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解讀
新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相比,前者是對后者的深化與發展,結構現實主義主張在方法論上對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的融合與滲透。結構現實主義著眼于體系,研究單元之間的權力分配狀況,進行結構分析。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新”,就在于它的科學化水平,把國際體系作為研究層次,把體系結構作為主要自變量,把國家行為作為主要因變量,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作為基本條件。
(一)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
結構現實主義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主要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的,民族國家是國家社會的關鍵角色。與傳統現實主義相比,其新的觀點在于國際社會中的各個行為體之間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依存,但新現實主義的國際合作對于新自由主義又是消極的。
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不僅是由于國際社會之中不存在一個具有足夠權威性的世界政府,而且也是因為國際社會的過程是混亂的、無序的。結構現實主義學派把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分析單元,這些分析單元存在著力量對比,由此產生了權力的不均衡分配,這就導致了國際社會在產生權力的過程中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從國際社會存在至今,就一直處于無政府狀態,不存在一個類似于國家內部的中央政府來管理國際事務,甚至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也沒有這樣的作用。
“以無政府狀態為基本標志的國際體系是自助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國家的目的不是無限制的獲得、維持和增加權力,而是力圖保證自我生存。”[2]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安全,權力是追求目標的手段。
(二)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本行為單位。
華爾茲認為,結構的界定只是因為主要行為體所起的作用,這里的主要行為體指的是大國。所謂大國,主要指具有較強權力的國家,一般具體指物質能力,即國家“在下述所有各項因素上所得的分數:人口的多少和領土的大小、資源的儲量、經濟力量、軍事實力、政治穩定性和能力”[3]。在此標準下,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在亞洲南部大部分國家人口少、領土小、資源少,經濟力量薄弱,軍事實力相對較小,國內政治時有動蕩,因此這些國家我們可以認定為小國。
令人遺憾的是,在華爾茲的理論建構時代,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們在使用結構現實主義分析國際體系時,需要排除國際組織的作用。例如,在東北亞地區存在的國際組織G20、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發揮的作用,不在我們的分析范圍之內。
(三)結構是影響體系的最大因素。
華爾茲說道:“系統被定義為一系列互動的單元,從一個層次來說,系統包含一個結構,結構是系統層次上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它才可能設想單元組成一個體系,而不同于簡單的集合。”[4]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體系是一系列互動單元構成的,但這不是簡單的構成,因為結構也是體系的一部分。該理論強調體系與結構的關系,多個單元(民族國家)按一定的原則組成一個整體,這些單元之間的互動就構成了體系,即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國際體系。體系中的權力分配狀況決定了結構,體系會隨著結構的變動而變動。
二、東北亞分析單元的篩選與互動關系
根據上文表述,結構現實主義者尤其是著名代表人物肯尼斯·華爾茲認為大國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分析單元,因此首先需要找出東北亞的分析主體,進而分析這些單元之間的互動關系與行為。
(一)東北亞分析單元的篩選。
東北亞地區在地理位置上包括六個國家,蒙古因人口、資源、經濟等方面都非常有限,其他國家我們都稱之為大國。
隨著中國的崛起,在國際上中國成為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具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是當之無愧的大國。日本是東北亞地區公認的經濟強國,冷戰后不斷謀求其政治地位,軍事方面雖受美國保護,但其自身的國防力量也不容忽視。在朝鮮半島上,朝鮮與韓國兩個國家雖然人口少,國土面積小,但是其地緣位置在國際社會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與影響。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地員遼闊,其大部分地區位于亞洲大陸,隨著國際重心逐漸的由西向東轉移的趨向,俄羅斯越來越重視亞洲地區的發展,在亞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此外,在東北亞地區我們定不能忽視美國這一極其重要的因素,雖然美國在地理位置上不屬于亞洲大陸,但是在東北亞地區發揮著自己的獨特作用,尤其表現在美日同盟、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等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在重視歐洲的基礎上,同樣把目光放在了亞洲地區,重返亞太戰略就是其典型表現。
因此,在東北亞地區界定的分析單元是中國、日本、韓國、朝鮮、俄羅斯以及美國六個國家。
(二)東北亞分析單元之間的互動關系。
在東北亞地區,中美日俄韓朝六個國家之間相互聯系,構成了多個復雜的雙邊、三角關系,我們將其稱之為東北亞地區六大國之間的利益交叉體。其中,其核心作用的雙邊關系是中、美、日、俄四大國之間的中美、中俄、日美、日俄、美俄五大雙邊關系。這些雙邊關系深刻影響著東北亞地區的政治、安全結構,并形成了一張“立體式”的蜘蛛網。
以中美俄三國之間的互動關系為例,中俄關系不僅是東北亞地區而且是整個世界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俄兩國交好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如今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等方面的合作都具有良好地發展勢頭,正處于最好的歷史時期。冷戰后,中美關系逐漸得到改善,這不僅是中國崛起的需要,更是美國持續發展的要求。中美兩國主要還是以經濟合作為主,政治互信明顯遠不如中俄,增強中美之間的互信程度,無論對哪一方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顯而易見,中俄高級政治要強于中美,中美低級政治強于中俄,由此使得中國不得不采取“雙向”戰略,即在高級政治方面,不斷發展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關系,在低級政治方面,加強與美國的互利共贏。而對于俄羅斯和美國不得不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充分考慮中國這一不可忽視的因素。美國重返亞太、俄羅斯“東傾西向”戰略都離不開在中國方面的考慮。
單元之間的互動關系,不僅影響了體系結構,更重要的是各主要分析單元為了得到更多的權力而最終改變了國家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
三、東北亞體系結構的分析
結構現實主義主張在體系層次上來分析分析國際體系的行為,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結構決定了國際體系,“進而主導的是單位國家行為,不斷加速改變的卻是單位國家力量動態波動所形成改變國際體系結構的任何預期都將得到其他國家行為更為敏感的回應”[5]。因此,面對東北亞大國間的“暗潮涌動”,分析東北亞的體系結構是非常必要的。
根據結構現實主義來分析,東北亞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性質是無政府的,是一個自助系統。華爾茲認為,“在任何自助系統中,單元都對自身的生存感到憂慮,而這種憂慮卻限制了他們的行動。”[6]
如今,在東北亞這個自助體系中,六個主要分析單元都對自己的國家生存安全感到或多或少的擔心與憂慮。美、日、韓在冷戰結束后仍保持同盟關系,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即使重返亞太,但是美國的硬實力--軍事力量分布中心仍在歐洲地區,短時期內是無法調動足夠的軍力來維持它在太平洋地區的霸權,而且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美國在考慮與日本同盟關系的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因素而有所顧忌,甚至是收斂。
近些年,日本的種種行徑在國際社會都引起了不小的反映,如:購買釣魚島、參拜靖國神社、修憲擴軍等等。此外,朝鮮半島局勢“周期性動蕩”,是國際社會一直在擔憂的問題,但是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朝鮮半島雖動蕩不安,卻一直未能真正的發動戰爭,因為朝韓兩國都必須要考慮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爭帶給人類的永遠是災難,無論哪一方都不可避免的會遭受損失。
通過對東北亞現狀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在東北亞這一自助體系中,呈現出了多極化的結構。在權力分配方面,東北亞地區六個單位之中擁有最強大權力與地位的美國并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使得其他五個國家為了保證國家安全而友好合作,這正是由五個國家的國內因素決定的,除了國家性質這一根本原因外,歷史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同樣的,除美國外的其他五個國家都沒有足夠的權力成為單極結構。中國、俄羅斯經濟實力與日本、美國相比還有所差距,日本、韓國、朝鮮軍事實力不足,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東北亞的國際體系結構是多極化的。
“在國際政治多極結構下,各單元將為尋求安全而增加軍事等方面的投入,而這恰恰會使得其它單元感到恐懼,進而相應增加投入,陷入安全困境。換言之,今日使自己聊以自慰的增量將成為他人寢食難安的因素。”[7]結構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分配的變化會隨之改變體系結構。
美國重返亞太的重心主要表現在其國家的硬實力即軍事力量上,朝鮮不斷進行核試驗,日本企圖通過修憲擴軍等等,這些都是單位權力的變化,而無論是一變還是多變,都可能影響體系結構。美國與日本、韓國在冷戰之后依舊保持著同盟關系,特別是軍事同盟,美國不斷采取措施完善三國的關系,以確保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中國雖然與美國和俄羅斯都是友好合作關系,但是中美關系主要體現在經濟合作當中,中俄主要體現在政治互信與軍事合作方面,加之中俄不僅合作,還是睦鄰關系,所以中俄關系的合作力度要強于中美關系。隨著美日韓三方的軍事同盟體系不斷得到加強鞏固,將來可能會引起中、俄、朝由于安全壓力而走向進一步合作,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均勢。
結語
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以及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東北亞地區正處于大國間相互制衡的協調狀態,呈現出一種斗而不破的多極格局。對東北亞多極格局的分析,運用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來解釋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解釋所有的問題,因為結構現實主義事實上只是一種解釋路徑。用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來解讀東北亞格局只是對現實的一種而不是所有的解釋,因為世界在發展,理論在不斷創新。
[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e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
[2]王雷.論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J].重慶: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8.
[3]秦治來.國際政治學簡明教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27-128.
[4](美) 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M].信強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53.
[5]王宣華.國際體系演進的結構現實主義解讀及啟示[J].許昌:許昌學院學報,2009:11.
[6](美)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M].信強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139.
[7]曾守正.結構現實主義視角下的東北亞格局[J].廣州: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11:132.
D822
A
1671-864X(2016)05-0169-02
李青青(1990—),女,山東萊蕪人,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國際關系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國家和地區間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