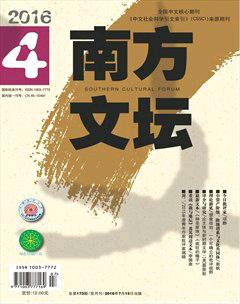當我們敘述戰爭時,我們敘述什么
毋庸諱言,過往的中國戰爭文學敘事,常常跟集體性、英雄性、民族性緊密地聯系在一起。20世紀以降的世界文學譜系中,從英雄主義向人道主義的轉折是戰爭文學的鮮明標識。這股潮流也促使了近年中國戰爭文學(包含電影等泛文學敘事)對狹隘民族主義話語的反思和對世界主義話語的內化。然而,這種文學實踐又常常陷落于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的話語糾結之中。民族主義的戰爭敘事站在民族性立場上指斥對手、塑造敵人、建構英雄,完成政治動員、整合民族認同、敘述國家前傳、建構政權合法性的功能。時至今日,各種抗日神劇的流行印證著民族主義話語法則并未耗盡其歷史勢能;另一方面,在近年關于抗戰歷史記憶的文學及影視敘事中,以世界主義為支撐的敘事逐漸成為一種流行話語。借用卡佛那個著名的句式,向戰爭敘事發出這樣的追問:當我們敘述戰爭時,我們敘述什么?敘述逝者的哀慟、敘述英雄的氣概、敘述民族的血淚和仇恨,同時也敘述民族的光榮與夢想,這大概是今日中國戰爭文學敘事最常見的答案。從中我們不難辨認出某種以英雄性、民族性為內核的敘事倫理。可是,慘烈復雜的歷史在召喚著新的民族災難記憶書寫,在我看來,熊育群積十幾年之功完成的新著《己卯年雨雪》正是一份帶著雄心和問題意識重構的民族災難記憶。同時,它更包含著文學如何面對戰爭、如何敘述戰爭這樣的敘事倫理關切。
建構生產性的戰爭反思敘事
《己卯年雨雪》引人矚目地以日本人武田修宏、武田千鶴子為重要主角。然而,小說采用的不是“反向視點”,而是“雙向視點”:小說既從日本人武田修宏夫婦角度,也從中國人祝奕典、左太乙等人的角度敘述戰爭。正如作者所言:“要真實地呈現這場戰爭,離不開日本人”,“超越雙方的立場,從仇恨中抬起頭來,不僅僅是從自己國家與民族的立場出發,從受害者的立場出發,而是要看到戰爭的本質,看到戰爭對人類的傷害,尋找根本的原由與真正的罪惡,寫出和平的寶貴,這對一個作家不僅是良知,也是責任。”①顯然,熊育群希望以超越民族性的立場去表現戰爭的傷害。可是,超越民族性并非好作品的充分條件。更重要的其實在于作品能否提供一份生產性的民族災難記憶。所謂“生產性”,意味著作者不是為“世界主義”而“世界主義”,其敘事不僅落實在超越民族的觀念上;意味著小說對戰爭的反思具備了抵抗“世界主義”新臉譜的具體性和深度。《己卯年雨雪》雖然始終拒絕將日軍作為刻板化的野獸形象進行敘述,但更拒絕為了“去臉譜化”而刻意復雜化。不妨以電影《南京!南京!》相對照,片中,陸川對日本軍人角川的人性復雜性處理便有為去臉譜化而形成新臉譜之嫌。恰恰是為了表現日軍的復雜性,陸川對角川進行了極度的單純化處理。我們知道,集體化軍事體制和酷烈的戰斗氛圍,很容易漩渦一般將所有人裹挾進去,從眾意識和嚴格的軍紀使獨自完美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幾無附著之地。就此而言,純潔角川其實是一種隔岸觀火、隔靴搔癢的文學想象。相比之下,《己卯年雨雪》就更為客觀地展示了戰爭對即使是最善良士兵人性的異化。小說中,武田修宏的身份被安排為一個熱愛哲學,理想是成為作家的多思青年,并設計了他參戰前的避戰心理。即使是這樣一種身份,作者也并未簡單地讓他成為日軍的人性代表。而是將他的鄉愁、恐懼和扭曲、異化作為一體兩面進行表達。同樣寫到武田修宏的性,熊育群突出的不是他的“出淤泥而不染”,而是他那種日漸滲透的心靈變異。當千鶴子在前線找到丈夫,在二人不可抑止的魚水歡愉中,武田修宏卻分明有著無法推開的分心:
扯下兜襠布,武田修宏荒野里勃發的情欲赤裸又熾熱,看著躺在地上的千鶴子,身上交錯著一道道黑色線條,這是蘆葦投下的影子。陽光刺得千鶴子瞇起了眼睛……支那女人的軀體突然浮現,她們遭人奸污的一幕幕過電影一樣晃動,千鶴子身子一瞬間像一具遺棄的軀體。武田修宏涌起一股厭惡的情緒。②
這段敘述精彩之處在于,武田修宏并非角川正雄那樣的純潔飛地,他的心靈不可避免地由于戰爭壓力的磨損而落下陰影。戰地的性壓抑和性發泄都消解了他對千鶴子原有那種洶涌熾熱、相互忠誠、非此不可的原初情感,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這樣的復雜性是可信的復雜性。同樣是拒絕將“敵人”臉譜化,熊育群細致地刻畫了日本軍人在大肆殺戮底下那種鄉愁、恐懼、迷茫而強找寄托的復雜心理,也努力追問殘酷的戰爭如何把人變成野獸的問題。
向山坡地發起沖鋒,沖在前面就意味著死亡。武田修宏幾次都想著要沖到最前面去,以證明自己的勇敢,武士道把人求生的愿望看做卑怯,偷生是羞恥的,他被羞恥感裹挾著,只有不斷證明自己不怕死才能擺脫這種羞恥的糾纏。但巨大的恐懼讓他邁開腳步時又退縮了。③
這里還原了軍人武田修宏的第一層心理沖突:武士道教育的獻身榮譽感與人性與生俱來的恐懼之間的沖突。武田修宏并非嗜血的動物,他在掃蕩中踢開堂屋的大門,看到屋內供奉的祖宗牌位,便不敢太放肆。他對死者不敢造次,戰場上有人去死人身上找煙抽,他從不用死人身上的東西。他身上還留著人的畏和怕,正因此他并不同于冷血的殺人狂魔和不通人倫的禽獸。作者也敏感地意識到畏和怕所導致的軍人的“迷信”,他們逃避某些不吉利的數字,身上帶著護身符。當戰爭把人拋進一個未知的黑暗管道時,“信”便是他們唯一能夠抓住的稻草,這是非常自然的。“戰場上,生命就像一場賭博,輸贏不到最后無從知曉。人們只有靠祈求神靈,求神靈保佑武運長久。士兵喜愛賭博,這是同一種心理。”④迷信和賭博反證著戰場士兵內心的茫然和恐懼。戰爭迎面撲來,個體渺小得如同驚濤駭浪中的一葉飄萍。心藏反戰情緒的武田,也必須在戰爭中拼命搏殺,在你死我活的肉搏中,“人們從血中聞到了一種腥甜,勾起嗜血的原始欲望。殺人是戰爭的手段,現在殺人是目的了。”⑤這里對戰爭加之于個體的異化效應有著深刻的洞察。它并非在寬宥戰場上的殺戮者,抹平戰爭中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而是以更深刻的洞察力,撕下長期貼在所有“敵人”臉上的面具。因為,為“敵人”貼上一副邪惡丑陋、千篇一律的面具遠比洞察恐怖敵人臉譜下面的豐富表情容易得多。前者抵達的是一個已經做出的正確判斷,而后者則期望用更具體的生命和歷史情境去提供進一步反思的可能。endprint
最初,武田修宏并不愿參軍,可是在家族、社會所交織出的集體壓力、榮譽補償的價值坐標中不得不無奈上陣。小說以深厚的史料支撐說明參戰共榮的價值理念已經成為彼時日本社會廣泛的民間意識。作品中,千鶴子正是充分習得此種意識的日本人,他們認為“蔣介石是個混蛋,不顧人民的死活,不要和平,死硬要跟日本人打仗。他是戰爭的罪犯。那時,千鶴子正在讀高村光太郎的新體詩,讀到了他寫蔣介石的詩歌《沉思吧,蔣先生》。國內許多人寫起了戰爭的和歌與俳句,她把這首詩抄寄給了武田修宏”⑥。千鶴子作為一個代表表明個體作為被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整合起來的對象,很難逸出其定義的思想空間。只有當她真正遭遇戰爭之后,她才深刻地意識到這種意識形態實踐的虛構性。《己卯年雨雪》區別于一般世界主義的戰爭敘事之處在于,它不但提供了“敵人”臉譜下復雜的表情,更對戰爭何以發生,戰爭如何被認同提供了深入的解釋和反思。換言之,當陸川將戰爭敘事語法由民族主義式的“看啊,這禽獸”轉換為“看啊,這禽獸也是人”之后;熊育群更進一步提供了“人如何成為人獸”的故事,他內在的關切其實正是“人如何免于成為禽獸”。我想,這既是對狹隘民族主義敘事的超越,也區別于抽象人性主義,它指向的是一種生產性民族災難記憶的建構。
重建抵抗者的文化主體性
《己卯年雨雪》在超越民族主義的同時,并未以“人性主義”進行“去民族化”敘事。在后殖民的文化背景下,民族敘事常常不可避免地落入各種身份危機之中。可貴的是,《己卯年雨雪》人道主義敘事依然內在于對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堅持中。這在作品中主要體現為祝奕典、左太平尤其是左太乙這些人物的塑造。從情節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認為主角是武田修宏、千鶴子,或者是祝奕典,可是從小說的精神內核看,我們甚至可以將主角指認為左太乙。因為小說中左太乙并非一個功能性人物,他攜帶著一套獨特的世界觀,為這部關于民族創傷記憶的小說提供了一個超越性的精神維度。如果不理解這個維度,就沒有真正把握到小說的精髓。左太乙的兄弟名叫左太平,太平和太乙既是同胞兄弟,又關聯著兩種中國傳統思想。太平關涉的是經世致用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儒家;太乙關聯的則是遺世獨立羽化登仙的道家。小說題名“己卯年雨雪”,而不是“1939年雨雪”,自是意味深長!1939是公元紀年系統上一個唯一的年份,而己卯則是每六十年一循環的天干地支紀年中的年份節點,這種中國傳統的紀年方式來自道家思想。它隱隱暗示著,作者將現代性的災難事件納入中國道家思想資源中尋求拯救與逍遙的可能。不明乎這一層,恐怕無法真正把握作者的思想內質。與左太乙/左太平的命名相類,王旻鯤/王旻鵬這組命名也有著道家背景(鯤鵬來自于莊子《逍遙游》)。
小說中,左太平、左太乙和祝奕典構成了中華文化人格的三種類型:湘陰縣長左太平秉承的是儒者的風骨,左宗棠那種“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人格情懷深深影響了他,所以他帶領著鄉民“大股敵來則避,小股敵來則斗,敵進則斷其歸路,敵退則截其輜重,與祖宗廬墓共存亡,不離鄉土,不輟耕作,捍衛鄉土”⑦。顯然,家國患難之際,左太平這樣的儒官乃是民族之棟梁。相比之下,祝奕典身上更多的是俠者氣概。“他一會兒是篾匠,一會兒是跑江湖的船幫,一會兒殺日本梁子,一會兒又與土匪糾纏不清,隱身江湖,任性而為,從無約束。”⑧他身佩五行刀,手刃日本兵,英雄傳說一直在江湖。他被擁戴為首,嘯聚抗日。左坤葦和王旻如都愛著他的野性和英雄氣概。這種俠人格一直充盈于中國通俗小說中,并占據著中華人格版圖的重要空間。可是,熊育群最傾心的卻應該是左太乙所代表的道家人格。長期居住在楊仙湖荒洲上的左太乙親近節候所代表的自然,親近群鳥所代表的生靈。他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念都無所不在地踐行著“道法自然”的法則。作為一個常人眼中的怪老頭,從秋到春,他都住在三洲,與群鳥為伍;總是在第一聲春雷炸響,準備著從三洲撤退。左太乙的怪體現在他已經將生活行動跟自然時間建立起固定的關系;左太乙與自然中的生靈也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想念那些朝夕相處的鳥,三天沒聽到它們的叫聲便覺得身上不自在。他為水上的白鷺取名,或噢噢、麻羽、雪羽、大鳴、小鳴、長腳仙,他為受傷的白鷺療傷,他與白鷺對話并建立一種相互可解的語言。在我看來,左太乙的“道”既是自然,更是深情,是切近自然之后對生靈的慈悲和憐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武田千鶴子作為戰俘在中國活下來,正來自左太平、左太乙和祝奕典三人的“搭救”。祝奕典是千鶴子的捕獲者和施救者,他之不忍之心,既來自千鶴子跟王旻如外表相似所激發的懷念、同情等復雜情愫,也來自作為人的基本理性(“殺王旻如的是日本兵,與這個女人沒有關系”);左太平是放過千鶴子的重要助力,在獲悉祝奕典俘獲日本女人之初,他便發出留下活口的命令。他的動機顯然是出于戰局的現實性考慮。而左太乙卻以一種高貴慈悲憐憫接納了千鶴子這個異族女子,在他那里,連白鷺的生命都需要鄭重對待,何況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呢?如果不是左太乙的支持乃至堅持,千鶴子是不可能在左家獲得生存空間的。換言之,三種中國文化人格參與了對千鶴子生命的拯救接力。一面是承受著非人般的暴力災難,一面依然擁有面對世界的理智心和慈悲心。這種超越以暴制暴仇恨倫理的書寫,事實上重建了被侵略的抵抗者在高文明滋養下的文化主體性。
在陸川的電影中,承受災難的中國人并沒有獲得完整自我表述的機會,他們命如螻蟻,魂也如螻蟻。如果說陸川對日本士兵抱持同情的話,(這并不需要否定)他對中國人卻有著太多的苛刻,他以人性的名義放逐了中華的文化主體性。相比之下,熊育群則傾心于道家文化,并將道跟儒、俠一道確立為小說的內核,進而確認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這使《己卯年雨雪》在接納人道主義話語、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同時沒有陷入民族身份認同的困境。
虛構/非虛構:事關一種寫作倫理
讀者很容易從《己卯年雨雪》中讀出一種非虛構性。正如作者一再申明的,此書所依據的發生于1939年的營田慘案不但有史可據,而且也經過作者千辛萬苦、歷時多年的口述史田野實證。“60年后,我動員屈原管理區的朋友易送君對‘營田慘案做田野調查,二十多個人歷時一年,尋找到了一百多個幸存者,記錄了那一天他們的經歷。”⑨小說最重要的情節武田千鶴子來中國慰軍并尋找丈夫武田修宏這一線索同樣生發于現實原型⑩。作者這樣表白:“長篇小說《己卯年雨雪》中幾乎所有日軍殺人的細節和戰場的殘酷體驗都來自這些真實的記錄,我并非不能虛構,而是不敢也不想虛構。我要在這里重現他們所經歷所看到所制造的災難現場。”11endprint
近年來,散文領域中非虛構作為一股潮流強勢崛起。相比之下,小說中的“非虛構”就顯得更加意味深長。它意味著虛構和非虛構在尋找著一種倫理上的共處契機。小說就其文體特質而言當然不能背離虛構,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緣由使得《己卯年雨雪》有援引“非虛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呢?這里也許必須區分一下小說的物質外殼和小說“非虛構”的區別。小說物質外殼的構造確實在考驗著作家實證的工夫,特別是涉及非當下題材時,作家如果不對故事發生的時代歷史器物有一番艱苦卓絕的摸底的話,不免陷入一落筆便是錯的困境。而小說“非虛構”則意味著小說支撐性的背景、情節、人物皆具有現實依據和佐證。就此而言,我們既可以說《己卯年雨雪》下了深厚的實證工夫,也可以說它是具有濃烈“非虛構”色彩的小說。問題于是變成了:作為小說,它為什么需要“非虛構”?虛構是人們賦予小說的文體特權,在何種意義上,作者對于這種小說特權的謹慎會成為一種美德呢?
虛構從來不同于胡編亂造,正如李敬澤所說“虛構之肺要吸納全世界的空氣”12,這些空氣既有著實證性的部分,更有著倫理性的元素。因此,《羋月傳》讓秦代的人物用紙筆通信意味著其虛構吸納的實證空氣包含了過量的毒霾;《金陵十三釵》讓妓女們代替女學生前去日營(此一情節《南京!南京!》也有)則意味著其虛構的倫理空氣將讓女性主義者嚴重不適。換言之,嚴肅的虛構背后都包含著嚴肅的實證表達和嚴肅的倫理表達。嚴肅的實證表達在《己卯年雨雪》中體現為作者對歷史現場的還原和對日本歷史文化的深入探究。從史料上意外獲悉1939年在故鄉營田所發生的日軍屠殺到將已經湮沒于時間中的事件進行記憶拼圖,他下足了一番歷史學者式的田野功夫13。為了對侵略者有足夠客觀理性的認識,他又下了一番文化學者的功夫:“我開始注意日本這個大和民族,從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開始,我讀一切研究日本的書籍,從小泉八云的《日本與日本人》、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網野善彥》《日本社會的歷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歷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我進入日本的歷史文化,尋找著緣由,我渴望理解它的國民性。”14為了重建一份有價值的民族災難記憶,熊育群既成了中國抗戰史專家,也成了日本歷史文化專家。在后記中我們發現熊育群對日本的歷史、文化、政體、民族性格乃至于軍隊建制都有獨到的分析,這些都內化到小說敘事中。只是他的立場不是口述史、報告文學,也不是歷史文化研究。所有的知識背景僅是寫作出發的基礎,又對作者吁請著個人的精神位置和話語立場——一種嚴肅的倫理表達。
如此,我們似乎可以回答《己卯年雨雪》為何需要“非虛構”了。如上所言,嚴肅的“虛構”并非沒有條件,當它所服膺的倫理面對特殊的現實,吁求嚴苛的真實時,“非虛構”便會成為與小說“虛構”合二為一的河流。這里“特殊的現實”指的便是大屠殺的災難記憶。也許沒有任何事情像大屠殺這樣,事實便是其戲劇性的最大值,任何減少或夸大都將減損其文學感染力。當你企圖面對歷史反思歷史時,誠實是最大的美德。我想熊育群一定意識到這一點,歷史記憶敘事在召喚著“非虛構”。在真實的歷史災難面前,任何聰明的故事編撰都是乏力而捉襟見肘的。這是何以嚴歌苓充滿戲劇性的《金陵十三釵》雖然精致好看,但我反而對哈金將戲劇化風格最小化的《南京安魂曲》充滿敬意的原因;這是相比充滿戲劇性張力的《小姨多鶴》我更致敬具有非虛構底座的《己卯年雨雪》的原因。
可是,且慢。莫非我主張的是歷史記憶敘事的“非虛構”化?莫非我以為《己卯年雨雪》是一部純然“非虛構”的作品嗎?當然不是。“非虛構”是面對歷史記憶的倫理,可是“虛構”才可能提供更高的文學倫理。這里的“虛構”指的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想象一種面對世界的精神法則。具體到《己卯年雨雪》則是將戰爭記憶上升為一種戰爭文學敘事,在常常或陷于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和民族主義,或困于去民族化的世界主義的戰爭敘事迷津中尋找一種具有超越性、融合性的文學倫理。
戰爭作為一種有組織、規模化的極致暴力現象是長期伴隨人類的重要社會現象。時至今日,此刻,依然有相當多的人正遭受著戰爭的蹂躪,在戰火中流離失所。伴隨戰爭而來的戰爭文學可謂最古老的文學類型。以歐洲而言,戰爭文學經歷了從英雄主義到人道主義的轉變。人們在《荷馬史詩》中既讀不出明顯的部落、族群意識,更讀不出對戰爭殺戮的恐怖意識。只看出對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奧德修斯這些或勇敢或智慧的英雄的禮贊。戰斗中的勇敢被視為對生命意義的最高詮釋,這種英雄主義的價值觀使荷馬時代的人在諸神的陰影下獲得了人的尊嚴。中世紀的的英雄史詩在英雄主義之外還融入了封建忠君意識和宗教意識,只有在資本主義及其孕育的人道主義話語空間中,對英雄史觀和戰爭殺戮的反思才可能成為重要的文學主題。眾所周知,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描寫的是俄羅斯反抗法國入侵的衛國戰爭。雖然托爾斯泰是站在本民族立場上表現戰爭。可是,他的立場遠遠超越了民族戰爭意義上的勝利/失敗,他思考得更多的是生/死、靈/肉、有限/永恒、自我/他者等形而上的生命話題,或者說廣義的戰爭/和平議題。
20世紀二次世界大戰使作者們在驚悚的戰爭體驗中提煉出存在的意義危機和生命的荒誕意識,在此基礎上,反英雄、反戰爭、反崇高的頹廢性戰爭敘事倫理才得以確立。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中,巴恩斯之喪失性能力是他不得不承受的戰爭后遺癥。問題是,這個后遺癥作為一種文化隱喻卻不能在民族論的意義上建立起來。眾所周知,美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受益者。如果站在個人—民族同構的身份認同基礎上,美國青年巴恩斯身上的文化隱喻絕對不是“喪失性能力”。反過來說,海明威顯然是站在人類的意義上感受著戰爭的肉身毀滅性和精神破壞性。《永別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的戰爭體驗就充滿頹廢感:“我可沒見過什么神圣的,所謂光榮的東西也沒有什么光榮,所謂的犧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場,只不過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裝進罐頭,而是掩埋掉罷了。”15海明威以降,對戰爭荒誕性的反思體現在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馮古內特的《第五號屠宰場》以及電影巨作《現代啟示錄》等等作品之中。endprint
值得追問的是,今天什么樣的作品才堪稱現代的戰爭文學?或者說,現代的敘事文學吁求著什么樣的文學倫理?王富仁先生認為有必要區分“戰爭”“戰爭記憶”和“戰爭文學”這三個概念,在他看來,前二者是事實上的層面,從屬于現實和歷史;而后者則屬于想象和文學:“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中,我從電視里觀看到美軍導彈轟炸伊拉克的場面。空襲開始之后,巴格達上空烏云翻滾、硝煙彌漫,炮火驚起了一群飛鳥,它們在戰云翻滾的天空中驚懼地鳴叫著。這是什么?我想,這就是戰爭文學。戰爭文學是什么?戰爭文學就是這群飛鳥,就是這群飛鳥的叫聲。”16
王先生站在人類性的立場上作出的描述既形象又充滿啟發,戰火中的飛鳥鳴叫當然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它具有現實利益的超越性和戰爭災難的反思性。這群飛鳥是一種確鑿無疑的戰爭現實,選擇描述這群飛鳥則已經涉及一種敘事倫理。回到上面的卡佛式提問。當我們敘述戰爭時,我們不僅是在還原歷史、重建記憶,更是在探尋一種面對戰爭、面對人類災難的敘事倫理態度。誠然,民族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的話語幽靈依然盤踞在大部分中國戰爭敘事的上空;而荒誕、頹廢的西方現代主義式戰爭敘事在超越民族主義之途中也常常把我們帶入生之虛無境地。在此意義上回看《己卯年雨雪》會發現,它描述的不但是戰火中飛鳥的鳴叫,更是戰火中人性的鳳凰涅槃。小說對戰爭加之于人的現實和心靈傷害的表現自然可圈可點,可是更重要的是,作者依然對人性的包容性、交往性保有信心。可以說,當戰爭以摧毀一切的盲目性使人受苦、使民族蒙難之際,是人性的光輝重新拯救了深陷危機的武田千鶴子;是人性的可交往性使千鶴子從戰爭宣傳中擺脫出來,理解了戰爭的苦難和中國人心中的善。這種對人性的信心也許是《己卯年雨雪》區別于大量西方荒誕性戰爭敘事的地方。
結語
也許可以概括熊育群的戰爭敘事背后的文學倫理了:這種倫理首先是面對歷史的誠實,它在逝去的時間之河上打撈史實,以歷史文化框架探析日本發動戰爭的民族心理,從而沉淀關于歷史的真知灼見。由此作品舍棄了某種虛構的特權而與非虛構迎面相逢。這種倫理也是超越性的。它超越狹隘民族主義,拒絕僅從某個民族國家的立場來描述戰爭的勝利與失敗,由此它具有對戰爭中普遍人類創傷的深切同情。同時,它也超越臉譜化的人性主義和簡單的“去民族化”世界主義。簡化的人性主義把人性復雜性變成了一張新臉譜,將人性之平庸視為人性之絕對本然;又將人性普遍性絕對等同于“去民族化”。《己卯年雨雪》恰恰賦予了普遍人性以具體的歷史文化內涵,其中的人性既是普世的,也是民族的。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學倫理隱含著對人性光輝性的理解:人性的脆弱中包含著恐懼、自私、貪婪等因素,但人性同樣包含著光輝的、值得信賴的拯救性力量。這種“向光”的文學倫理不僅為戰爭文學所需要,也為備受虛無主義折磨的現代主義文學所迫切期待著。正是在此背景下,我覺得《己卯年雨雪》是一部有確信、有雄心的作品。它在20世紀戰爭敘事被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擠壓得狹小逼仄的甬道中另辟蹊徑,既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又堅持了民族文化主體性;既堅持了人道主義,又區別于去民族化的簡化世界主義。這使這部作品在中國抗戰敘事譜系中獲得了鮮明的辨析度和思想價值。這顯然不是一部可以用一篇文章說完的小說,它的思想和藝術抱負,值得這個時代認真辨析,鄭重以待。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4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87、104、69、71、72、65、35、41、365、386、373頁,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⑩如作者后記言,千鶴子以日本女人近藤富士為原型,這源于作者對馬正建編寫的《湘水瀟瀟——湖南會戰紀實》一書的閱讀。《己卯年雨雪》,377頁,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12李敬澤:《精致的肺》,載《十月》2016年第1期。
13十幾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熊育群從史料中獲悉1939年在故鄉營田所發生的日軍屠殺慘案。那些他所熟悉的村莊的名字跟殘酷的戰史相連,強烈地震撼著他的心靈。可是,他要面對的是歷史細節的湮滅和今人戰爭記憶的抽象化。“發生在我出生和成長之地的戰爭我竟然不知道,它離我出生的時間還不到20年!”重回兒時記憶,“外公常說走兵,中央軍、日本梁子一撥撥來了去、去了來,他常搞不清是誰的部隊”。《己卯年雨雪》,361-362頁,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15海明威:《永別了,武器》,林疑今譯,18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16王富仁:《戰爭記憶與戰爭文學》,載《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
(陳培浩,韓山師范學院文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