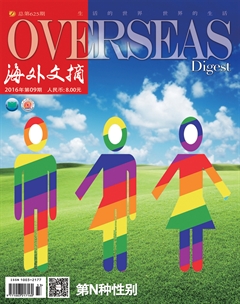教師職業(yè)危機(jī)
金慶敏·金明智++倪戌冰
在韓國,教師十分受尊重,也是相親時(shí)好感度很高的職業(yè)之一。據(jù)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去年發(fā)布的報(bào)告稱,受調(diào)查的15歲以上的韓國青少年中,選擇“希望成為一名授課教師”的人數(shù)占調(diào)查總?cè)藬?shù)的15.5%,是這項(xiàng)調(diào)查平均比例的近三倍。韓國言論振興財(cái)團(tuán)對私立高中的學(xué)生就未來職業(yè)選擇進(jìn)行了問卷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教師僅次于公務(wù)員,位列第二。
“我曾在物流公司的客服中心打過工,但現(xiàn)在覺得比那個(gè)時(shí)候還要累。”35歲的李雅英是韓國首爾市某私立高中的合同制英語教師(僅簽訂了一年),現(xiàn)在準(zhǔn)備辭去教師職務(wù),赴國外攻讀研究生。雖然李雅英從高中起就夢想著能成為一名英語教師,但在真正走上教師道路的這幾年里,她卻越來越懷疑當(dāng)初的選擇是否正確。去年,與李雅英就職于同一所高中的李雅英的大學(xué)同學(xué)A,因難以啟齒的事選擇了辭職,也因此對教師職業(yè)充滿了失望和質(zhì)疑。
“后悔當(dāng)了教師”
曾同為私立高中合同制英語教師的A平時(shí)輕聲細(xì)語,為人處世小心謹(jǐn)慎。調(diào)皮學(xué)生經(jīng)常拿她開玩笑,玩笑內(nèi)容越來越肆無忌憚,終于有一天,“A和有婦之夫偷情”的謠言在學(xué)生間散布開來,甚至傳到了學(xué)生家長的耳朵里。即便學(xué)校和A本人一再解釋這不是事實(shí),只是孩子們開的玩笑,學(xué)生家長還是要求學(xué)校開除A。家長們認(rèn)為這涉及到個(gè)人品質(zhì)問題,并表示他們絕不妥協(xié)讓步。最后,A一年的合約還未滿,就不得不離開了學(xué)校。
李雅英說:“A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癥。我現(xiàn)在越來越覺得教師這個(gè)職業(yè)似乎更像服務(wù)業(yè)。每當(dāng)遇到把老師當(dāng)成服務(wù)員的學(xué)生和學(xué)生家長時(shí),我就非常后悔當(dāng)老師。”
韓國現(xiàn)任教師又是如何看待教師這一職業(yè)的呢?經(jīng)合組織發(fā)布的“2013年教師教學(xué)國際調(diào)查”分析結(jié)果顯示,韓國有20.1%——超過調(diào)查對象國平均數(shù)兩倍以上——的教師表示“后悔當(dāng)了老師”,相當(dāng)于每5名韓國教師中就有1名后悔自己當(dāng)初的職業(yè)選擇。
越來越多教師希望退休,這種現(xiàn)象也進(jìn)一步使問題突顯。據(jù)新國家黨議員姜恩熙從教育部收到的“2013-2015年各市退休申請和批準(zhǔn)現(xiàn)狀”的報(bào)告顯示,申請退休的人從2013年的5946名,到2014年的13376名,再到2015年的16575名,呈逐年遞增趨勢。事實(shí)上,離開講臺(tái)的教師從2013年的5370名,到2014年的5533名,再到2015年的8858名,也呈遞增趨勢。
教師們離開學(xué)校的理由也各種各樣,其中包括行政雜務(wù)導(dǎo)致工作壓力過大、難以適應(yīng)隨時(shí)變更的課程、因公務(wù)員退休金改革而對老年生活感到擔(dān)憂等,因?qū)W生對教師實(shí)施暴力和學(xué)生家長過度干涉引起的教師威信受損也位列其中。
暴力事件
2015年12月,從網(wǎng)絡(luò)上流出一段拍攝于韓國京畿道利川市某高中的視頻,視頻中學(xué)生用掃帚毆打并辱罵老師。“掃帚毆打教師事件”引發(fā)了學(xué)生和學(xué)生家長對教師使用暴力的問題的激烈爭論。教師遭受暴力的情況并非近來才有。中學(xué)教師B因訓(xùn)斥上課時(shí)間玩手機(jī)的某名學(xué)生而被威脅“我要打碎你的腦殼再殺了你”;高中教師C被學(xué)生用椅子擊中前往醫(yī)院,最后因受這件事沖擊過大而申請退休。
女教師遭性騷擾蒙羞的事件也比比皆是。高中教師D在學(xué)校小賣部前看到有學(xué)生用紅色噴漆寫了提及自己身體部位,以及“想和老師發(fā)生性關(guān)系”這樣的話,但即便D看到了這些污言穢語,也要裝作毫不知情的樣子,照常走進(jìn)教室上課。一位現(xiàn)任的高中教師說:“這些現(xiàn)象在教師實(shí)習(xí)期更加嚴(yán)重,即使那些實(shí)習(xí)女教師正式入職了,也還是會(huì)聽到‘姐姐我們交往吧這樣的話,甚至有不少學(xué)生直接詢問女教師的性經(jīng)驗(yàn)。對這種見怪不怪的‘性騷擾,我現(xiàn)在都可以做到一笑了之了。”
韓國全國教師總聯(lián)合會(huì)(以下簡稱總會(huì))發(fā)布的資料顯示,近5年,由學(xué)生和學(xué)生家長引起的侵害教師尊嚴(yán)事件不斷增加:2010年2226起,2011年4801起,2012年7971起,2013年5562起,2014年4009起,5年共計(jì)24569起。總會(huì)發(fā)言人金東碩對此表示:“每年光接到報(bào)案并正式登記在冊的侵害教師案件就有數(shù)千起,默默忍受侵害而沒有報(bào)案的教師的數(shù)量更是無法想象。”
侵害教師事件使教師的教育權(quán)利和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權(quán)利都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為防止此類事件繼續(xù)發(fā)生,政府去年籌劃了“提高教師地位及保障學(xué)業(yè)活動(dòng)特別法”修訂案。該法案重點(diǎn)從教育監(jiān)督員、校長、學(xué)生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尊師重道,維護(hù)正在逐漸崩塌的師道尊嚴(yán),讓教師在一個(gè)更安全的環(huán)境里教學(xué)。
該法案規(guī)定,毆打、辱罵教師等事件發(fā)生后,案情知曉者有義務(wù)及時(shí)保護(hù)教師并將保護(hù)措施、案件內(nèi)容及處理結(jié)果上報(bào)教育部長官或教育監(jiān)督員。法案中還提及,各級學(xué)校均需設(shè)立學(xué)校保護(hù)教師委員會(huì),以便在學(xué)生監(jiān)護(hù)人或?qū)W生對教師實(shí)施暴力時(shí),起到積極保護(hù)教師的作用。
這是一部為了保障教師人權(quán)而籌劃的初級法案。以該法案為基礎(chǔ),政府推出了進(jìn)一步保護(hù)教師的措施:提供以教師為幫助對象的法律咨詢服務(wù)。自2011年起,韓國總會(huì)與律師協(xié)會(huì)攜手推進(jìn)“一所學(xué)校一名法律顧問”的制度。首爾市教育廳與總會(huì)也從去年起構(gòu)建的由律師組成的“維護(hù)教師尊嚴(yán)法律支援團(tuán)”,為發(fā)生侵害教師尊嚴(yán)事件的學(xué)校和被侵害教師提供法律咨詢服務(wù)。
但一時(shí)之間,社會(huì)上對這些保護(hù)制度的實(shí)際效果還持懷疑態(tài)度。在沒有常設(shè)律師的情況下,專業(yè)咨詢師應(yīng)對法律條文時(sh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何況學(xué)校只有一名專業(yè)咨詢師。還有許多人認(rèn)為這些措施會(huì)打破最傳統(tǒng)的師生關(guān)系,而直接將老師和學(xué)生看作潛在沖突事件的當(dāng)事人。對此觀點(diǎn),首爾市教育廳保護(hù)教師支援中心教學(xué)視導(dǎo)人員金道鍵解釋道:“細(xì)想,教師最終面對的還是‘學(xué)生,因此即使教師受到了侵害,人們還是非常忌諱(沖突、對立的師生關(guān)系)的。”
合約關(guān)系
“最近,師生問題已成為社會(huì)熱點(diǎn),師生關(guān)系從過去傳統(tǒng)的尊師重教漸漸轉(zhuǎn)變成合約關(guān)系,”建國大學(xué)的楊圣觀教授認(rèn)為,“教師尊嚴(yán)不被尊重并不是新鮮的事情,新的教師文化中已經(jīng)浮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相沖突的部分。”引進(jìn)教師評價(jià)制度和薪酬等級制度(按韓國政府規(guī)定,教師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等定量評價(jià)方法、實(shí)行學(xué)生人權(quán)條例等措施都使得整個(gè)教師文化漸漸變得只以合約為中心,這也說明了教授觀點(diǎn)的真實(shí)性。雖然以前也有過類似的問題,但是在保有原先師生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再互相多一些忍耐和包容,就可以解決問題。而現(xiàn)在不同,隨著選擇舉報(bào)并“公了”的情況不斷增加,師生關(guān)系已成為社會(huì)問題。在這一點(diǎn)上,互聯(lián)網(wǎng)和社交網(wǎng)絡(luò)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事件發(fā)生之后,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的問題還未解決,這起事件可能就已經(jīng)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和社交網(wǎng)絡(luò)在大范圍內(nèi)極速擴(kuò)散開。
社會(huì)看待教師的視角也有所變化。去年從中學(xué)校長一職上退休的一位前任教師就表示:“最近在年輕教師中,很多人與其說帶著使命感,倒不如說是真正的上班族。不管是老師、學(xué)生還是學(xué)生家長,一旦發(fā)生問題,都直接向外部機(jī)構(gòu)或者學(xué)校內(nèi)的各類委員會(huì)投訴。正因這樣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學(xué)校的整體氛圍也和從前截然不同。”
韓國全國教職員勞動(dòng)工會(huì)發(fā)言人宋在赫指出:“教師政策把教師對象化、客體化,使得教師失去尊嚴(yán),因此形成了輕視教師的不良社會(huì)風(fēng)氣。”在他看來,雖然身為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學(xué)生和老師互相指責(zé),但事實(shí)上兩者都只是制度的被害者。應(yīng)試教育把學(xué)生們逼進(jìn)了無盡的競爭關(guān)系中,而比起學(xué)生的綜合素質(zhì)教育,老師更關(guān)心提高學(xué)生成績和自身的教學(xué)評價(jià),如此冷漠的教學(xué)環(huán)境使得教師文化變得畸形。宋在赫充滿憂慮地說:“在情況極其嚴(yán)重的時(shí)候,我們就需要采取強(qiáng)制教育措施,但一旦這樣的方式成為主流,教育就會(huì)消失殆盡。”
亞洲大學(xué)教育學(xué)教授李奎美認(rèn)為:“我們需要一種全面的觀點(diǎn),包括考慮到師生、父母與子女等各類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應(yīng)該遵守的‘底線被攻破等情況。”建國大學(xué)楊圣觀教授則表示:“我們需要樹立‘教師人權(quán)和學(xué)生人權(quán)同樣應(yīng)該被尊重的價(jià)值觀,并采用新的作業(yè)方式,去維護(hù)新的教師文化中教育主體的權(quán)利,平衡教育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
[譯自韓國《時(sh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