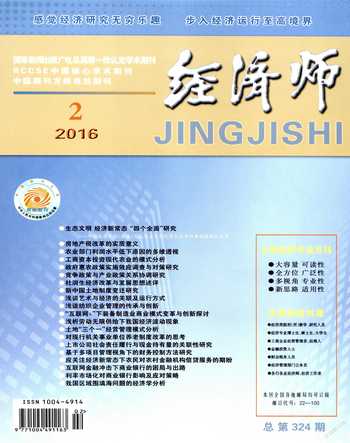基于公平視角的勞動者離職決策模型研究


摘 要:在傳統的經濟學思想中,勞動契約表現為簡單的勞動力需求模型,雇主需要做出的管理決策只有有限的幾個。因此建立在古典契約思想上的勞動契約的執行是存在第三方強制或者契約是自我執行的。但是實際上勞動契約的本質是第二方執行契約,即為了保護資本要素所有者的利益,資本方便會利用勞動契約短期化及隨意解雇來降低勞動力成本。如今人力資本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日益受到重視,從而人力資本的所有者能夠參與分享企業的剩余,而且在歷史的發展中和理論邏輯上也證明了這一點。
關鍵詞:勞動契約 解雇 公平
中圖分類號:F249.26;D4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2-235-05
雇主與勞動者的合作是一種雙贏,雙方通過共同合作達到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的結合,從而創造出超過任何每一方單獨創造的價值之和(在這里實際上是雙方若不合作則很可能沒有收益),即存在剩余。然而勞動者與雇主的合作是自愿的,不能采取強制性的手段,那么雙方合作的剩余分配比例就成為雙方進行合作的條件,但是分享比例要想讓大家都接受就雙方進行討價還價。在這里雇主與勞動者的“討價還價”除了合作剩余的分享比例外,還包括勞動者與雇主雙方就雙方都關心的生產性條件或環境等進行協商與談判,這實際上就是雙方就合作經濟利益在勞動者與雇主之間進行分配和取得。需要注意的是,勞動者不僅會對分配剩余的多少進行衡量。而且也會與雇主所得進行比較,如果雇主表現得比較摳門,或者雇主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那么勞動者也會感覺不公平,則勞動者就會進行呼吁或者離職。同時,如果雇主比較慷慨讓員工占有剩余的較大部分,即使薪酬與外部市場相比較低,勞動者仍會留在企業中,即表現為忠誠,愿意留在企業與雇主同甘共苦。也就是說,剩余分享比例會影響到勞動者的公平感覺,當勞動者感覺不公平時則會增加選擇流動的可能性。
一、雇主運用“解雇權”對于勞動者的利益剝奪
雇傭契約是在所謂契約自由下的古典契約,此時的雇傭契約是短期的完全合約,雙方存在著名義上的絕對自由債權思想。但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更多的是一種相對的自由。尤其是在雙方力量不一致時,只有具有更大力量的一方才可以有真正的離職自由。在理論上,勞動者享有從事勞動的權利,并且享有他人不妨礙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但是勞動者與雇主的主體地位并不平等,作為現實的交易主體,雙方都會有經濟、政治、出身、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差異。此時雇傭契約具有強制實施契約的性質,是靠“可置信威脅”來實施的,即雇主依靠強制性解雇來占有雙方合作的整個組織組,而勞動者只能獲得保留工資。所以勞動契約是不公正的。
下面通過建立一個簡單的“解雇要挾”博弈模型,從而證明雇主可以通過解雇相要挾來剝奪企業內部勞動者應得的組織租。
假設一個古典企業生產要素為勞動L和資本K,市場所決定的收入為w和r,雙方合作所創造的組織租設為一常量π。同時假設雇主占有“合作租金”的份額為θ,則勞動者占有的份額為1-θ。每一方的總收益為在市場能夠獲得的平均收益再加上由于雙方合作而獲得合作剩余的分享份額,即分享到的合作租金。所以如下式所示,雇主選擇和勞動者合作時所能獲得總收益為:
πk1=r+θπ
勞動者在選擇合作時的總收益為:
πl1=w+(1-θ)π
同時我們假設如果雇主解雇勞動者,雇主可以直接從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同質勞動(即在古典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是同質的),但必須考慮到重置成本,也就是說即使從市場上重新購置相同勞動也需要付出的成本(設為ξ)。此時,雇主的總收益公式可以改寫為:
πk2=r+θπ-ξ
但是顯然由于存在大量的相同勞動者,所以雇主在勞動力市場所獲得勞動力并不具有討價還價能力,雇主可以雙方合作的全部“組織租金”,即θ→1,ξ→0。這和某些現實的勞動市場是相吻合的。雇主的解雇要挾模型如下圖所示。
在P1點,雇主決定對雇員威脅提出解雇與不威脅提出解雇。如果雇主決定不對勞動者提出解雇,那么該博弈立刻結束,從而雇主與勞動者雙方所能獲得的還是原有的收益。但是如果雇主選擇對勞動者提出解雇的威脅,則該討價還價博弈到達P2點,此時,雇主通過提出對勞動者的解雇威脅來單方面要求雇員減薪。勞動者選擇是否接受,如果接受,則雇員不被解雇。如果勞動者拒絕,博弈進入結點P4,由雇主決定是將勞動者解雇還是放棄,博弈結束。
本博弈可以使用逆推法進行求解。在該博弈的最后一個結點由雇主選擇是否對勞動者實行解雇。因為θ≤1總是成立,而且古典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的勞動者之間由于同質性高,因而替代程度很高,所以雇主解雇勞動者后重新雇傭另一勞動者的重置成本趨近于0,因此下式總是成立:
r+π-ξ>r+θπ 對于?坌θ∈[0,1]
r+θπ+S>r+θπ 對于?坌S>0
上面兩式意味著,雇主選擇提出解雇勞動者時總會得到勞動者的響應,即勞動者一般會選擇屈服。這對雇主而言就是選擇“威脅解雇”優于選擇“不威脅解雇”。所以對于雇主而言在任何情況下,其最優選擇總是對勞動者威脅提出解雇,一直到雇主已經得到了所有的合作剩余。
作為勞動者的反應,必須是在考慮雇主提出解雇要挾為前提,他只需要在接受還是拒絕之間做出選擇。由于被解雇走人是可置信的,此時勞動者的選擇就取決于選擇后的收益比較。因為勞動者熟悉雇主的決策原則,所以勞動者知道到雇主一定會采取“威脅解雇要挾”,此時勞動者的選擇只能是“接受”或者“拒絕”。在結點P3上,由于“答應減薪否則走人”屬于可置信威脅,因此勞動者選擇“接受”還是“拒絕”就取決于w+(1-θ)π-S≥w是否成立,如果減薪后留下所獲得的收益大于市場上的可能獲得的工資,勞動者就會接受減薪,從而雇主也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即獲得盡可能多的合作剩余。因此,只要:
(1-θ)π≥S
雇主就能夠通過威脅解雇勞動者從而獲得更多的合作剩余。而雇主的要挾空間為:
S∈[0,(1-θ)π]
由于(1-θ)π是勞動者可以分享到的全部組織租。也就是說,如果勞動者之間的同質性越高,勞動者的供給越是大于雇主的需求,雇主通過威脅解雇而獲得的組織租就越多。在古典的完全競爭市場上,或者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存在大量的剩余農民勞動力的前提下,雇主則有可能獨占全部的勞動者和雇主雙方合作剩余,而作為另一方的勞動者卻只能得到自己的保留工資。
在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由于物質資本的相對于人力資本是稀缺,從而導致了人力的相對過剩,也就是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勞動者相對于資本而言過剩了,使得“資本”不但“雇傭”勞動,而且“支配”勞動。勞動者在市場上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其在企業中的地位也是受到雇主的絕對支配著。因此勞動者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只能獲得一個生存工資,即勞動者被剝奪了。
二、勞動契約的本質特征——第二方執行契約
勞動者與雇主雙方如何心甘情愿地去履行雇傭契約呢?尤其是在勞動者被剝奪的情況下,勞動契約的執行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而建立在古典契約思想上的勞動契約的執行則是認為由于存在第三方強制或者由于契約本身是自我執行的,所以勞動契約是可以執行的。
所謂第三方強制指的是除了勞動者與雇主雙方之外的第三方(例如法院或者中立的第三方)可以強制勞動契約的執行。也就是說,勞動契約可以在法律上能夠被強制執行,而這則需要要求合同本身必須具備嚴格的條件,也就是要成為所謂的完全契約,即契約式完備的,不僅對當下的可能發生的所有情形及其如何履約作了詳細的規定,而且對于將來的契約期限范圍內的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也作了詳細的規定,所以一旦雙方由于履約而發生的任何爭議都可以通過第三方來強制執行。
但是與正式合約不同,大多數勞動契約都是不完整的和不明確的。勞動契約的不明確性通常是在下列意義上而言的:首先雙方都只具有有限理性。也就由于勞動契約的是不完整和不明確的,雙方中的一方或雙方都有可能從欺騙對方,即以某種方式撕毀合約的行為中獲益;或者勞動契約締約一方利用力量的不對稱獲得額外利益。在上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雇主由于存在解雇權,從而可以對勞動者進行利益剝奪,因此勞動契約的實施就存在著難以想象的困難。即使在國家層面上制定了許多的關于勞動契約的法律法規,在現實中仍是難以將勞動契約全面規制,所以在作為第三方仍是難以完全了解勞動契約的具體細節。
由于勞動契約的不完全性,第三方不可能強制執行,所以許多文獻認為勞動契約之所以能夠執行是由于勞動契約是自我執行契約。也就是說由于在勞動力市場上有無數的買主和買主,任何簽訂契約的雙方在執行契約的過程中不僅僅要考慮在本次執行的收益和成本,而且必須考慮到本身的行為在勞動力市場上造成的影響。若是雇主喜歡解雇勞動者,或者勞動者總是比較隨意地辭職,則會在勞動力市場上形成不好的聲譽,從而導致雇主在以后的雇用中必須付出更高的工資水平才能獲得同等資格的勞動者,而勞動者在以后的求職中也只能獲得更低的工資水平。所以雇主和勞動者都不會輕易地進行解雇和辭職,勞動契約就能獲得很好的執行。但是如果外部勞動力市場的運行出現異常或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雇主或勞動者不需要建立所謂的“好名聲”,例如在我國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始終存在著勞動力的供給過剩,即使雇主隨意解雇勞動者也照樣可以從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勞動力補充,因此就存在隨意解雇勞動者或者只是與勞動者簽訂短期勞動合同的現象。所以,當外部出現由于解雇而獲得很大的收益或者成本微不足道時勞動契約是不能自我執行的。
因此,勞動契約的執行都不能完全依賴于第三方執行或者契約的自我執行。勞動契約實際上是第二方執行契約,勞動契約的執行是通過勞動者單方面的離職來保證的。
勞動契約是勞動者與雇主雙方進行合作協商的產物,雙方合作的基礎是合作能夠產生剩余,但是由于雇主的解雇權的存在以及雇主本身所具有的優越條件,勞動者必須團結起來才能獲得與雇主抗衡的力量與權利,從而再通過立法層面上的權利賦予來獲得自己的相應的份額。然而如今需要勞動者更趨向于原子化,一個是由于經貿全球化導致的各國的競爭導致勞動者的勞動標準實際上是降低的,而且資本的全球化使得勞動者更加難以團結起來。其次是現在勞動履行的場所有以成年男性勞動者為主的工場制轉為場所分散的多樣化履行。從而使得勞動關系的特征由以勞動者團結為主的集體抗爭走向由勞動者單個面對雇主的原子化抗爭。為了保證獲得勞動契約的公平份額以及保證勞動契約的履行,勞動者采取了以“消極互惠”為主要的抗爭形式。
互惠(reciprocity)的概念是由德國學者圖恩瓦(Thurnwald)首先提出來的。其是指建立在給予、接受、回報這三重義務基礎上的兩集團之間、兩個人或個人與集團之間的相互扶助關系,其特征是不借助于現代社會中的金錢作為交換媒介{1}。互惠意味著善意回應善意,惡意回報惡意。例如人們會回贈禮物或采取報復,甚至在與素不相識的人打交道時亦如此,即使這對他們來說是要付出代價的。消極互惠則是指的是報復性互惠。在勞動者與雇主的雙方合作剩余分享中,雇主利用自身的優勢占有的剩余愈多,勞動者認為自身受到的傷害就越大,從而勞動者就越會采取報復性行動。在這里就表現為勞動者的離職,勞動者知道離職會給自己造成損害,但是也會給雇主造成損害,所以勞動者仍會采取離職行為報復雇主。
因此勞動者在采取離職行為時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公平。公平(fairness)是經濟學、法律學和倫理學的重要范疇。作為一個倫理學范疇,公平同公道、公正、正義等范疇有著相近的含義。含有從公正的角度出發平等地善待每一個與之相關的對象的意義{2}。在本研究中公平是勞動者的一種感覺,如果勞動者感到公平,那么勞動者就會履行與雇主的勞動契約。而如果勞動者感到不公平,就會出現心理上的緊張、不安,從而使勞動者采取行為以消除或減輕這種心理緊張狀態。一般勞動者采取的措施有呼吁、申訴。如果上述手段都不奏效,勞動者仍然感覺不公平,那么勞動者就會選擇退出{3},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辭職。
三、納入公平的勞動者討價還價博弈模型
根據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理論,勞動者與雇主的勞動契約達成受到外部環境以及自身討價還價過程的影響,因此對于過程的考察將是研究的重點內容。我們可以借助于現代博弈論科學的發展以及其研究成果,將生活在現實中的勞動者與雇主之間的談判行為簡化為動態博弈過程,從而可以構建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談判博弈分析的基礎框架。
根據前面的論述,如果勞動者與雇主通過討價還價談判博弈達成“合作解”,那么雙方就可以簽訂勞動契約進行合作;如果雙方的討價還價失敗,那么就意味著討價還價破裂,表現為勞動者的流動,即從一個雇主轉向另一個雇主。在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談判過程中,雙方能夠達成的均衡結果應該都是每一方都能接受的,一般來講,勞動者與雇主雙方每一方都能夠接受的分享數值至少等于各自的風險值的大小,但是雙方進行合作肯定不能只得到和沒有合作之前一樣的收入,否則合作就是沒有必要的。因此,勞動者和雇主的討價還價談判博弈解,必然是勞動者與雇主每一方所能接受的分配值是風險值加上合作剩余的平均或分配值。所以勞動者和雇主之間的博弈是一種變和博弈,如圖2所示。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任何協議中,每個談判者都至少獲得風險值,否則合作就無利可圖。討價還價問題的一個合作解是要每個談判者獲得風險值外加合作剩余的一個平等份額。所以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談判博弈過程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勞動者和雇主各自確定自己的風險值,也就是所謂的談判底線,低于這個數值談判就會直接破裂;第二個階段是明確雙方進行合作的話能夠獲得的合作剩余;第三個階段就是勞動者與雇主雙方進行討價還價談判,從而確定各自所能獲得分享比例。
為了分析談判的邏輯,我們首先考察不合作的后果,假設雙方合作失敗,他們將各自達到自己的某種水平的福利,用人單位持有資產或者將資產用于其它用途的投資,從而能給他帶來一定的收益。對于勞動者來講如果假設他不能在該用人單位工作,那么至少他有可能獲得一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平均工資,如果不能尋找到其他工資,則可能獲得一個失業補貼,這對他來講是合作失敗的價值。因而在不合作解中,雙方的利益我們稱之為風險值。與此相反,合作解是指雙方進過討價還價獲得一個雙方都接受的工資水平,通過合作雙方都擁有了合作剩余的一部分,即雙方都獲得一個超過風險值的部分。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和傳統的完全理性人不同,勞動者的效用不僅僅取決于工資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說不僅僅取決于雙方討價還價的具體數額的多少,還取決于勞動者的工資數量占整個合作剩余的份額大小,即在勞動者的效用中引入了公平的要素。通過我們建立的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博弈結果意味著首先雇主與勞動者按照自身的討價還價能力分割雙方的合作剩余。如果該勞動者的資產對于其他生產要素是唯一的,且是勞動力市場上是難以替代的,即其他生產要素對于該生產要素是依賴的(專有性),則該勞動者就可能獲得的合作剩余的全部。所以合作剩余的分享比例是不確定的,而分享比例則可以看出雇主對于勞動者的友善程度,極低的比例意味著過度的盤剝,是一種惡意的體現,較高的分享比例則反映出雇主對于勞動者的友善。
費厄和斯科米德特(Fehr and Sohmidt,1999),提出了一個關于“規避不均等”(或稱為嫉妒和“內疚”)的模型,在其中參與者不僅關心他們自己的收益,還關心他們的收益與其他人收益之間的差別。參與者i對社會分配X≡{x1,x2,…,xn}的效用可以這樣描述:
Ui(X)=xi-■■max(xk-xi,0)-■■max(xi-xk,0)
這里假定0≤βi<1并且βi≤αi。參與者的公平感覺來源于他們的嫉妒和內疚:他們既不愿意獲得比別人低的分配(這時表現為嫉妒,以衡量其程度),但也不愿意(程度稍輕一些)獲得比另一方高的分配(這時參與者表現為內疚,以d1衡量其程度),費厄和斯科米德特運用標準的均衡概念得出了能用來解釋實驗結果的嫉妒和內疚程度的值。而拉賓(Rabin,1993){4}的關于“公平均衡”的觀點則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即現實生活照的人們都會對那些對自己友善的人友善,但是對待那些傷害過自己的人則持有敵視態度。
據此我們建立了在勞動者與雇主討價還價模型中的勞動者的效用函數:
MaxUl(w)=Max(w-amax(π-w,0))
St.w≥wr
其中Ul(w)為勞動者在獲得工資為w時的效用,w為勞動者與雇主討價還價后的所得,π為雇主所得,wr為勞動者的保留工資。
其中勞動者的效用水平不僅來源于與雇主討價還價所能獲得的工資收入,還與勞動者與雇主雙方進行討價還價的相互分配份額有關。由第一節的分析可知,勞動者由于處于天然劣勢,會被雇主利用解雇權進行壓榨,因此勞動者參與者的公平感覺主要來源于他們的嫉妒,以大小來衡量其程度。
結合上面的圖(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談判模型)可以看出,影響勞動者與雇主談判破裂的因素主要是勞動者的保留工資、勞動者所得與雇主所得的差距以及勞動者本身的嫉妒程度,其中后面兩個可以認為是勞動者的公平程度的體現。這就導致了勞動者是否流動不僅取決于實際的工資水平,還會取決于勞動者的心理感覺,即公平。
所以在這里勞動者對于勞動者與雇主之間就合作剩余進行的分割比例是十分看重的,直接決定了勞動者是否感到公平。如果勞動者認為分享比例是公平的,便會感到受到了公平待遇,因而心理平衡、心情舒暢、工作努力,勞動者會選擇留在企業。如果認為分享比例是不公平的,便會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產生怨恨情緒,從而會影響到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而且分享比例與勞動者自己認為的標準相差越多、差距越大,勞動者的不公平感覺就會越強烈。這時勞動者可能產生挫折感,甚至是義憤感和仇恨心理,從而產生破壞心理。如果條件允許,勞動者離職的可能性無疑就會增加。
四、勞動者離職決策的影響因素
很久以來,在勞資關系和經濟學范疇內,除了研究雇主和勞動者的主體性和關系之外,雇傭環境的研究也是一個重要課題。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博弈除了本身是自成系統外,還和系統之外的社會因素有關系,勞動者和雇主的契約談判除了受到談判本身(如破裂風險、保留工資等)的影響外,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其中一些是由于勞動者本身的特點所決定,例如勞動者的自身公平感等。
1.市場競爭。市場競爭其實就是雇主之間的競爭或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雇主競爭是指雇主為了獲得或留住勞動者而采取的競價策略,例如在雇主勞動力需求量遠遠大于供給量的情況下,雇主會采取向上的競價策略,這導致了市場上的工資率水平上升與勞動者流動率的下降,反之則會導致市場工資率水平的下降,但是對于勞動者流動率的影響則是未定,如果整個市場上的工資水平是一致的,則勞動者的流動率會保持不變,因為流動并不會是的勞動者的福利水平增加;如果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水平是離散的,而會導致勞動者增加流動從而獲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說,前者是后者運行的結果。流動體現的是一種過程變動,是雙方市場力量相互平衡的一種過程。所以勞動力市場競爭的本質是通過勞動要素的流動來達到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因此可以看出市場工資的離散度越高,則勞動者的流動就會越頻繁。
但是在上述的分析中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只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勞動者的流動。其實其他因素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勞動力的流動,譬如勞動力供給彈性的變化、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全程度、宏觀經濟形勢、產品市場以及雇主本身的策略等均可能影響到勞動力的流動。
而雇主作為勞動者的使用者,到底是采取專制還是霸權主要是為了保證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因此在勞動者流動比較頻繁時雇主會采取措施限制勞動者的流動,而在勞動者的流動率比較低時,為了促進勞動者之間的相互競爭和勞動要素的優勝劣汰會采取措施促進勞動者的流動。
2.政府干預。凡是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均為政府,“政府就是國家的權威性的表現形式”。作為雇主與勞動者之外的第三方,政府發揮著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1)政府有權制定和修改各項法律制度。所以政府的對于社會價值的判斷和自己的意志都會貫穿于各項法律制度,也為勞動者與雇主之間的討價還價談判奠定了基本框架。(2)政府控制了許多公共部門,例如提供健康、教育、消防等服務的政府機構,還有通信、交通、電力等公用事業單位,以及航空、鋼鐵、銀行等行業中的國有企業。這樣政府就換成了社會上的最大的雇主,政府與勞動者之間的討價還價模式也就成為私人部門勞動關系的“樣本”。(3)政府可以采取的方針、政策和行為{5}。所以政府是雇主和勞動者雙方競爭中的調節者和仲裁者、立法者、市場管理者、雇主{6}。政府通過勞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來干預、調整雇主和勞動者之間的討價還價博弈行為。而政府對勞動者與雇主討價還價的調控和調解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公權介入的國家干預來保障勞權,以實現勞動關系的平衡和穩定。
3.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即其體力和智力的恢復、更新和發展。勞動力再生產既包括現在一代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不斷恢復、更新和增強,又包括新一代勞動力的不斷教育、培訓和補充。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勞動者必須在雙重意義上是自由的人。第一,勞動者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能夠自由的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既沒有生產資料又沒有生活資料,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別無生路。前者意味著勞動者不存在人身依附關系,后者意味著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自由得一無所有。因喪失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現代無產者。亦稱工資勞動者。他們一方面具有人身的自由,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勞動者本身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他所能擁有的只不過自己的勞動力,為了獲得生活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勞動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來出賣,在資本的支配下,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資本家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勞動者處于被剝削和被奴役的地位。勞動者雖然可以把勞動力賣給這個或那個資本家,但是為了要活下去,卻離不開整個資本家階級,好像有一根無形的鎖鏈,把雇傭勞動者鎖在資產階級身邊,使雇傭勞動者成為替資產階級生產剩余價值的雇傭奴隸。這就是雇傭勞動者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
而由森{7}所定義的現在又被廣泛認可的自由的概念,既包括法治意義的自由,也包括生活上的自由,即人們能夠過自己愿意的那種生活。很顯然,能有尊嚴的生存是其基本假設,并且有尊嚴的死亡亦是一個人的自由。
現在我們回來看馬克思所定義的雙重意義上的自由的勞動者,很顯然,第二個自由根本就不是所謂的自由,那是不得已而為之,因其在要生存的前提下別無選擇,即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自由得一無所有已經不是所謂的自由,因此時所謂的自由已經毫無自由的意義。
因此現代勞動力的再生產國家更多地參與進來,例如國家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就業促進政策等,這些無不是在給予勞動者擺脫對于單一雇主的依附。從而保證勞動者既有給自己干活的自由又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別人以掙取生活資料的自由,即他們有兩個選擇(基于生存的基本假設之上)。
應該說,只要存在商品經濟,存在市場,勞動者如有勞動能力,并且又想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通過勞動者自由流動使得勞動者享有了“實質的自由”。
所以勞動者再生產體現了勞動者對于雇主的依附程度,勞動者對于單個雇主的依賴大小決定了勞動者在討價還價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大小,而勞動者的流動正是勞動者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的一種有效手段。
五、小結
勞動者與雇主經過討價還價后會達成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條款就形成了勞動契約,而勞動契約是動態的,即勞動契約是由無數的短期勞動契約構成的長期契約。換句話講,勞動者可以在一個企業內部工作很長時間,但是在工作期間勞動者仍需要和雇主就勞動條件進行討價還價談判,談判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勞動契約的表現形式可以書面的,也可以是口頭的,甚至是心理的。因此勞動者與雇主的討價還價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勞動者與雇主雙方討價還價破裂的后果就表現為勞動者的離職。
勞動契約與其他契約特殊性不僅勞動契約是動態的,而且勞動契約的談判雙方是不平衡的,由于雇主本身的力量遠遠大于勞動者的力量,尤其是雇主所具有的解雇權對于勞動者而言更是一把高懸于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勞動者不得不接受雇主的苛刻要求,即勞動者分享的企業剩余會很低或者沒有。也就是說,勞動者被雇主剝削了,這會加重勞動者的不公平感。
勞動者的公平感不僅和勞動者獲得的工資水平絕對高低有關系,而且和勞動者所得與雇主所得的比較有關系。勞動者本身是一個理性的社會人,不僅會答應對自己有利的條款,而且還會進行比較,即拿自己的所得與雇主的進行比較,如果分享比例差距過大,勞動者即使獲得一個比較高的工資仍會感覺不公平。一般來講,勞動者感覺不公平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當勞動者分享合作剩余的比例明顯過低時,即使勞動者獲得的是效率工資,勞動者仍會感到不公平。在另外一種情境中,如果限制勞動者的討價還價權利,使得勞動者只能答應或不答應,即勞動者選入最后通牒的狀況,也會使得勞動者感受到不公平感,會促使勞動者加速離職。
注釋:
{1}李鵬程,鄒廣文,羅紅光,李紅等.當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詞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朱貽庭,崔宜明.倫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3}〔美〕阿爾伯特·O·赫希曼 著,盧昌崇 譯.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4}Rahin, Matthew. 1993.Incorporating fairnesst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3,1281—1302.
{5}Michael Pool. Industai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Patters of National Diversity,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99.
{6}Mike Leat. Exploring Employee Relations, Butterwprth-Heinemann, 2001.
{7}阿馬蒂亞·森著,任賾,于真譯.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4,32,175
(作者單位: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北京 100029)
[作者簡介:田輝(1974—),男,漢族,山東省肥城市人,經濟學博士,勞動保障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
(責編: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