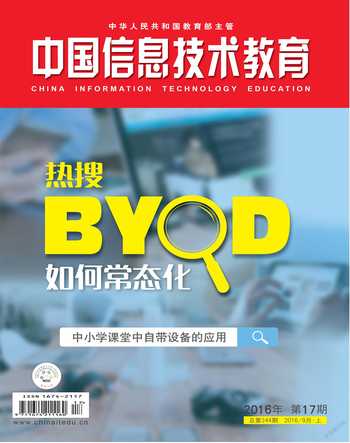數據生產融合數據消費
2016-09-10 07:22:44魏忠
中國信息技術教育
2016年17期
魏忠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做了七件事情: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建立馳道、巡游六國、實現郡縣制、修建長城,而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統治信息化的手段。秦始皇的信息化建設,奠定了中國后來的1000年盛世基礎,也帶來落后的病根。按照信息發生方式研究,秦始皇的信息化建設,建立了極權秩序的開端,只是那個時代這種制度還不成熟。秦始皇采用的七項信息化手段,實現了中央命令上情下達,但信息還是單向的,即秦始皇讓全國人民知道了中央政府,而秦始皇卻不知道全國人民怎么想的。也因此,幾個極為關鍵人物——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羽(彼可取而代之),劉邦(大丈夫當如是)及趙高(陽奉陰違),都是秦始皇單向的極權秩序無法掌控的。
不僅如此,秦始皇的第七項信息化手段——修建長城,不僅沒有幫助建立極權秩序,反而多次成為游牧民族的超級信息體,一直影響著中原王朝。事實上,長城并不是秦始皇所修建,只是秦始皇將數段長城連成一片,而就是這“連成一片”,讓中原王朝從此數度遭殃。按其本意,長城的烽火臺、烽火、驛站、馳道構成的信息化手段是確保秦始皇萬世基業長治久安的策略,然而,正是這連成一片的長城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按照地質學家和農學家計算,北部游牧民族在每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的時候,都以放牧為生,中原的農耕百姓與游牧民族相安無事,而每當年降水量低于400毫米的時候,草原退化,強悍的游牧民族就會過來搶,而當降水量恢復之后,游牧民族又會回到草原,周而復始。……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2021年8期)2021-09-10 17:59:45
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2021年4期)2021-06-06 04:36:26
甘肅教育(2020年18期)2020-10-28 09:06:02
活力(2019年21期)2019-04-01 12:16:40
中華手工(2017年2期)2017-06-06 23:00:31
中外會展(2014年4期)2014-11-27 07:46:46
中國衛生(2014年1期)2014-11-12 13:16:34
江蘇年鑒(2014年0期)2014-03-11 17:09:40
建筑創作(2001年3期)2001-08-22 18:48:14
祝您健康(1987年3期)1987-12-30 0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