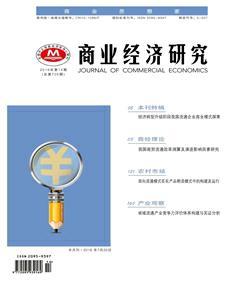區(qū)域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分析
聶喜玲


內容摘要:本文選擇東中西部三大代表性城市經(jīng)濟圈,比較分析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研究發(fā)現(xiàn),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總體較為積極,但存在一定的結構失衡,食品、居住等基本生存型公共產品的消費效應明顯高于醫(yī)療保健、文化教育娛樂等的消費效應。同時,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存在區(qū)域差異,其中成渝經(jīng)濟圈農村基本公共產品供給帶來的消費效應明顯較高,但對于文化娛樂等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明顯低于長三角經(jīng)濟圈和長江中游經(jīng)濟圈。
關鍵詞:農村 公共產品供給 消費效應 城市經(jīng)濟圈
問題的提出
農村公共產品就是農村地區(qū)為了滿足農村經(jīng)濟發(fā)展和農民生活需求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公共性產品或服務。農村公共產品包括道路、電網(wǎng)、水利灌溉系統(tǒng)、生態(tài)林網(wǎng)等基礎設施以及文化驛站、教育場所、醫(yī)療衛(wèi)生站等公共服務點等等。通過公共產品的不斷供給,可以為農民的生產生活提供更多的發(fā)展空間,能夠優(yōu)化農村消費環(huán)境、拓寬消費領域、提升農民消費層次,因而可以說,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可以形成一定的消費效應。
目前,我國的消費市場呈現(xiàn)快速增長態(tài)勢,但總體消費需求仍然不足,農村地區(qū)消費難以充分啟動,無論對農村自身以及所在城市的發(fā)展還是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等都有一定不利影響。“新常態(tài)”下,消費驅動型發(fā)展模式不斷成為主流,擴大內需必將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而農村地區(qū)必然是未來的新戰(zhàn)場。“十三五”時期,我國也將推進供給側改革,公共產品供給將成為重要發(fā)力點。通過公共產品不斷供給,為消費市場提供更大發(fā)展空間。那么,我國農村地區(qū)公共產品供給產生多大的消費效應呢?不同區(qū)域這種消費效應存在怎樣的異同?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在選擇樣本時,為了縮小空間以提高精確性,同時盡量涵蓋我國重點發(fā)展區(qū)域,并兼顧局部城市地區(qū)的抱團式、一體化發(fā)展的鮮明特征,在東中西三大區(qū)域分別選擇相應的城市經(jīng)濟圈進行研究。
模型及數(shù)據(jù)說明
(一)模型概述
(二)變量及數(shù)據(jù)說明
為了對東中西部城市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進行比較研究,本文鑒于我國三大區(qū)域城市經(jīng)濟圈的代表性,東部地區(qū)選擇長三角經(jīng)濟圈,中部地區(qū)選擇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西部地區(qū)選擇成渝經(jīng)濟圈。對于長三角經(jīng)濟圈,雖然國務院2014年批準的《國務院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jīng)濟帶發(fā)展的指導意見》指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jīng)濟圈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但是安徽屬于中部后發(fā)崛起的地區(qū),一部分城市仍未充分崛起并融入長三角,因此本文選擇的城市包括上海市、江浙兩省所有城市,以及安徽的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中部城市經(jīng)濟圈實際上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由武漢城市圈、襄荊宜城市帶、長株潭城市圈這3個城市群構成。其中武漢城市圈包括武漢、黃石、黃岡、鄂州、孝感、咸寧、仙桃、天門、潛江;襄荊宜城市帶包括襄陽、宜昌、荊州、荊門;長株潭城市圈包括長沙、岳陽、常德、益陽、株洲、湘潭、衡陽、婁底。西部成渝經(jīng)濟圈則包括四川省的成都、綿陽、德陽、樂山、眉山、遂寧、內江、南充、資陽、自貢、宜賓、廣安、達州13個市以及重慶市。
本文主要研究區(qū)域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因此需要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等變量進行定義。對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由于統(tǒng)計年鑒等相對統(tǒng)計資料中均沒有直接提供指標數(shù)據(jù),因此本文參考部分學者的做法,采用政府對地方“三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進行衡量。具體地,對于每個城市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指標即為城市圈內所有城市的政府“三農”財政支出總額與所有城市財政支出總額的比值。對于農村居民消費指標,本文按照消費產品類型分為8類,分別為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和服務、醫(y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交通通信設備和服務、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和服務、其他產品和服務,其余消費支出大部分為私人屬性產品,本文略去不計。除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農村居民消費兩個指標外,根據(jù)式(7),還需定義農村居民收入指標,具體采用各個城市經(jīng)濟圈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表示。
本文選取的時間序列均為2005-2014年,指標數(shù)據(jù)來源于對應城市的統(tǒng)計年鑒、統(tǒng)計公報,以及國研網(wǎng)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庫。
檢驗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時間序列與城市橫截面組成的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這種模型包括固定效應、隨機效應、混合效應三種類型。為選擇最佳類型,首先對三種類型分別進行回歸,根據(jù)結果選擇類型。如果Hausman檢驗值滿足在10%以內的顯著性水平顯著,那么就拒絕隨機效應,反之則選擇隨機效應。若拒絕隨機效應,那么觀察LM檢驗值,如果LM值也滿足在10%以內的顯著性水平顯著,那么就接受固定效應,反之則選擇混合效應。東中西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的回歸結果分別如表1、表2、表3所示。
(一)總體分析
綜合東、中、西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的回歸結果可以發(fā)現(xiàn),所有回歸的結果都比較理想,大部分變量都滿足一定的顯著性水平,模型擬合程度也都較高,這充分說明選擇的模型及估計方法是比較可行的。
綜合東、中、西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的回歸系數(shù)可以發(fā)現(xiàn),總體上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民消費支出基本上都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對農民消費支出的影響結構基本相似。其中,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食品、居住、交通通信設備和服務這3種消費支出的邊際影響均比較高。從食品支出的系數(shù)最高這一結果可以看出,目前無論是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城市區(qū)域,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水平仍然不夠理想,從側面反映了當前我國城市經(jīng)濟圈內部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依然顯著,農民的生活消費主要仍體現(xiàn)在食品消費方面,對于高端消費的支出相對缺乏。從居住消費支出的系數(shù)最高這一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城市的農村居民在解決基本溫飽問題以后,居住便成為農民的第二大消費支出,這也表現(xiàn)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具有的非公共特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交通通信設備和服務消費支出的邊際貢獻排名第三位,這也體現(xiàn)了農村居民對于交通通信消費的渴望,尤其是近年來休閑經(jīng)濟不斷成為主流,旅游業(yè)不斷興起,農民對交通的消費支出不斷增加;同時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不斷盛行,農民對手機等通信設備的需求也越來越高。
(二)細分比較分析
而從細分比較來看,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食品、居住,公共產品供給帶來的邊際消費貢獻在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存在明顯差異。其中,成渝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帶來的食品和居住的邊際消費貢獻明顯高于長三角城市經(jīng)濟圈和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而且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這一邊際消費貢獻也高于長三角經(jīng)濟圈。系數(shù)結果中,成渝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食品消費的貢獻系數(shù)為0.405,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食品消費的貢獻系數(shù)為0.299,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長三角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食品消費的貢獻系數(shù)雖然也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但數(shù)值僅為0.217。成渝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居住消費的貢獻系數(shù)為0.218,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而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和長三角經(jīng)濟圈該系數(shù)分別為0.187和0.159。從農村食品消費需求來看,西部地區(qū)由于經(jīng)濟發(fā)展明顯滯后,許多農村地區(qū)居民的消費仍大部分集中在基本食品消費層面,而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較快,尤其是長三角經(jīng)濟圈經(jīng)濟發(fā)展遙遙領先,因而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已不局限在食品方面,更多地在與其他附屬產品消費上。從農村居住消費需求來看,西部地區(qū)農村居民對住房的消費意愿較高,這是由于不同地區(qū)居住的觀念存在差異,西部地區(qū)農民無論家庭條件如何,在住房擇向上更多地關注房屋美觀、寬敞程度,同時也受到當?shù)厥杖胨较拗疲蚨伯a品供給的增多,更能激發(fā)當?shù)剞r民購房居住。
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交通通信設備和服務的消費貢獻程度也存在明顯差異,表現(xiàn)為成渝經(jīng)濟圈最高,長三角經(jīng)濟圈次之,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最低。首先,西部地區(qū)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成渝經(jīng)濟圈農民收入明顯低于長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而收入的低水平會對農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消費產生一定限制;其次,長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經(jīng)濟圈的交通運輸和通信設施明顯比西部成渝經(jīng)濟圈完善,而如果交通通信設施不完善,那么農村共享這些設施也將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夠很大程度緩解這些矛盾。
對醫(y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消費貢獻表現(xiàn)為長江中游、成渝兩個城市經(jīng)濟圈大致相當,且高于長三角經(jīng)濟圈。對衣著的邊際消費貢獻,三個城市經(jīng)濟圈的比較結果與醫(y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基本一致,中西部兩個城市經(jīng)濟圈高于長三角經(jīng)濟圈。這些結果都表明了中西部城市經(jīng)濟圈農村居民對于醫(y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衣著等的消費渴望性較高,公共產品帶來的邊際消費貢獻也較高。但公共產品供給對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和服務的影響結果則截然相反,長三角經(jīng)濟圈的系數(shù)明顯高于另兩個城市經(jīng)濟圈,且成渝經(jīng)濟圈的系數(shù)尤其之低。可見,我國西部地區(qū)城市內部的農村居民對文化娛樂的消費追求欲望仍沒有被激發(fā)出來,更多地還是在于維持生活的基本消費上。
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本結論概括如下:第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基本能帶來正向的消費效應,對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市場的拓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第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在東中西部的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都存在結構失衡,食品、居住、交通通信等基本生存型公共產品的消費效應明顯較高,而對于醫(yī)療保健產品和服務、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和服務等的消費需求意愿則與現(xiàn)狀供給之間存在一定的缺口。第三,三大城市經(jīng)濟圈不同公共產品供給帶來的消費效應也都存在區(qū)域差異,西部成渝經(jīng)濟圈農村基本公共產品供給帶來的消費效應明顯較高,但對于文化娛樂等公共產品供給的消費效應偏低。
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建立東中西部農村公共產品均衡供給的機制,加大對西部地區(qū)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并完善提升相關服務能力 。第二,建立健農村公共產品差異化需求機制,有效緩解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及實際需求之間的結構失衡。第三,積極鼓勵農民參與和獻計獻策,促進公共產品的供給更加符合農民需求,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
參考文獻:
1.周久妹.公共品供給結構偏向對居民消費影響實證研究[J].商業(yè)經(jīng)濟研究,2015(11)
2.張曉慧,梁海兵.基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農村公共品供給實證分析[J].農業(yè)技術經(jīng)濟,2010(9)
3.Linda M. Y & Jill E. H. Vertical Linkages in Agri-Food Supply Chains: Changing Roles for Producers,Commodity Groups,and Government Policy[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2, 24(2)
4.王君萍,王玉龍.西北地區(qū)新農村建設投資對擴大農村消費需求的貢獻率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區(qū)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證分析[J].軟科學,2011(10)
5.鄧宗兵,楚圓圓,劉夏然,王炬.農村公共品供給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研究[J].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5)
6.Jarmin R S,.Klimek S. D & Miranda J.. The Evolution of Retail Markets in Metropolitan, Micropolitan and Rural Regions[J]. U.S.Census Bureau, 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