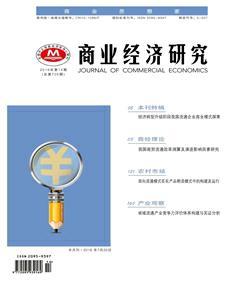信貸政策、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與資本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
彭璐瑤



內(nèi)容摘要:本文立足于中國特有的環(huán)境,以2010-2014年557家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實(shí)證檢驗(yàn)了信貸政策、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以及兩者共同對資本結(jié)構(gòu)的影響。結(jié)果表明,信貸政策作為宏觀層面因素對資本結(jié)構(gòu)具有顯著影響,當(dāng)存貸利差增大時(shí),企業(yè)負(fù)債水平會相應(yīng)提高。在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方面,國有企業(yè)資產(chǎn)負(fù)債率明顯高于非國有企業(yè)。進(jìn)一步地,當(dāng)信貸政策發(fā)生變化,非國有企業(yè)更加敏感。
關(guān)鍵詞:資本結(jié)構(gòu) 信貸政策 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
引言
資本結(jié)構(gòu)影響企業(yè)選擇,企業(yè)選擇影響企業(yè)價(jià)值,因此資本結(jié)構(gòu)歷來都是研究的重點(diǎn),是融資決策的核心問題。什么決定了資本結(jié)構(gòu)、影響因素有哪些,理論界和實(shí)務(wù)界都產(chǎn)生了大量的學(xué)術(shù)成果。利率市場化后,不同商業(yè)銀行的貸款政策不完全相同,給企業(yè)提供了選擇的機(jī)會,由此帶來不同影響。近年來,關(guān)于信貸政策與資本結(jié)構(gòu)的研究中,大多數(shù)都證明信貸與資本結(jié)構(gòu)存在明顯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根據(jù)張?zhí)⒅x赤、高芳(2007)的研究,利率是決定性的因素,利率變動對于其調(diào)整有顯著影響,其中短期利率與負(fù)債比率顯著正相關(guān),而長期利率與負(fù)債比率顯著負(fù)相關(guān);伍中信、張婭及張雯(2013)在研究中指出,在控制資本結(jié)構(gòu)需求因素的基礎(chǔ)上,信貸供給會產(chǎn)生顯著的同向影響,其中對流動負(fù)債的影響顯著大于長期負(fù)債;唐國正、劉力(2005)從理論上分析了債務(wù)融資相對于股權(quán)融資的優(yōu)勢,說明利率管制導(dǎo)致的利率扭曲對資本結(jié)構(gòu)的選擇具有重要影響;曾海艦和蘇冬蔚(2010)也發(fā)現(xiàn),資本市場供給方面的因素對于資本結(jié)構(gòu)具有重要且顯著的影響。
從已有文獻(xiàn)看,國內(nèi)外對于信貸與資本結(jié)構(gòu)的研究不少,但研究的立足點(diǎn)主要集中在信貸需求方面,對于信貸供給等宏觀政策方面的研究較為缺乏,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的企業(yè)對信貸政策的敏感性研究也較為稀缺。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以2010-2014年國內(nèi)A股上市公司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兼顧數(shù)據(jù)的觀測性和獲得性,選取了能夠連續(xù)觀察的信貸利差作為解釋變量來考察對資本結(jié)構(gòu)的影響,在此基礎(chǔ)上,加入了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虛擬變量以豐富研究。
理論分析與假設(shè)
權(quán)衡理論強(qiáng)調(diào)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在權(quán)衡利息的抵稅收益與財(cái)務(wù)拮據(jù)成本的基礎(chǔ)上,選擇實(shí)現(xiàn)企業(yè)價(jià)值最大化的資本結(jié)構(gòu)。既然利息有抵稅效應(yīng),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資者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可分配收入,因此舉債會降低企業(yè)稅負(fù),降低資本成本,但同時(shí),負(fù)債的增加也會帶來各種成本的增加,比如財(cái)務(wù)拮據(jù)成本和代理成本等。穆爭社(2004)在研究中指出,商業(yè)銀行是連接中央銀行和融資企業(yè)的橋梁,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工具改變商業(yè)銀行的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財(cái)富總量和信用供給量,以此調(diào)節(jié)信貸規(guī)模。但需要注意,商業(yè)銀行是具有獨(dú)立利益的經(jīng)濟(jì)實(shí)體,當(dāng)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時(shí),在多大程度上進(jìn)行調(diào)整,取決于商業(yè)銀行實(shí)現(xiàn)自身利益的程度。因此,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影響,商業(yè)銀行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商業(yè)銀行的利益目標(biāo)并非由單一的利率因素決定的時(shí)候。在控制需求的前提下,從資本結(jié)構(gòu)的供給看,當(dāng)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的利差擴(kuò)大,由于信貸業(yè)務(wù)利潤增加,銀行放貸的積極性會顯著提高,由此帶來企業(yè)負(fù)債水平提高;反之,隨著銀行存貸利差縮小,銀行由于獲利減少而積極性下降,企業(yè)負(fù)債水平下降。由此,提出假設(shè):
假說1:銀行存貸利差與企業(yè)負(fù)債水平正相關(guān),即銀行存貸利差增大,企業(yè)負(fù)債水平提高。
由于在我國政府干預(yù)現(xiàn)象較嚴(yán)重,加之國有企業(yè)與國有銀行之間天然的契約關(guān)系,使得國有企業(yè)相比于非國有企業(yè),更容易從四大商業(yè)銀行或其他國有金融機(jī)構(gòu)獲得貸款。國有銀行的獨(dú)立性明顯減弱,即使國有企業(yè)達(dá)不到貸款條件,國有銀行也會迫于壓力提供貸款。另一方面,由于兩權(quán)分離,國有企業(yè)的所有者為國家全體公民,但我國公民監(jiān)督意識薄弱并且市場機(jī)制不健全,因此企業(yè)缺乏一個(gè)人格化的代表來對經(jīng)營管理者進(jìn)行有效監(jiān)督,道德風(fēng)險(xiǎn)明顯提高,企業(yè)價(jià)值最大化可能會被管理者利益最大化取代,國有企業(yè)的管理者可能會為私人目的舉債投資凈現(xiàn)值為零甚至為負(fù)的項(xiàng)目。肖作平(2010)指出,在我國,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yè)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實(shí)質(zhì)是同一所有者的內(nèi)部借貸,是以低效率的非市場性債權(quán)債務(wù)契約關(guān)系和國有產(chǎn)權(quán)制度超經(jīng)濟(jì)強(qiáng)制下信貸政治化效應(yīng)為典型特征。由此,提出假設(shè):
假說2:國有企業(yè)的資產(chǎn)負(fù)債率會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yè)。
預(yù)算軟約束是指,當(dāng)一個(gè)預(yù)算約束體的支出超過了收益時(shí),預(yù)算約束體不僅沒有被破產(chǎn)清算,反而被支持體救助繼續(xù)存活。在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期的我國,這種現(xiàn)象較為嚴(yán)重。國有企業(yè)由于行政色彩和歷史原因承擔(dān)了大量的政策性負(fù)擔(dān),當(dāng)企業(yè)出現(xiàn)虧損時(shí),政府會出面進(jìn)行救助。正是由于預(yù)算軟約束的存在,國有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者會產(chǎn)生一種想法:不管企業(yè)由于何種原因發(fā)生虧損,自己都不用承擔(dān)任何責(zé)任,政府和銀行會為此“埋單”。 通過曾海艦和蘇冬蔚的研究發(fā)現(xiàn),銀行可貸資金的變動主要影響小公司、民營程度高的公司以及擔(dān)保能力弱的公司,而大公司、國有程度高的公司以及擔(dān)保能力強(qiáng)的公司則不容易受到影響。因此,面對信貸政策的變化,國有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者優(yōu)化資本結(jié)構(gòu)的動機(jī)嚴(yán)重不足。當(dāng)存貸利差增大時(shí),本文提出假設(shè):
假說3:信貸政策發(fā)生變化時(shí),非國有企業(yè)比國有企業(yè)更加敏感。
數(shù)據(jù)、變量與模型
(一)數(shù)據(jù)來源與處理
本文數(shù)據(jù)選取時(shí)間跨度為2010-2014年,選取對象為滬深A(yù)股上市公司,并且做了如下處理:剔除金融保險(xiǎn)類行業(yè)上市公司;剔除ST和ST*上市公司;剔除樣本期間內(nèi)觀測數(shù)據(jù)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樣本期間內(nèi)資產(chǎn)負(fù)債率<0或者資產(chǎn)負(fù)債率>1的上市公司。由此,得到了一個(gè)包含557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數(shù)據(jù)。被解釋變量、資本結(jié)構(gòu)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數(shù)據(jù)均來自國泰安數(shù)據(jù)庫中上市公司企業(yè)數(shù)據(jù)板塊,信貸政策變量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wǎng)站公布的年度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
(二)變量選取
在參考已有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研究需要,本文選取的具體變量及定義如表1所示。
(三)計(jì)量模型設(shè)計(jì)
為檢驗(yàn)本文提出的3個(gè)假設(shè),構(gòu)建如下回歸模型:
(1)
(2)
(3)
模型(1)中,資本結(jié)構(gòu)變量Leverage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債務(wù)水平。credit代表信貸政策,即銀行短期存貸利差。根據(jù)假說1,存貸利差與負(fù)債水平正相關(guān),即存貸利差增大,負(fù)債水平提高,預(yù)期credit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正。模型(2)中引入了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虛擬變量(SOE),若為國有企業(yè),則SOE為1,反之為0。根據(jù)假說2,國有企業(yè)的資產(chǎn)負(fù)債率會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yè),預(yù)期SOE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正。模型(3)在模型(1)、(2)的基礎(chǔ)上加入了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與信貸政策的交互項(xiàng)(credit*SOE),根據(jù)假說3,信貸政策發(fā)生變化時(shí),非國有企業(yè)比國有企業(yè)更加敏感,因此預(yù)期SOE*credit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負(fù)。
其余變量為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一是企業(yè)規(guī)模(size),根據(jù)權(quán)衡理論,其他條件不變,規(guī)模越大財(cái)務(wù)拮據(jù)的可能越小,財(cái)務(wù)杠桿利用越充分,因而企業(yè)規(guī)模與資本結(jié)構(gòu)應(yīng)呈正相關(guān),預(yù)期size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正。二是成長性(growth),根據(jù)已有文獻(xiàn)資料,成長性的影響不能確定,一方面,從權(quán)衡理論考慮,高成長性的企業(yè)財(cái)務(wù)拮據(jù)成本較大,因此負(fù)債水平較低;另一方面,高成長性的企業(yè)資金需求量大,內(nèi)源融資很有可能無法滿足資金需求,因此更有可能以債務(wù)融資的方式融通資金。三是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structure),固定資產(chǎn)規(guī)模越大,抵押擔(dān)保價(jià)值越大,資本成本越低,因而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與資本結(jié)構(gòu)應(yīng)呈正相關(guān),預(yù)期structure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正。四是盈利能力(profit),根據(jù)融資啄序假說,外部融資的成本大于內(nèi)源融資,因此盈利能力較強(qiáng)的企業(yè)往往內(nèi)部資金充裕,債務(wù)融資比例較小,因而盈利能力與資本結(jié)構(gòu)應(yīng)呈負(fù)相關(guān),預(yù)期profit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負(fù)。五是非債務(wù)稅盾(DEP),從稅收成本考慮,內(nèi)部折舊、攤銷等非債務(wù)稅盾比例越大,利用財(cái)務(wù)杠桿提高稅盾的可能性越小,因而非債務(wù)稅盾與資本結(jié)構(gòu)應(yīng)呈負(fù)相關(guān),預(yù)期DEP的系數(shù)應(yīng)顯著為負(fù)。
實(shí)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tǒng)計(jì)
根據(jù)本文的研究目的,結(jié)合已有數(shù)據(jù)進(jìn)行描述性統(tǒng)計(jì),表2是回歸模型中所涉及變量的簡單描述性統(tǒng)計(jì)。
根據(jù)表2中數(shù)據(jù)可得出:資產(chǎn)負(fù)債率(Leverage)平均值為0.467,國際上認(rèn)為資產(chǎn)負(fù)債率為0.6較合適,表明A股上市公司2010年至2014年之間平均負(fù)債水平較低,并且數(shù)據(jù)呈左偏分布(中位數(shù)為0.476),表明個(gè)別資產(chǎn)負(fù)債率極低,這與我國上市公司的“強(qiáng)股權(quán)”偏好有關(guān);另外,根據(jù)標(biāo)準(zhǔn)差0.203能夠看出,債務(wù)水平存在較大差異,企業(yè)由于償債能力、公司戰(zhàn)略、經(jīng)營目標(biāo)等因素舉債經(jīng)營的偏好不同,由最大值(0.927)和最小值(0.007)也可以看出債務(wù)水平的巨大差異。此外,企業(yè)規(guī)模(size)主要分布在18.851與28.509之間,標(biāo)準(zhǔn)差為1.377,平均值為22.440,中位數(shù)為22.240,呈右偏分布,表明個(gè)別企業(yè)由于管理者存在過度擴(kuò)張。成長性(growth)標(biāo)準(zhǔn)差為1.533,最大值26.641,最小值為0.091,表明不同企業(yè)未來的投資機(jī)會差異較大。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structure)呈右偏分布,表明個(gè)別企業(yè)為了追求盈利而激進(jìn)投放較大比例資金于固定資產(chǎn),標(biāo)準(zhǔn)差0.185,說明不同企業(yè)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側(cè)重不同,抵押變現(xiàn)能力差異不同 。盈利能力(profit)分布較分散,標(biāo)準(zhǔn)差為0.096,表明2010至2014年間A股上市公司的質(zhì)量存在著較大差異。非債務(wù)稅盾(DEP)標(biāo)準(zhǔn)差為0.487,最大值為10.503,最小值為0.001,表明非債務(wù)稅盾的運(yùn)用程度不同,稅盾效應(yīng)的作用受限,企業(yè)會努力提高非債務(wù)稅盾,右偏分布也表明由于債務(wù)融資的不足,尤其是股權(quán)比例極高的企業(yè)只能運(yùn)用非債務(wù)稅盾來獲得節(jié)稅利益。
(二)信貸政策與資本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分析
為了使結(jié)果更具可靠性,本文對同一模型進(jìn)行了兩種回歸:包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不含年度變量和行業(yè)變量;包含解釋變量和所有控制變量。
表3為信貸政策與資本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多元回歸結(jié)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資產(chǎn)負(fù)債率(Leverage);短期存貸利差(credit)為信貸政策對資本結(jié)構(gòu)影響的解釋變量,其余變量為控制變量,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size)、成長性(growth)、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structure)、盈利能力(profit)和非債務(wù)稅盾(DEP),用以檢驗(yàn)本文的假說1:存貸利差與負(fù)債水平正相關(guān),即存貸利差增大,負(fù)債水平提高。
信貸政策變量即短期存貸利差(credit)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表明存貸利差與資本結(jié)構(gòu)顯著正相關(guān)。在我國企業(yè)中,流動負(fù)債占有相當(dāng)大的比重,隨著短期存貸利差地增大,商業(yè)銀行會更加積極進(jìn)行放貸以提高整體收益,企業(yè)特別是非國有企業(yè)會借此機(jī)會貸款,資產(chǎn)負(fù)債率隨之提高。因此,隨著存貸利差的增大,企業(yè)會相應(yīng)地提高資產(chǎn)負(fù)債率,該結(jié)果符合假設(shè)的預(yù)期,假說1得到驗(yàn)證。
其他控制變量的檢驗(yàn)結(jié)果與理論預(yù)期基本一致。企業(yè)規(guī)模(size)與資產(chǎn)負(fù)債率顯著正相關(guān),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表明隨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kuò)大,債務(wù)水平相應(yīng)增加;成長性(growth)與資產(chǎn)負(fù)債率顯著負(fù)相關(guān),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符合權(quán)衡理論,即高成長性的企業(yè)資金需求量大,內(nèi)源融資無法滿足資金需求,因此更傾向于以債務(wù)融資的方式融通資金。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structure)與資產(chǎn)負(fù)債率顯著正相關(guān),并且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固定資產(chǎn)越多,償債能力越強(qiáng),越容易獲得借款,資產(chǎn)負(fù)債率越高。盈利能力(profit)與資產(chǎn)負(fù)債率負(fù)相關(guān),說明盈利能力強(qiáng),內(nèi)部資金充足,對外依賴較少,負(fù)債水平較低。非債務(wù)稅盾(DEP)與資產(chǎn)負(fù)債率顯著負(fù)相關(guān),并且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yàn),表明非債務(wù)稅盾與債務(wù)稅盾之間存在“替代效應(yīng)”,非債務(wù)稅盾提高,企業(yè)會減少債務(wù)稅盾的運(yùn)用,以此降低經(jīng)營風(fēng)險(xiǎn),降低負(fù)債水平。
(三)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與資本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分析
為了使結(jié)果更具可靠性,本文對同一模型進(jìn)行了兩種回歸:包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不含年度變量和行業(yè)變量;包含解釋變量和所有控制變量。
表4為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與資本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多元回歸結(jié)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資產(chǎn)負(fù)債率(Leverage);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虛擬變量(SOE)為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對資本結(jié)構(gòu)影響的解釋變量,其余變量為控制變量,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size)、成長性(growth)、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structure)、盈利能力(profit)和非債務(wù)稅盾(DEP),用以檢驗(yàn)本文的假說2:國有企業(yè)的資產(chǎn)負(fù)債率會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yè)。
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變量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表明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與資本結(jié)構(gòu)顯著正相關(guān)。一方面,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機(jī)制不健全,國家以及全體公民對管理者的監(jiān)督意識薄弱,導(dǎo)致國有企業(yè)的管理者在事實(shí)上掌握了控制權(quán),因此投資以及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更多地是出于對管理者自身利益的考慮而非股東利益,管理者可能出于私人目的而舉債投資于凈現(xiàn)值為負(fù)的項(xiàng)目,導(dǎo)致負(fù)債率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從企業(yè)和銀行的所有權(quán)方面來講,國有企業(yè)的所有權(quán)人為國家,與非國有企業(yè)相比,這在很大程度上減小了國有企業(yè)貸款的難度。換言之,即使國有企業(yè)達(dá)不到貸款條件,但迫于壓力銀行也會不情愿地發(fā)放貸款。因此,國有企業(yè)的負(fù)債水平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yè),該結(jié)果符合假設(shè)的預(yù)期,假說2得到了驗(yàn)證。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構(gòu)與表三一致,在此不再贅述。
(四)信貸政策、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與資本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分析
為了使結(jié)果更具可靠性,本文對同一模型進(jìn)行了兩種回歸:包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不含年度變量和行業(yè)變量;包含解釋變量和所有控制變量。
表5為信貸政策、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對資本結(jié)構(gòu)共同影響的多元回歸結(jié)果。為了檢驗(yàn)信貸政策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對資本結(jié)構(gòu)的共同影響,在上述一般模型的基礎(chǔ)上加入信貸政策與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的交互項(xiàng)(credit*SOE)。其中被解釋變量為資產(chǎn)負(fù)債率(Leverage);短期存貸利差(credit)、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虛擬變量(SOE)以及短期存貸利差與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交互項(xiàng)(credit*SOE)為解釋變量,其余變量為控制變量,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size)、成長性(growth)、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structure)、盈利能力(profit)和非債務(wù)稅盾(DEP),用以檢驗(yàn)本文的假說3:信貸政策發(fā)生變化時(shí),非國有企業(yè)比國有企業(yè)更加敏感。
信貸政策與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的交互項(xiàng)變量(credit*SOE)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yàn),表明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確實(shí)會通過影響信貸政策來影響資本結(jié)構(gòu)。在我國,國有企業(yè)有著較強(qiáng)的行政色彩,承擔(dān)了很多社會目標(biāo),例如增加就業(yè)、維持社會穩(wěn)定等,因此國有企業(yè)在很多時(shí)候并不是以企業(yè)價(jià)值最大化為目標(biāo),政府也會為國有企業(yè)“埋單”,當(dāng)國有企業(yè)資不抵債時(shí),政府會對國有企業(yè)施以援手。同時(shí),國有企業(yè)薪酬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使國有企業(yè)的管理者沒有動力優(yōu)化資本結(jié)構(gòu)。不同的是,非國有企業(yè)的管理者往往也是大股東,管理者利益與股東利益趨于一致,非國有企業(yè)會抓住機(jī)會積極優(yōu)化資本結(jié)構(gòu)。因此,當(dāng)信貸政策發(fā)生變化時(shí),非國有企業(yè)更加敏感,即存貸利差增大,非國有企業(yè)會基于銀行的積極放貸努力提高負(fù)債水平,而國有企業(yè)不存在貸款難的問題,提高負(fù)債水平的動力不大,該結(jié)果符合假設(shè)的預(yù)期,假說3得到了驗(yàn)證。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構(gòu)與表3一致,在此不再贅述。
穩(wěn)健性檢驗(yàn)
為了增強(qiáng)實(shí)證結(jié)果的可靠性,進(jìn)行如下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首先,將短期存貸利差全部替換為短期貸款利率;其次,將資產(chǎn)負(fù)債率細(xì)分為流動資產(chǎn)負(fù)債率和長期資產(chǎn)負(fù)債率分別進(jìn)行回歸;最后,在模型中增加GDP等宏觀經(jīng)濟(jì)方面的變量以及高管持股水平、機(jī)構(gòu)持股水平等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量。結(jié)果表明,不論上述哪種改變,模型估計(jì)結(jié)果都具有良好的穩(wěn)健性,變量回歸系數(shù)的符號和顯著性均沒有發(fā)生實(shí)質(zhì)性變化。
結(jié)論
本文首先從信貸供給方面,研究了信貸政策對資本結(jié)構(gòu)的影響,說明資本結(jié)構(gòu)會隨信貸供給的改變產(chǎn)生同向變化,即當(dāng)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的利差增大時(shí),企業(yè)會積極提高負(fù)債水平,資產(chǎn)負(fù)債率顯著上升;反之,當(dāng)存貸利差減小,資產(chǎn)負(fù)債率顯著下降。進(jìn)一步,本文研究了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對資本結(jié)構(gòu)的影響,結(jié)果表明國有企業(yè)的資產(chǎn)負(fù)債率明顯高于非國有企業(yè)。這一研究結(jié)果與理論預(yù)期一致。與此同時(shí),在前述結(jié)論的基礎(chǔ)上,本文還發(fā)現(xiàn),當(dāng)信貸政策發(fā)生變化時(shí),非國有企業(yè)更加敏感,非國有企業(yè)會更加積極地調(diào)整負(fù)債水平,這也從側(cè)面反映了國有企業(yè)預(yù)算軟約束以及非國有企業(yè)貸款難的問題。
參考文獻(xiàn):
1.張?zhí)x赤,高芳.利率對上市公司資本結(jié)構(gòu)影響的實(shí)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7(12)
2.伍中信,張婭,張雯.信貸政策與企業(yè)資本結(jié)構(gòu)——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J].會計(jì)研究,2013(3)
3.唐國正,劉力.利率管制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jié)構(gòu)的影響[J].管理世界,2005(1)
4.曾海艦,蘇冬蔚.信貸政策與公司資本結(jié)構(gòu)[J].世界經(jīng)濟(jì),2010(8)
5.穆爭社.信貸配給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J].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1)
6.肖作平.所有權(quán)和控制權(quán)的分離度、政府干預(yù)與資本結(jié)構(gòu)選擇——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實(shí)證證據(jù)[J].南開管理評論,2010(5)
7.陸正飛,辛宇.上市公司資本結(jié)構(gòu)主要影響因素之實(shí)證研究[J].會計(jì)研究,1998(8)
8.馬文超,胡思.貨幣政策、信貸渠道與資本結(jié)構(gòu)[J].會計(jì)研究,2012(11)
9.盛明泉,張敏,馬黎,李昊.國有產(chǎn)權(quán)、預(yù)算軟約束與資本結(jié)構(gòu)動態(tài)調(diào)整[J].管理世界,2012(3)
10.忻文.國有企業(yè)的資本結(jié)構(gòu)分析[J].經(jīng)濟(jì)研究,1997(8)
11.趙冬青,朱武祥.上市公司資本結(jié)構(gòu)影響因素經(jīng)驗(yàn)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06(2)
12.楊亞達(dá).國有企業(yè)資本結(jié)構(gòu)的實(shí)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2(4)
13.趙興楣,王華.政府控制、制度背景與資本結(jié)構(gòu)動態(tài)調(diào)整[J].會計(jì)研究,2011(3)
14.方軍雄.所有制、制度環(huán)境與信貸資金配置[J].經(jīng)濟(jì)研究,2007(12)
15.曾海艦,蘇冬蔚.宏觀經(jīng)濟(jì)因素與公司資本結(jié)構(gòu)變動[J].經(jīng)濟(jì)研究,2009(12)
16.Barclay M . ,and C . smith .The priorit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bond yields spreads [J].Journal of Finance , 1995(50)
17.Frank,M.Z.,andV.K.Goyal.CapitalStructureDecisions:Which Factors are Reliably Important? [J].Working paper,Sauder 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