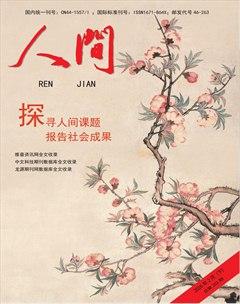試論中國文化里的“詩意棲居”
黃鵬濤
摘要:在如今物欲橫流的社會中,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能讓我們的心靈沉寂下來的自由空間。物質的享受只愉悅于感官,而精神上的享受則在于詩意棲居思想的翱翔。“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仿佛我們的靈魂本就應該屬于那無拘無束的詩意境界,我們的生活也應該屬于那“桃花源”里的恬淡閑趣。我們從中國文化中找尋,從詩人的意境中回味,從他們的永恒意志中構建現代人的“詩意棲居”。
關鍵詞:詩意棲居;儒家;道家;現代意義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215-01
現代人在探尋詩人的心靈世界,主要是通過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的生活描述。如人們對于陶淵明的詩意生活就是推崇備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短短的兩句,閑情雅致的愜意生活就躍然紙上。詩中的意象“菊”、與“南山”如真真切切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仿佛二者就是這樣愜意生活的象征。詩人賦予了平常事物不一樣的生命特征,這種特征是詩人自身某種品質的體現,或是某種不可得到的事物的寄托。對于詩意的棲居的研究,自古有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引用詩人荷爾德林的著名詩句“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息于這塊大地上”,他給予了這首詩以深刻的哲學詮釋, 中國詩人對詩意棲居的理解則表現在一首首詩詞中,通過直接的描寫,展現詩意棲居的美好畫卷。
一、“詩意棲居“里的儒道釋思想
自先秦以來,道家老子的“無為守靜”的思想以及莊子“天地與我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地人為一的思想,促使與啟迪無數人開始探尋思想的自由,回歸自然,找尋自我。道家一再強調的自由究竟為何物?自由體現了人的本質,人們對自由的向往是人們前進的最大動力,道家的偉大之處在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自由、詩意的精神世界,實現精神的自在與逍遙。唐朝詩人李白的人生標簽必有他的豪放不羈,自由無束。“筆落驚天地,詩成泣鬼神”,他展現出的正是道家對人生的一種態度,飲酒賦詩,縱情山水、求仙訪道。在他的詩歌中充滿著天馬行空般的想象,“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正是他這樣的人生態度為他的詩歌賦予了鮮明的特色,他的人生就是在濁世中翩然獨立的“詩意人生”。道家對于詩意的生活除了在精神上給予引導,在具體地生活形態也給予了描繪。“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這是道家眼中詩意生活的具象,也是陶淵明心中的桃花源,更是無數人內心深處的靈魂歸宿。在這片小天地里,社會的秩序無需政治力量的干涉,依靠的是人們純良的本性,無兵禍戰亂、無苛政重賦、無詭譎人心、無爾虞我詐,有的只是民風淳樸、物美人善的田園棲居。與外界的隔離,盡管會脫離歷史的發展,但保留的是人性的純真與質樸。莊子《大宗師》謂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將這一份恬淡的詩意棲居增添一份逍遙之意。
《論語·學而》中說:“子曰:句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儒家以“入世”的觀點影響著無數的讀書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儒家比道家多了些世俗的羈絆,如何能達到詩意的棲居?也許我們可以從孔子對顏回的稱贊中找到答案,“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儒家思想中,君子,當安貧樂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也應專心求學。換言之,儒家給予人們是面對困苦之境的意志支撐。它的作用則在于為詩意的生活提供現實的追求,使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相互聯系。
禪宗作為受外來文化影響而中國化的哲學思想,強調“明心見性“、”“ 空靈自在”的精神境界,追求超脫世俗來獲得內心的寧靜與自由。享受著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智慧安樂的人生。這點可以從許多詩人的禪理詩中體現。詩人不僅從禪理中體會詩意的人生,以一份超然物外的姿態“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歲天外云卷云舒”。對心外之物保持著淡然、寧靜。
二、“詩意棲居”的詩意化表達
受三種哲學思想的影響,中國詩人在現實生活之外,通過自己的筆觸描繪屬于自己靈魂的精神居所。從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中“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再到王維的“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落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還有“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終南別業》),對于自然的那份空靈與寂靜以淡雅的色彩抹在人生畫卷上,我們不得不感嘆詩人的蕙質蘭心,世界從來不缺乏美,缺乏的往往只是發現美得眼睛。詩中充滿了禪意,為自然之景蒙上了一道理性的面紗,表明了擺脫了世俗羈絆的詩人已觸摸到人與自然渾然合一的玄妙之境。
讓后人記憶最深的是陶淵明的精神世界,因為他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屬于精神的伊甸園,它通過筆下的漁夫,穿過世俗牽絆的山洞,找到了靈魂深處的那片凈地。身處于思想與社會動蕩不安的東晉之世,陶淵明在繼承儒家的入世有為思想的基礎上,又繼承了道家出世的逍遙人格。詩人的安居之處,在于構建一處不僅可供安身立命的生命場域,而且可以用詩意刻畫人生的詩意棲居。
三、詩意棲居與現代社會的反思
高樓林立的都市森林取代了園林與田舍,寄情的山水已是人山人海。“大隱隱于朝,小隱隱于野”,所謂的隱逸文化已漸漸地離我們而去,隱逸文化的斷裂與缺失,但作為一種文化心態,卻是永恒的,留在現代人的心底。除了緬懷文人們的高逸情懷外,在日益追求和諧的今天,精神與物質,自然與發展都需要詩意的調和,它與現代社會的商業消費相結合,共同構成了居住文化、審美文化。人們在建筑風格上效仿古代建筑,希望賦予那冰冷的建筑以文化內涵,希望家是如桃源般的歸宿。其次,在審美的過程中我們對古典美學以現代化的注解,將“詩意棲居”中所代表的美學看作為“日常生活的美學”,雖向往著古人貼近自然、炊煙裊裊的生活,但并非如空中樓閣構建與虛無之上,而是將這種理想宛若天成的融入于現代的日常生活中,在現實和心靈之間留下一方凈土。
參考文獻:
[1]李澤厚《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2]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演講與論文集》,三聯書店20()5年10月北京版
[3]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一,中華書局,1997年10月版.
[4]袁行需撰《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