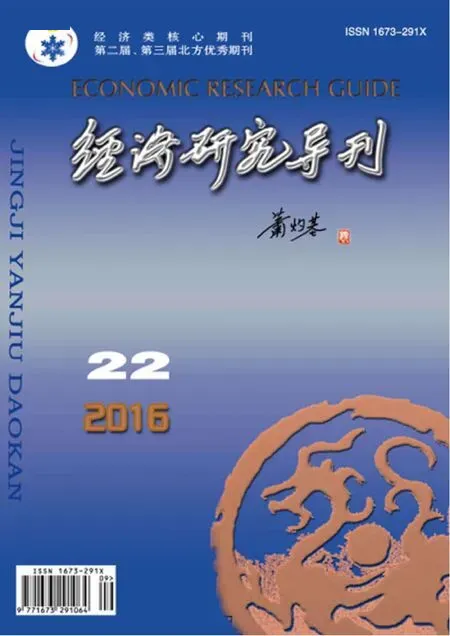中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與“中等收入陷阱”規(guī)避研究
王瑋
(哈爾濱商業(yè)大學(xué),哈爾濱 150028)
中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與“中等收入陷阱”規(guī)避研究
王瑋
(哈爾濱商業(yè)大學(xué),哈爾濱 150028)
自“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以來,能否順利規(guī)避“中等收入陷阱”被視為檢驗(yàn)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試金石。中國經(jīng)濟(jì)長期粗放型發(fā)展,導(dǎo)致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失衡,需求結(jié)構(gòu)、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鄉(xiāng)結(jié)構(gòu)、收入分配結(jié)構(gòu)不協(xié)調(diào)等問題日益突出。通過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實(shí)證分析,發(fā)現(xiàn)中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與收入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均衡關(guān)系,但居民消費(fèi)率與城鎮(zhèn)化水平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作用不顯著。因此,中國需通過結(jié)構(gòu)改革推進(jìn)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規(guī)避“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
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中等收入陷阱;經(jīng)濟(jì)增長
一、國內(nèi)外關(guān)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guān)研究
“中等收入陷阱”一經(jīng)提出,便引起經(jīng)濟(jì)學(xué)界的廣泛討論,并且常常被作為衡量中國經(jīng)濟(jì)前景的參考點(diǎn)。李克強(qiáng)總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bào)告中指出,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階段,同時(shí)指出,當(dāng)前發(fā)展中總量問題與結(jié)構(gòu)性問題并存,結(jié)構(gòu)性問題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方法推進(jìn)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亞洲開發(fā)銀行在《亞洲2050:實(shí)現(xiàn)亞洲的世紀(jì)》報(bào)告中表示,針對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亞洲國家必須進(jìn)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以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轍。因此,適時(shí)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矯正結(jié)構(gòu)性失衡,成為促進(jìn)中國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規(guī)避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guān)鍵點(diǎn)。
基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視角,Hausman(2006)指出,由貧窮國家向富有國家轉(zhuǎn)變的經(jīng)濟(jì)增長過程實(shí)際上就是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和升級的過程[1]。WingThye Woo(2009)以馬來西亞為例,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進(jìn)行分析,指出為保持宏觀經(jīng)濟(jì)平穩(wěn)運(yùn)行,馬來西亞政府必須進(jìn)行徹底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改革[2]。Vandenberg和Zhuang(2011)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不合理,甚至出現(xiàn)產(chǎn)能過剩的情況,這些問題可能誘發(fā)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但林毅夫(2012)認(rèn)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中國經(jīng)濟(jì)的必然命運(yùn),經(jīng)濟(jì)水平長期處于低等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主要原因是不能進(jìn)行持續(xù)性的結(jié)構(gòu)變遷[4]。馬巖(2009)、馬曉河(2011)通過對比國家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認(rèn)為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是現(xiàn)階段中國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5~6]。劉偉(2011)從微觀資源配置與宏觀經(jīng)濟(jì)調(diào)控兩個(gè)角度,分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guān)鍵在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轉(zhuǎn)換發(fā)展方式[7]。
雖然國內(nèi)外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眾多,但絕大多數(shù)文獻(xiàn)仍注重在理論上對于經(jīng)濟(jì)增長發(fā)展瓶頸的解決,尚未形成系統(tǒng)全面的理論分析結(jié)構(gòu),仍缺少廣泛的實(shí)證研究。另外,針對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威脅這一現(xiàn)狀,中國除有其他國家表現(xiàn)出的共性問題外,同時(shí)因經(jīng)濟(jì)大國的身份與國情的復(fù)雜還表現(xiàn)出一些特性問題,例如農(nóng)業(yè)基礎(chǔ)薄弱、區(qū)域發(fā)展不協(xié)調(diào)。因此,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還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中國國情,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指標(biāo)與數(shù)據(jù)
世界銀行以人均GNI對各個(gè)國家或地區(qū)的收入水平進(jìn)行劃分,但由于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人均GNI與人均GDP高度一致,人均GDP比人均GNI更容易獲得,且經(jīng)濟(jì)研究中普遍以GDP或人均GDP度量經(jīng)濟(jì)增長,因此選用人均GDP(AGDP)代替人均GNI作為被解釋變量。
參考廣義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定義,主要從消費(fèi)結(jié)構(gòu)、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鄉(xiāng)結(jié)構(gòu)、收入分配結(jié)構(gòu)四個(gè)方面作為解釋變量描述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變動情況,以居民消費(fèi)率(con)衡量消費(fèi)結(jié)構(gòu),第一、二、三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pri,sec,ter)衡量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鎮(zhèn)化水平(urb)衡量城鄉(xiāng)結(jié)構(gòu)、基尼系數(shù)(gini)衡量收入分配結(jié)構(gòu)。
樣本選取時(shí)間為1981—2014年,樣本量共計(jì)34。除基尼系數(shù)來源于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庫,其他數(shù)據(jù)均來自于《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
三、實(shí)證分析
(一)模型的選取
考慮到選取多個(gè)解釋變量,構(gòu)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采用最小二乘估計(jì)對時(shí)間序列進(jìn)行分析。為了消除時(shí)間序列的異方差性,對全部變量取對數(shù)處理。構(gòu)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c為常數(shù)項(xiàng),b1、b2、b3、b4、b5、b6為回歸系數(shù),εt為殘差項(xiàng)。
(二)平穩(wěn)性檢驗(yàn)
在對經(jīng)濟(jì)變量的時(shí)間序列進(jìn)行建模分析時(shí),首先要求各個(gè)時(shí)間序列保持同階單整,才能進(jìn)行后續(xù)的協(xié)整分析。由于對各個(gè)變量取對數(shù)后的上述時(shí)間序列的ADF檢驗(yàn)的P值均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不能拒絕各時(shí)間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shè),即認(rèn)為各時(shí)間序列不平穩(wěn)。因此,對這些時(shí)間序列進(jìn)行一階差分,再對一階差分后得到的序列進(jìn)行ADF檢驗(yàn),一階差分后的時(shí)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yàn)的P值均小于5%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各時(shí)間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shè),即認(rèn)為各時(shí)間序列平穩(wěn),均表現(xiàn)為一階單整,可以進(jìn)行協(xié)整檢驗(yàn)。
(三)回歸分析與協(xié)整檢驗(yàn)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jì)中國收入水平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協(xié)整關(guān)系的長期方程,由于在模型中存在影響不顯著的被解釋變量,因此對解釋變量逐個(gè)剔除,最終模型如下所示:

在該模型中,F(xiàn)值為5 741.828,F(xiàn)值與參數(shù)的t統(tǒng)計(jì)量的P值均為0.000,表示該模型通過整體顯著性和參數(shù)顯著性檢驗(yàn),校正的判定系數(shù)為0.999,表示該模型可擬合99.9%的數(shù)據(jù),DW值為1.661,模型不存在自相關(guān)。
對變量進(jìn)行協(xié)整檢驗(yàn)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偽回歸,考察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guān)系。通過對模型的殘差序列進(jìn)行ADF檢驗(yàn),t值為-5.047,對應(yīng)的P值為0.000,在1%的水平上顯著。結(jié)果表示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yàn)平穩(wěn),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可以建立長期均衡方程,上述長期均衡方程有明確的經(jīng)濟(jì)意義。由于變量間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但結(jié)果不顯著,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短期均衡關(guān)系。
(四)結(jié)論
在長期均衡結(jié)果中,盡管居民消費(fèi)率與城鎮(zhèn)化水平對中國收入水平均有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中國不能從單純地依靠居民消費(fèi)率與城鎮(zhèn)化率的提高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模型結(jié)果表明,中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長期均衡影響因素主要表現(xiàn)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與收入分配結(jié)構(gòu)。當(dāng)?shù)谝弧⒍⑷a(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將分別帶動中國的人均GDP增加0.89%、2.675%、1.178%,說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與升級是拉動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的主要?jiǎng)恿Αkm然三次產(chǎn)業(yè)的彈性系數(shù)均為正,但考慮到中國作為農(nóng)業(yè)大國的實(shí)際情況,農(nóng)業(yè)收入仍然是農(nóng)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另外,第二產(chǎn)業(yè)與第三產(chǎn)業(yè)的邊際貢獻(xiàn)明顯大于第一產(chǎn)業(yè)。因此,升級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應(yīng)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促進(jìn)二、三產(chǎn)業(yè)能力的提高。當(dāng)基尼系數(shù)變動1%時(shí),將會使中國人均GDP反向變動0.248%,說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越會抑制經(jīng)濟(jì)增長。
四、政策建議
中國目前正處于剛剛擺脫下中等收入進(jìn)入上中等收入水平的發(fā)展階段,這一階段也是重要的社會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時(shí)期。為規(guī)避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改善結(jié)構(gòu)失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從“中等收入陷阱”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相關(guān)理論出發(fā),分析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與“中等收入陷阱”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調(diào)整發(fā)展戰(zhàn)略,并采取綜合性的對策思路。
第一,轉(zhuǎn)變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再平衡。中國經(jīng)濟(jì)應(yīng)當(dāng)摒棄過去粗放型的增長模式以及對投資的過分依賴,以推動經(jīng)濟(jì)改革作為經(jīng)濟(jì)再平衡的切入點(diǎn),促使經(jīng)濟(jì)向創(chuàng)新驅(qū)動和結(jié)構(gòu)均衡的增長模式轉(zhuǎn)變。第二,推進(jìn)新型城鎮(zhèn)化,推動需求結(jié)構(gòu)改革。政府應(yīng)當(dāng)保證進(jìn)城務(wù)工人員和城鎮(zhèn)邊緣群體的基本權(quán)益,推進(jìn)戶籍改革,力爭城鄉(xiāng)居民享受同樣的社會公共服務(wù)。通過真正推動人口市民化進(jìn)程,將有助于提升中國內(nèi)需增長的動力,促使中國需求結(jié)構(gòu)的再平衡。第三,鼓勵(lì)技術(shù)創(chuàng)新,發(fā)展現(xiàn)代化產(chǎn)業(yè)。積極推動技術(shù)創(chuàng)新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協(xié)同發(fā)展,加大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完善創(chuàng)新激勵(lì)機(jī)制和服務(wù)體系,引進(jìn)優(yōu)秀人才,為推動技術(shù)創(chuàng)新和產(chǎn)業(yè)升級提供智力支持。第四,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兼顧公平與效率。構(gòu)建橄欖型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實(shí)現(xiàn)共享型發(fā)展理念,平衡收入分配,完善初次分配機(jī)制,健全再分配機(jī)制,整頓和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持續(xù)擴(kuò)大就業(yè),穩(wěn)定物價(jià)水平,是政府需要進(jìn)行宏觀調(diào)控的方向。
[1]Hausman Bailey.StrcturalTransformationandPatternsofComparative Advantage inthe Product[J].CID Working Paper,2006,(5):56-62.
[2]Wing Thye Woo.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J].Working Paper in SSRN,2009,(8):117-124.
[3]Vandenve,J.Zhuang.How Can China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R].Beijing: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1:26-29.
[4]林毅夫.新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學(xué)與中國發(fā)展之路[J].中國市場,2012,(5):3-8.
[5]馬巖.中國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及對策[J].經(jīng)濟(jì)學(xué)動態(tài),2009,(7):42-46.
[6]馬曉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關(guān)照和中國策略[J].改革,2011,(11):5-16.
[7]劉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guān)鍵在于轉(zhuǎn)變發(fā)展方式[J].上海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12):4-11.
[責(zé)任編輯吳高君]
F123.16
A
1673-291X(2016)22-0005-02
2016-06-23
王瑋(1993-),女,黑龍江綏濱人,碩士研究生,從事統(tǒng)計(jì)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