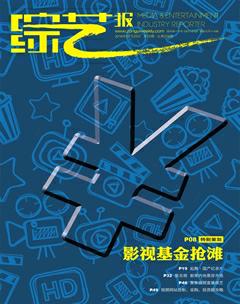對話《我在故宮修復文物》導演葉君:現代化趣味處理傳統內容
《綜藝報》:《我在故宮修復文物》角度新穎,當初是如何確定下這一選題的?
葉君:《我在故宮修復文物》這個選題是5年前我就想拍的,當時因為各方面條件不具備就暫且擱置了。
5年前,我參與了紀錄片故宮系列第二部《故宮100》的拍攝,當時我是分集導演,負責拍攝中軸線上的建筑。在做那個項目時,徐歡(紀錄片《故宮》總導演之一、《我在故宮修復文物》監制)、雷建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我在故宮修復文物》制片人)已經開始立項籌劃《我在故宮修復文物》,當時想的名字是《故宮心傳》,寓意將古代文化用心往下傳。《故宮》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側重建筑和歷史故事,一直缺少拍攝里面正在發生的事情和那些可愛有趣的人的故事。當時雷建軍帶著幾個學生在里面扎根數月,借助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做田野調查,并形成約10萬字的調查報告。
但要辦成一件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2015年,恰逢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需要一個獻禮片,這一項目得以重啟。
《我在故宮修復文物》不是歷史題材,呈現的是現實生活,既有文物修復技藝、也有不同性情的人,還有故宮生活細節。我們當時總結了“物(件)、事(件)、人(物)、非(物質文化)”4個字,不僅要有物件、事件、人物,還要體現故宮文化傳承的情感、情懷。
這次拍攝采用的是獨立紀錄片常用的長時間紀實拍攝辦法。三四個月時間里,不間斷地紀實拍攝,團隊人數最多時也就5-7人,當然這也是為了文物安全,拍攝團隊不宜過大。我們與修文物的師傅們——可別覺得都是花白胡子,他們中很多是高顏值的70后、80后、90后。我們一起同吃同工作,不久便熟悉、信任起來,最終成為朋友。
《綜藝報》:《我在故宮修復文物》受到眾多年輕人的歡迎,你和團隊在創作之初是否有意識向年輕觀眾靠攏?
葉君:我們自己就很年輕,并不需要特意向年輕觀眾靠攏。我的工作可以分解開來:內容設計者+項目負責人,那么少的人(5-7人),那么少的錢(制作經費不到15萬元),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把項目完成,我感受到的更多是緊迫感。
制作初期,我有兩個初衷——讓完全外行的人看得下去,讓年輕人看得下去。我有9個表弟9個表妹,年齡覆蓋80后、90后、00后,每年過年回家都解釋不了自己的工作,紀錄片離他們生活還是有些遠,我希望他們能看到這個片子并且看得下去。
《綜藝報》:通過這次播出,可以總結哪些經驗?
葉君:首先不要做一個對生活漠不關心的人。《我在故宮修復文物》反映的是一個職業人群的職業觀。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職業,每個職業都有瑣碎之處,故宮的這些師傅是在教我們如何與職業相處,與世界相處,與自己相處。影視作品、文學作品都有主題,這是我最早觀察到的和想表現的,而不是后來熱議的工匠精神。當然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大家喜歡看、有打動自己的地方就好。
其次是把傳統內容做現代化趣味處理,做出既現代又傳統的感覺。我們背著唐詩宋詞長大,但也坐著地鐵高鐵成長。傳統文化中有很多精彩內容,不經過現代趣味處理,可能大家真的久而久之就不看了。我們必須想辦法讓80后、90后、00后、10后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像看韓劇、日本動漫、美劇、英劇那樣去追。
第三是把專業性的東西做到通俗易懂。這也是我大學畢業的論文方向。我上學時不太喜歡本專業的課程,總去旁聽其他系的課,翻過一套叢書《人文社會科學是什么》很受啟發,每一冊都是一個專業領域的專家向外行講解本專業的知識。清華建筑系、美院的講座我也經常去聽,平時也喜歡看工藝美術和建筑設計方面的書,應該說我的運氣很好,把大學以來感興趣的東西都融入到這樣一部片子里。
《綜藝報》:是否預料到《我在故宮修復文物》在B站、豆瓣等平臺受熱捧?是否有團隊運營?
葉君:很慚愧,我平時看紀錄片不多,看書和文學作品比較多,所以無法預料。《我在故宮修復文物》在網上火爆,沒有團隊運營,原因很簡單——沒錢。片子在網上得以傳播,說明國人對高質量的文化消費是有需求的。
《綜藝報》:《我在故宮修復文物》目前是否收回了成本?主要有哪些收益方式?
葉君:據我所知應該沒有收回成本。賣給各大視頻網站的價格極低,3集總共萬元左右。紀錄片在中國只能叫行業,不能叫產業,這個行業缺少產品經理。
《綜藝報》:未來是否會拍攝第二季或其他衍生節目?
葉君:這是一部四方合作的紀錄片,央視、故宮、投資方杭州潛影以及制作方清影工作室。第二季目前還沒有規劃。衍生節目和電影,杭州潛影在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