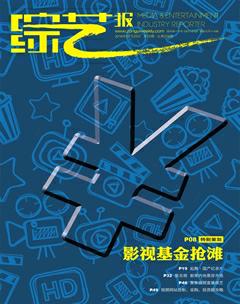兩年被批“太白”奧斯卡大幅擴充成員力求多元化
陸瑤
自2015年起,連續兩屆奧斯卡獲得提名和獎項的幾乎全是白人,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以下簡稱“學院”)因此被業內人士和社交網絡批評“太白”,指出奧斯卡存在明顯的歧視問題。很多電影人站出來斥責評委對少數族群的“無視”,著名導演李安就曾在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后發表公開信,除指出提名和獲獎結果的不公之外,還抗議奧斯卡的頒獎典禮“有損亞裔形象”。
走到這步田地,身為奧斯卡主辦方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也沒法再態度曖昧地閃爍其詞。最近,學院痛下決心,打算開放尺度在內部進行改革。今年6月底,學院公布了享有奧斯卡投票權的新晉成員名單,高達683人的數字創出歷史新高,名單中不但出現了侯孝賢、賈樟柯等亞洲電影人的名字,深受年輕人歡迎的“赫敏”扮演者艾瑪·沃特森等眾多年輕電影人位列其中。
這樣的改革對于傳統悠久的奧斯卡來說自然不易,但也顯示出學院改革的決心,只是,恐怕學院沒想到,自己突破保守思維的放手一搏,反而迎來了新一波質疑與嘲諷,這一次,卻是針對奧斯卡未來的威脅。
多樣性“千呼萬喚始出來”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奧斯卡評委普遍具有三個特征:年齡偏大、男性、白人。今年年初,學院總共有6261名會員,其中92%為白人,75%為男性。這次學院擴充奧斯卡評委,就是想通過調整6261名會員的構成,爭取“多樣化”。今年的新成員里,白人以外的少數種族占41%,奧斯卡評委總體少數種族的比例由8%提升至11%;新成員中女性占46%,女性評委總人數的比例由25%提升至27%。新成員里還包含28位奧斯卡獎獲得者,以及98位被提名者,來自59個海外國家的評委多達283人。新成員中甚至還有處于上升勢頭的年輕電影人,比如除了艾瑪·沃特森,還有在《星球大戰8》中嶄露頭角的黑人新星約翰·波耶加,音樂人瑪麗·簡·布萊姬和Will.i.am。另外,一些早已擁有成為奧斯卡評委資格的資深電影人也首度進入了學院名單,比如英國導演肯·洛奇,以及不久前剛剛過世的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相比較前幾年而言,今年的新成員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2011年學院只接收了176名新成員,2012年為178名,僅僅比前一年多了兩位。到了2014年,招收成員數字首次突破了200人限制,達到271人。2015年,322名新成員加入奧斯卡評委大軍,而2016年接收新成員的數量竟達到去年的兩倍有余。
如此大膽且大幅度的擴充會員名單,并引入眾多少數族裔及女性評委,學院主席謝麗爾·布恩·艾薩克斯以及獨立制片協會執行長唐恩·哈得森當然也不是“瞎指揮”。近年來新成員數量逐漸增多,評委群體漸漸擴張,但主體并未改變,仍舊是中年白人男性居多,女性和少數種族的比例反而隨著評委的增多而漸漸減小,評委構成越來越單一。實際上,早在2014年舉行第86屆奧斯卡的時候,“奧斯卡太白”的口號就已經產生,并引起了廣泛熱議。然而當時的抗議并沒有產生實際作用,也并未引起圈外人士的注意。直到2015年行業人士再次喊出“太白”的口號,并終于在社交媒體上炒作起來時,學院委員會才不得不重視起這個問題。學院主席艾薩克斯在學院委員會的支持下,投票決定了學院在2020年前,必須增加女性及少數族群會員比例。而想要達到一定的比例,2016年的候選人必定要擴大至少一倍。
降低“門檻”引發熱議
想要打入奧斯卡評委圈當然不是易事,首先必須取得一定的成績。學院在甄選新晉成員時會將內部分為17個分組,列出所有推薦名單,列出的每名新成員必須有兩位分組成員的推薦才有資格入選。基本條件是候選者必須在本領域有杰出的成就,而各個分組還會有其他的要求:比如,演員必須要有三個典型的銀幕形象,導演必須要有兩個導演作品。
許多分析人士并不看好奧斯卡評委的突然擴充,他們認為新增加的評委名單對于下一屆奧斯卡獎評選影響甚少,但對業內的認同標準卻影響頗大。從數字上來看,即便新入選奧斯卡評委有683人之多,然而看評委總數,女性和少數族群評委的比例卻只增加了2%到3%左右。而今年入選的會員達到史上最多,這讓甄選評委的標準產生了模糊,同時可以預見之后的評選工作會引發不少矛盾沖突。
首先,已經有不少業內人士對不屬于電影界的學院新成員頗多微詞。比如這一次入選的評委里,男演員安東尼·安德森曾獲得2015年艾美獎喜劇類最佳男主角提名,因主演《丑女貝蒂》而接連三次被提名金球獎喜劇和音樂電視劇最佳女演員的亞美莉卡·費雷拉,此二人在電視劇界赫赫有名,但在電影界卻無甚成就,這造成了他們雖入選卻很難服眾的結果。同樣遭遇的還包括戲劇界的切利·瓊斯、帕蒂·魯普恩,盡管他們的聲望和地位完全符合,甚至超出學院的基本要求,其才華也得到了大多數觀眾的認可,但還是無法很快被電影業內人士接受。
其次,擴充后的評委質量也令人擔憂。某位行業人士表示擴充舉措表面上似乎可以解決年齡、性別、種族上的歧視,然而入選的許多電影人事實上沒有足夠的職業生涯與評審經驗。有人提議,學院與其擴張數量,不如直接為少數族群單獨成立機構,這樣也不至于選入“不合格”或“資質不夠”的人進入奧斯卡評委群體。事實上,新名單中的確出現許多極有爭議的學院候選會員,有一些是非常年輕、資歷尚淺的電影人,比如這一次被提名的達科塔·約翰遜,雖然約翰遜是一位出身演藝世家、極有前途的女演員,但僅憑一部頗具爭議的電影《五十度灰》,就入選會員名單,未免略顯單薄。
再次,有些業內人士對學院的這項舉措反感,稱其“非常諷刺”。原因是這項新舉措對于一些老牌且貢獻極高的電影人來說,是一份太過“遲到”的公平:比如黑人導演馬文·范·皮布爾斯,曾經在1971年執導經典影片《斯維特拜克之歌》,開創了黑人電影的先河;1991年執導《塵土的女兒》的黑人女導演茱莉·黛許,也是杰出的少數種族女性導演,早已具備成為奧斯卡評委的資格,卻因為政策原因一直被推遲至今。不少業內人士懷疑“擴充”此舉形式多于實質,并未完全改變奧斯卡“太白”的核心。
奧斯卡未來問題重重
從此次新會員名單來看,奧斯卡評委“年輕化”的勢頭不可阻擋。然而“年輕化”就代表有道理嗎?從新名單來看,不少年輕演員和導演都入選學院成員,充分體現出奧斯卡重視“年輕力量”的意愿,反過來看,年輕也未嘗不是顆定時炸彈——畢竟好萊塢從業者極多,而年輕從業者的發展前景難以預料,如果他們未來發展平平,那么學院成員身份無疑就是給奧斯卡“挖了個坑”。畢竟推選制度決定了不是所有新會員都需要經過嚴格的篩查,也沒人能對年輕電影人的發展態勢給出客觀評價。
拿《星球大戰7》的約翰·波耶加來說,一位年僅24歲就擁有包括盧卡斯獎在內許多成就的電影人,雖然現在前途狀似一片大好,但過于年輕的年齡讓人難以判斷他是否能持續出現在電影舞臺上,又或者說能在一長段時間內維持現有水準。年輕電影人成為奧斯卡評委,畢竟為時尚早。
另外,這一屆的新成員不僅數量遠超歷屆新成員規模,除去少數族群,新成員里仍舊包含了大量的美國本土會員,考慮到少數族群的獲獎比例,美國本土電影人將面臨更大壓力,大大增加了奧斯卡的競選成本。
事實上,評委增多,也會給學院帶來經濟壓力。奧斯卡主辦方多年來相對節儉,過去學院一直主張不進行“高端”“非公開”的社交活動,目的是為了不影響奧斯卡投票的完整性、公正性。凡是會員違反規定參加社交活動,將會被剝奪選舉資格一年,再次違反的話甚至可以直接將之除名。這項規定自存在之日起,就一直被會員們從法律和道德等層面上質疑,畢竟此類社交活動看似奢侈,實則也是增進行業人士彼此了解的契機。經過長期磨合,學院才終于決定對院規進行部分調整、制定新規,規定學院在“活動日”即每年6月30日,成員可以參與各式高端社交活動,包括雞尾酒會、聚餐、茶會等。然而今年算上“擴招”的683人,擁有選舉資格的成員將從6000漲至7000,此類活動的成本也將一年年不斷增高。
另外,畢竟新名單中683人中的283位都來自于59個國家,而在此之前,學院最多只在2015年接待過來自海外國家的40余名評委。要使全部學院會員都能夠正常行使投票權,增加影片的獲獎率,首先就要讓會員都能在銀幕上看到電影。這除了要求屏幕的數量,也要求很高的軟硬件質量,畢竟觀影效果也要講求公平性。比如2009年橫掃第82屆奧斯卡各類獎項的《阿凡達》,又或者2013年獲得最佳影片、最佳視覺效果、最佳音效效果等等的《地心引力》,這些電影除了要求巨幕觀看,還必須配有相應字幕,逐一發送給會員。不管是影廳,還是翻譯與接待費用,甚至奧斯卡工作人員發送入圍的紀錄片、外語、短片郵件等等的工作量,都會給學院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
最重要的是,奧斯卡評委大幅增多且年輕化,會給評審標準帶來新的挑戰。人盡皆知,奧斯卡獎對商業影片和特效大片相對寬松,比較歐洲電影節和金球獎等等獎項,奧斯卡對商業影片一向給予最大的支持態度。然而新會員中的年輕電影人和非本土評委一般更傾向于獨立電影而非大成本商業電影,這些年輕人的大量加入,會對奧斯卡歷來堅持的評審標準帶來沖擊,很可能意味著好萊塢大片已經不再是奧斯卡評審的加分項。而大片“失寵”,或會導致部分觀眾的流失,進而影響到學院自身的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