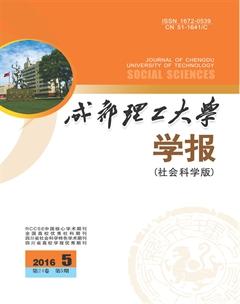關于我國刑法不存在片面共犯的探究
吳思齊
摘 要:關于片面共犯是否應以共同犯罪論處,理論界有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因果共犯論只是為共犯提供了處罰根據,并未實際解決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犯的問題。肯定說和否定說的理論基礎是行為共同說與犯罪共同說。以行為共同說為基礎所推演的結論不具有唯一性,結合我國刑法的規定,應當從解釋論上得出否定說的結論。片面共犯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是依據外國刑法解釋出的結論并非一定能適用于我國的司法實踐。
關鍵詞:因果性;行為共同說;共同故意;解釋論
中圖分類號: D92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5-0023-05
片面共犯是指行為人有與他人共同實施犯罪的意思,并實際參與他人的犯罪行為,但他人并不知情的犯罪形態。例如,甲追殺丙,乙知悉并且也希望置丙于死地,便在甲追殺丙的過程中設置障礙,阻礙丙逃跑,使甲順利完成犯罪,甲對此卻毫不知情(以下簡稱“典型案例”)。就不知情的甲而言,只需依其所犯之罪定罪量刑即可,并無爭議。然而對于知情并暗中參與的乙,是否應以共同犯罪論處,理論上存在肯定說和否定說的爭論。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作為共同犯罪的主觀要件,各個共犯人只要具有利用他人行為實現自己犯罪的意思就夠了,不要求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也不要求相互之間具有意思溝通和聯絡。因此,沒有意思聯絡的所謂片面共同犯罪之間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1]還有學者認為:“是否承認片面共犯,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共同犯罪的因果性……如果肯定共同犯罪的物理的因果性,那么,片面共犯也可以共同引起法益侵害,因而成立共同犯罪。”[2]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為:“所謂的‘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因為他的故意和行為都是單方面的,而不是行為人相互之間的共同故意和相互利用對方的行為,與我國刑法規定的共同犯罪的概念不符合。”[3]也有學者認為:“從整體上看,在所謂的片面共犯中,行為人無論是在認識因素上還是在意志因素上均不具有共同犯罪的一般特征。既然連普遍性都不存在,又從何談起特殊性?這時再稱之為共同犯罪,未免名不符實。”[4]理論上通常認為肯定說和否定說的理論基礎是行為共同說和犯罪共同說,持肯定說的學者一般以行為共同說為基礎論證片面共犯,持否定說的學者則以犯罪共同說作為論證依據。
對以上爭論進行梳理,不難發現肯定說和否定說的焦點在于因果性和犯意聯絡,亦即:首先,是否如持肯定說學者所言,將片面共犯成立的關鍵認定為如何理解共同犯罪的因果性?其次,承認因果性后,還應深入考慮片面共犯是否以意思聯絡為必要?這牽涉到犯罪共同說與行為共同說的合理性探討。最后,不應忽視的是,即使能在理論上得出肯定說的結論,也必須在我國刑法上找到條文作支撐,否則無法在裁判時指明法律依據。只有這三個問題得到解決,才能對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下結論,本文也由此展開。
一、因果共犯論與片面共犯的成立
任何犯罪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具有因果關系,這一點毋庸置疑,具體到共同犯罪的應用中,便是因果共犯論,該理論以因果關系為基礎來論述共犯的處罰根據。眾所周知,(狹義的)共犯并未直接實施惹起法益侵害結果的行為,為何刑法又將其作為犯罪處罰。對此,有責任共犯論、違法共犯論和因果共犯論的理論。責任共犯論以教唆犯為中心而發展,其主張共犯之所以被定罪處罰,是因為誘惑正犯,使其墮落進而陷入承擔刑事責任的境地。違法共犯論對責任共犯論進行了批判和修正,認為共犯之所以要受處罰,是因為其促使正犯實施了違法行為,使正犯卷入與社會的敵對狀態之中。因果共犯論主張共犯之所以要受處罰,是因為其通過正犯間接地使刑法要保護的法益受到現實的侵害或者危險,即共犯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性而受處罰。責任共犯論和違法共犯論因受到較多批判而逐漸遭到摒棄,因果共犯論逐漸成為通說(1)。
由因果共犯論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共犯與最終的犯罪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第二,共犯因參與正犯的行為或與正犯共同實行,進而引起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結果而應受處罰。以典型案例為例,乙暗中參與甲的追殺并設置障礙,阻礙丙逃跑,造成丙陷入前有阻礙、后有追兵的境地,其行為客觀上加劇了丙的生命遭受現實、緊迫的危險,并最終使得甲成功將丙殺害。盡管沒有意思聯絡,乙與甲的行為一起導致了丙的死亡,并且乙的阻礙行為使甲順利得手,與丙最終被殺害具有物理上的因果關系,所以乙的行為具有處罰根據。然而,并不能據此就得出“因果性是承認片面共犯的關鍵”的結論,理由如下:因果關系只是成立犯罪的前提之一,存在因果關系并非一定成立犯罪,更遑論成立片面共犯。同時,因果共犯論只是為共犯的處罰提供了理論依據,不能由此就認為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換言之,為共犯提供處罰根據的隱含前提,是成立共同犯罪或者說是具有共犯關系,在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還存在爭論的情況下,就認為承認片面共犯的關鍵是認識共同犯罪的因果性,結論難以成立。只有在論證片面共犯已經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才能繼續探討“是否承認片面共犯,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共同犯罪的因果性”這一觀點。
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與因果共犯論并非是同一層面的問題,將共犯的因果性作為論證片面共犯成立共同犯罪的依據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事實上,共犯因果性也并非承認片面共犯的關鍵,因為在經典案例中,若甲乙基于共謀而實行同樣的行為,則無疑會被認定為共犯,這種情形與原案例的差異也僅在意思聯絡上,透過控制變量法不難發現,承認片面共犯的關鍵是意思聯絡。
二、片面共犯的理論基礎探析
如上所述,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關鍵在于是否承認意思聯絡的必要性,這涉及到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的爭論。兩種理論都源于對共犯本質的理解,只是共犯成立要件有所區別,進而影響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
(一)共同犯罪的理論基礎是行為共同說
犯罪共同說包含完全犯罪共同說和部分犯罪共同說。完全犯罪共同說認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犯一罪,在不同的犯罪事實構成要件之間,不成立共犯[5]。部分犯罪共同說是在完全犯罪共同說基礎上修正的結論,認為如果數個犯罪存在構成要件的重合,則在重合限度內成立共同犯罪。該說在日本及我國成為通說。行為共同說則強調行為的共同,只要實施了共同的行為,就可以成立共同正犯,不要求必須是同一或者特定的犯罪,本質特征是“數人數罪”。然而關于什么是行為的共同,又存在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之分。主觀主義的行為共同說認為,行為的共同是指自然行為的共同,即前構成要件的或前法律的事實的共同,但這種觀點因不符合構成要件的定型性,已鮮有學者采納。客觀主義的行為共同說則認為是指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的共同[6]。現在的行為共同說通常指的是客觀主義的行為共同說。
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的爭論,體現的是時代的更迭與思維的深入。具體而言,完全犯罪共同說所表達的是最典型、最沒有爭議的共同犯罪。其根據是構成要件理論,因為犯罪都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而構成要件是犯罪的類型,共犯就應當是相同的犯罪類型,符合相同的構成要件。但如果二人以上出于不同故意卻共同實施某種行為時,依完全犯罪共同說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7]。部分犯罪共同說雖然在其基礎上進行了修正,卻并未改變完全犯罪共同說的本質,在論證上存在缺陷,因為在重合部分內成立共同犯罪并沒有意義,似乎是為了實現“共同”而刻意尋求犯罪的重合。另外,在“甲以殺人故意,乙以傷害故意共同致丙死亡,無法查清致死行為是誰實施”的場合,于故意傷害致死的范圍內成立共犯再進而認定甲是故意殺人罪,對甲有重復評價之嫌。行為共同說則主張通過實行行為的共同而自然地形成“共同”,只在罪名上實現個人責任即可,因而即使犯意不同,只要共同實行即可成立共犯。從犯罪共同說到行為共同說,是理論應對新問題的不斷完善,是從“數人犯一罪”到“數人犯數罪”、從“共同成立犯罪”到“共同實施犯罪行為”的認知的轉變。可以看到,行為共同說能解決現下出現而以往理論無法解答的新問題,同時在刑法理念上,尤其是較好地貫徹了罪刑法定、責任主義、法益保護原則,因而在共犯本質上,行為共同說存在合理性。
(二)行為共同說在片面共犯成立中的疑問
盡管行為共同說在解決共犯本質的問題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在論證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時有兩點疑問,具體如下:
首先,行為共同說提出了“共同行為”、“共同實行”的概念,彌補了犯罪共同說的不足,但是學者們進行論述時并未就“共同實行”是否一定需要意思聯絡給出明確的結論,而只在片面共犯的問題中才對意思聯絡的要件進行了闡述。這就導致持行為共同說的學者在是否需要意思聯絡上產生了分歧,有學者認為意思聯絡并非必需,從而承認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2]392,有的學者則認為意思聯絡是必需的,從而否認片面共犯,該學者指出:“盡管主張在不同構成要件之間能夠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在主觀上必須具備一個要素——‘共同行為的合意”[8]。因此,在以行為共同說為基礎論證片面共犯成立共同犯罪時,存在相當大的解釋空間,并非由行為共同說就一定能推導出肯定說的結論。
其次,在持行為共同說并且承認片面共犯的學者中,在成立范圍上出現分歧。有人認為在共同犯罪的各種范圍均可成立[5]79,89,90,有人認為片面共犯的范圍僅限于教唆犯和幫助犯,而不包含片面共同正犯[7]490,492,494。那么,同樣是持行為共同說,為何存在完全肯定和部分肯定的差異?共同正犯和狹義的共犯在本質上都是共同犯罪,既然行為共同說能合理解釋共犯的本質,就不應在論述片面共犯的成立范圍上存在分歧。這就說明在理論上僅以行為共同說為基礎推演片面共犯成立共同犯罪存在漏洞,在范圍上的不一致表示存在其他因素對片面共犯成立共同犯罪有制約,下文將就此詳述。
三、立足我國刑法的解釋
(一)立法體例在片面共犯上的差異
如上所述,行為共同說在論述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時存在較大的解釋空間,既可以得出肯定說的結論,也可以得出否定說的結論。即使得出肯定說的結論,在成立范圍上也有分歧。相反,犯罪共同說卻有承認片面共犯的空間,例如我國臺灣地區的主流觀點是犯罪共同說,卻承認片面幫助犯[9]。通過比較法上的考察,筆者發現其原因在于立法規定的差異,與共犯本質的理論并無必然關系。關于片面共犯的立法規定,主要有兩種模式:
1.明示的方式
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30條規定:“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雖他人不知情者,亦同。”泰國刑法中,也有類似的規定,該法典第86條規定:“在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時,以任何方法幫助或者便利其犯罪的,即使他人不知道該幫助或者便利情況的,也是從犯。”這些條文明確表明單方面的意思聯絡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故沒有爭議。
2.暗示的方式
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5條第2款規定:“數人共同實施犯罪的,均依正犯論處。”第27條第1款規定:“對他人故意實施的違法行為故意予以幫助的,是幫助犯。”《日本刑法典》第27條第1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第29條第1款規定:“輔助正犯的,以從犯處罰。”盡管從德國、日本的法條規定看,是否承認片面共同正犯可能還有爭論,但僅就幫助犯(從犯)的條文而言,完全能在解釋論上得到承認片面幫助犯的結論。
(二)對刑法總則關于共犯規定的解釋
行為共同說作為共犯本質的理論,只是為片面共犯的成立提供了一種可能,想要得出最終結論,還需要在我國刑法上找到法律依據,否則只能成為理論上的構建而不能具體應用于司法實踐。我國刑法第25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時在第二款還規定:“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第26條、27條、29條分別是關于主犯、從犯、教唆犯的規定(2)。與德、日、我國臺灣地區不同的是,我國大陸的刑法并未將共同正犯與狹義的共犯分開規定,而是將之捆綁為一個整體,因為在這三個條文之中都存在類似“在共同犯罪中”的規定,這表明主犯、教唆犯、從犯均是共同犯罪的下位概念。因此,若在解釋論上成立片面共犯,則其范圍應包含于所有共犯人而不應存在部分肯定的結論,否則與我國刑法的規定不符。這也是在論證片面共犯時,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最大區別。《刑法》第25條是對共同犯罪的定義,因此,對25條的解釋就成了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關鍵,就片面共犯而言,爭議點在于如何理解“共同故意犯罪”。
傳統理論認為,第25條規定的共同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認識他們的共同行為和行為會發生的危害結果,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要件上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為了成立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間必須存在意思聯絡(或意思疏通)。”[10]該理論顯然是以完全犯罪共同說為基礎,并明確提出共同犯罪需要意思聯絡。從解釋上看,該觀點并無問題,然而在論述片面共犯時又在否認片面實行和片面教唆的基礎上承認片面幫助[10]180。如前所述,因在解釋中未能貫徹共同正犯與狹義的共犯的一體化而與我國刑法規定不符。對此,有學者從行為共同說的觀點出發,將共同故意解釋為“共同故意去犯罪”[2]359。就該結論本身而言是也能成立,正如其隨后所言,這樣的解釋只是限制了共同犯罪的成立犯罪,結合第25條第2款的規定來看確實如此,但據此就認為成立共犯無需意思聯絡毫無根據可言。即使是共同過失犯罪,也需要意思聯絡。例如,甲乙相約去深山老林打獵,看見遠處樹林中有黑影竄動,便開槍射擊,誰知竟是長期生活在山中的“野人”,此處盡管甲乙共同過失致人死亡,但并非毫無意思聯絡。因為如果“共同去犯罪”之間不存在意思聯絡,僅憑客觀存在的“共同行為”就認定成立共犯,與同時犯沒有差別。
行為共同說在共犯本質的論述中具有合理性,并且在片面共犯中也并非存在結論的唯一性,因此筆者贊同將25條的“共同故意犯罪”解釋為“共同去故意犯罪”,但是必須承認這種“共同”以存在意思聯絡為前提。因為“共同去故意犯罪”的言下之意就包含了相互之間的意思聯絡,在漢語中“共同”一詞有兩種含義,而在共同犯罪的語境中并非只是形容詞性的“相同”之義,應作副詞“大家一起(做)”的意思去理解[11]。將“大家一起(做)”理解為包含只有一方知情而他方不知的情況,有違漢語用語習慣,也與一般人的認知難以契合。因此,即使采納行為共同說的理論去解釋第25條,也應當承認意思聯絡的必要性。德國、日本在該處的規定上與我國不同,首先,他們并未使用“共同犯罪”這一統籌共犯的定義;其次,在狹義的共犯的規定上,與共同正犯之間相互獨立,沒有“在共同犯罪中”這樣類似公因數的要求。所以,這也解釋了為何他們會在片面共同正犯上沒有定論,卻能承認片面從犯。
(三)對我國刑法分則關于共犯規定的解釋
對片面共犯持肯定論的學者另一個重要依據是具體犯罪的規定。例如我國《刑法》第198條第4款規定:“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為他人詐騙提供條件的,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論處。”再如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該學者將這些條文看作是刑法對片面共犯的特殊規定,應當與總則共同犯罪的規定相區別[5]19-23。
僅從這些條文本身看,認為片面共犯存在于我國刑法中可以成立。可是作為特別規定,其本身必須與刑法的一般規定不同才能被視作是“特別規定”,例如在轉化型搶劫中,犯盜竊、詐騙、搶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并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只是出于特殊考慮而將其擬制為搶劫。而在上述所謂存在片面共犯的條文中,本身就包含了存在和不存在兩種情況,不能僅以特殊規定的理由而冒然地得出肯定的結論,而必須從體系性的角度出發,結合總則的規定進行解釋。在總則的解釋中,筆者論證了成立共同犯罪需要意思聯絡,所以,對該學者所列舉的這些條文必須以第25條為依據,將其限縮為雙方互相知曉或通謀而提供幫助的情形,進而排除片面共犯,而不是將之理解為不存在意思聯絡的情形。這在理論上既是可能的結果之一,又有法律依據作為支撐,符合我國目前的刑法環境。
(四)片面共犯的處理方法
通過結合我國《刑法》規定進行解釋,應當得出片面共犯否定論的結論。對片面共犯的處理應分情況進行區分:片面共同正犯,若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直接以單獨正犯處理。在狹義共犯的場合,如果分則將相關教唆、幫助行為正犯化(如煽動分裂國家罪、放縱走私罪等),則可依該相關條文處理。其他情況則只能以無罪論處。對于無罪處理的結果,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此種做法會放縱犯罪分子[12]。事實上,通過比較外國刑法,我國刑法的規定確實有放縱行為人之嫌,這在立法技術上被稱為是法律漏洞,亦即立法者因疏忽未預見片面共犯的情況而對共同犯罪作了限縮規定。面對這樣的漏洞,我們當然不能單純以“罪刑法定”、“刑法沒有規定”為由直接出罪,應當通過刑法的解釋去彌補漏洞。但是當無法以解釋做出預期的結論時,就必須承認這樣的漏洞存在,不能將立法者的漏洞的風險轉嫁給國民,不能僅憑“應受懲罰”而在刑法未做出規定的情況下,罔顧罪刑法定原則強行定罪,這有悖法治理念。相應地,“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及時進行刑法的廢、改、立,以明確的法律規定宣告國家對這類行為態度的轉變,促使民眾即時調整對自己行為后果的預期,以避免觸犯刑法。”[13]
四、結論
綜上所述,因果共犯論只為共犯提供了處罰根據,并未解決共犯成立要件的問題。將共犯的因果性作為承認片面共犯的關鍵在邏輯上難以成立。行為共同說雖然在共犯本質的論述上存在合理性,但是在論述片面共犯時不存在結果的唯一性,必須結合我國刑法的規定進行解釋。以我國刑法的規定為依據,同時通過對比外國刑法的規定,應當承認我國刑法不存在片面共犯,對其處理作區別對待和具體分析,不能“一刀切”。雖然如此,在理論上就片面共犯進行構建確是完全可行的,行為共同說就是片面共犯的理論基礎,這也將為日后解決處罰漏洞而修改立法提供理論指導。只是在未做法律修改前,不能將理論上的構建或是由外國刑法解釋出的結論應用于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
注釋:
(1)因果共犯論內部存在純粹惹起說、混合惹起說和修正惹起說的分歧,三者均承認共犯的因果性,僅在共犯違法相對性的認識上產生了爭議。參見錢葉六:《共犯違法連帶性說的合理性及其應用——基于共犯處罰根據論的探討》,載《清華法學》2014年第3期。
(2)盡管對這三條規定的共犯人的分類標準有爭論,但是將其作為獨立的共犯人類型是被認可的。然而對刑法第28條規定的“脅從犯”,卻有學者認為其并非是作用分類下的共犯人類型,而應解釋為獨立的責任減免事由或寬恕事由,筆者同意此觀點。參見錢葉六:《雙層區分制下正犯與共犯的區分》,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黎宏.共同犯罪行為共同說的合理性及其應用[J].法學,2012,(11).
[2]張明楷.刑法學[M].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92.
[3]何秉松.刑法教科書:上卷[M].修訂版.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440.
[4]左堅衛,周加海.片面共犯問題的理論缺陷與立法建議[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1,(2):59-61.
[5]田鵬輝.片面共犯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46.
[6]閻二鵬.共犯本質論之我見——兼議行為共同說之提倡[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2):24-29.
[7]黎宏.刑法總論問題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66-467.
[8]許富仁.犯罪行為共同性:解決共犯本質問題的關鍵——對共犯本質學說的反思[J].法學評論,2007:(4).
[9]楊俊.海峽兩岸片面共犯理論比較研究[J].政治與法律,2008,(5):73-78.
[10]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78.
[11]現代漢語詞典[M].第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479.
[12]陳興良.論我國刑法中的片面共犯[J].法學研究,1985,(1):49-51.
[13]陳慶安.論刑法漏洞的存在與補救——兼論“以刑入罪”之隱憂[J].政治與法律,2010,(7):13.
Abstract:Theorists have disputes on whether one-sided accomplice shall be regarded as joint complicity, forming positive theory and negative theory. Theory of causal accomplice provides a basis of punishment for accomplice while it does not exact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whether one-sided accomplice constitutes joint complic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ositive theory and negative theory are the theory of joint conduct and the theory of criminal commonness. The conclusion inferred on the basis of theory of joint conduct is not specific. Combined with China's Criminal Law statutes,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theory shall be negative. Although one-sided accomplice exists in theory,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foreign criminal law cant be use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na.
Key words: causality; theory of joint conduct; joint intent; interpretative theory
編輯:魯彥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