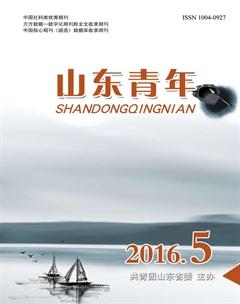論書法作品的精工
陳若冰
摘要:精工是書法作品中必然出現的一個審美范疇。精工即代表了一幅書法作品的風格,是追求工巧的。精工的書法作品同時也可以體現一個書家的書法功力之深。要達到精工,在技法上對書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必然要求書家“心手雙暢”,精益求精,但是精工不應該是書法作品所追求的最終境界,精工到了極致,走向反面,就變成是一種刻意為之。因此,一味地精工對書法作品來說是否能錦上添花,這是值得探討的。
關鍵詞:精工;尚意;樸拙
精工的書法作品,即精細、精到、精巧,自然與樸拙,野逸相對立。精工的書法作品往往是滿目鎏金與華彩地撲面而來。
書法不是一開始就走向精工的,自書法藝術產生以來的初期,比如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都是帶有原始圖案、象形意味的文字,筆畫相對減省,顯得稚拙可愛。再如西周早期的金文,鐫刻于器鼎內,厚重古意有余。這些象征書法萌芽性質的作品都帶著生意盎然、質樸大方之感。而后的書法在漫長的歷史探索中,逐漸地出現了多種風格的分支。以漢隸為例,既有《張遷碑》這樣嚴密方整又富有變化的代表作,又有《曹全碑》的秀麗靈動多姿。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時的書法有了承上啟下的劃時代意義。這其中以魏碑尤甚,其風格多樣,用筆恣肆活潑,由上繼承了漢隸,為后期唐楷奠定了基礎。
應該說,在唐代,精工的書法作品成為了一種主流。這與當時盛唐氣象密切相關。貞觀之治到開元時期,呈現了空前興盛繁榮的氣象。所謂“書至初唐而極盛”。人們不遺余力地在書法上下功夫。精工的書法作品,要求書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苦心經營,精心雕琢。早在西晉,成公綏在《隸書體》中就說:“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穩(wěn)手,必由意曉”。庾肩吾《書品》也說:“敏思藏于胸中,巧態(tài)發(fā)于毫铦”。這里不難看出,精工得到了當時書家一定的肯定以及尊重。精工是不容易做到的。這其實是要求書家意在筆先,筆畫、結構、章法都要預先設想,布局,給人以美感。
楷書在唐代達到鼎盛。鑒于這個書體的特殊性,從側面不難看出,精工是十分流行的。以唐楷歐書為例,歐體的結字幾近是唐楷中最為嚴密的,其字形結體欹側中又帶工穩(wěn),起收筆方圓兼施,含蓄內斂。歐陽詢寫此碑時已是古稀之年,才寫得如此精彩,這樣精工的楷書是需要苦練的,非朝夕能就。正是因為歐楷精工的成分多,后人在臨習之中常常感覺到束縛很大,初初臨習歐楷時,運筆是在小心翼翼中進行的,倘若是隨意地草草下筆,定有不到之處,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自然神采相去甚遠。
因而,書法作品的精工離不開書家堅實的功底。書法家在創(chuàng)作精工的書法作品時,必須使功力與之相當,使心中所想能落實到筆下所寫,這不僅需要大量的、艱苦的藝術實踐,更需要有所思、有所感、有所悟,不斷提升自己的眼界水平,才能達到作品中的精益求精。
但是,如果書法作品的精工走向極致,恐怕不是益事。明清兩代因科舉制度而盛行的館閣體就是其中一例。館閣體墨黑而光潤,它在視覺上,的確也比較美觀、大方、整潔,但由于強調楷書的共性,篇篇都中規(guī)中矩,千篇一律,缺少變化,在后期走向了呆板、僵化。流于俗氣,往往就是一個書體衰亡的開始。因此,精工到極致必然導致作品的書寫性減弱,成為一種程式化的書寫。精于工,精于巧,是不利于書家的個性、風格形成的,它會產生雷同。反觀宋代的“尚意”書風,由于受到歐陽修、蘇軾提倡“書如其人”影響,當書法作品與書家其人聯系在一起,自然精工不如質樸,裝飾不及樸素。宋黃庭堅言:“凡書要拙多于巧”。明末清初傅山曰:“寧拙毋巧……寧直率毋安排”。
宋書值得一提的是,既不完全否定唐人的法度,也不簡單地回歸晉人的隨意。在宋代歷史中,詩人、詞人的加入給宋代書法增添了新的意味。他們筆下的書法既有意趣,又能從中看出書家自身極高的修養(yǎng)。這時,人們的性情真真正正地在書法藝術中得到了解放。這是超脫了精細、工巧之上,另一番新的天地。
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正是如此。米芾最能之事在于集古字,可見,他并非排斥法度。他在作書時也不隨意下筆。他認為“信書亦一難事”。然而在他的書作中,卻能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書寫的趣味。其書作中結體收放自如,自然生動,字的欹斜搖擺,正側富有變化。可見宋人的尚意書風也并非隨意,也有意識形態(tài)的“精工”,其筆下卻是瀟灑有度。蘇軾在講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過程中就有這樣一段:“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可見,他推崇寫意,又不安排,追求信手拈來的境界。尚意書風可貴的是,這種隨心所欲,以我意寫我心,拋卻了刻意,又非隨意。如果說精工是需要技藝錘煉的,那么尚意書風便是在技藝成熟之際,還要能揮灑自如,抒情寄意。
書法作品的精工,是書家在漫長的藝術實踐里造就的。以時間為經緯,在不斷地技藝提高,巧思中體現,但過度著眼于精工,走向極致,一筆一畫都刻意安排,這其實是不可取的。書法之所以能從文字中脫離,成為一門特有的藝術,這其中就在于,書法在既定的法度中,能夠在線條中體現書家的人格內涵、自身修養(yǎng)。“書如其人”,倘若一切都成了精,成了工,不免就有造作之嫌。
相比較于精工,質樸的、率意的書風更有“初發(fā)芙蓉、自然可愛”之感。舉漢隸《開通褒斜閣道摩崖》為例,宋晏袤就評其:“字法奇勁,古意有余”。其整體章法是比較緊湊的,字的大小并沒有刻意的控制,參差有致。筆畫不是全然方直,其中又能體會到有微妙的波折。橫豎撇捺任意延展、隨意,樸質富有氣勢,有自然天成的意味。這樣的作品中所留下的可探索的空間就更多,內涵更豐厚。再如《崔敬邕墓志》,其用筆爽厲,雖一絲不茍卻富有韻致,結體方整古樸,因其不乏有隸書的筆意,雖備法度卻不刻板,不愧為北魏書中精品。
應該說,書家在初期的精工是可取的,這是一個必然的過渡階段。小至筆墨紙硯的擇取,內容的挑選,章法的布局,下筆時的構思都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在創(chuàng)作的初期,我們在對全局的把控性上還有所欠缺,太過率意去寫,很難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這個時候追求精工,即是在精益求精,十分必要。但是一個書家無法在后期信手拈來,刻意追求精工,對于作品本身就弊大于利。此時精工已不再是衡量作品質量高低的唯一標準了。當有了一定的技法支撐,就應該在作品中增其書寫性。
李白有一句詩說得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南碑《瘞鶴銘》雖為楷字,因石勢而行,越發(fā)自然而然,突破了一般楷書結體規(guī)則的束縛;北碑中王遠的《石門銘》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結體寬博大氣,適度夸張,用筆勁爽富有變化,相比一般楷書實在有趣味得多;王羲之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美,得天趣,字如其人。弘一法師李叔同的書法,淡淡如水,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寧靜致遠的禪學意味。恰如他自己所言:“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沖逸之致也”。反觀那些筆筆都是精工,苦心經營的書作,反而流于習氣、俗氣,矯揉造作。可見,書作中的自然之趣,反而能在漫長的歷史長流中給人反復推敲、斟酌、賞味的余地。
綜上所述,書法作品的精工在一方面確有其積極肯定的意義,它肯定了一個書家的創(chuàng)作功底與創(chuàng)作能力。因為能夠稱為“精工”的書作,在技法這一層面一定是比較完善的,甚至是無可挑剔的。“精工”是需要慢功夫來漸修的。但是太過執(zhí)著于精工,往往就容易忽略書法作品的抒情性。一個書家無法適意暢快地去書寫,過度追求工巧,很容易走向刻意,走向造作。因為書法作品畢竟是需要抒發(fā)書家自身的情感的,以情動人。可見,精工如果走向極致實則不可取。在書藝迢迢的道路上,最終我們都該“返璞歸真”,在樸拙中能見風骨,于書作中能見書家的真精神,能夠自然而然、給人清風徐來之感的,才是書法作品真正可貴之處。
[參考文獻]
[1]中國書法史第四卷隋唐五代卷 朱關田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9.
[2]中國書法美學 金學智 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4.
[3]書林藻鑒 馬宗霍 文物出版社 1935.
[4]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 商務出版社 1988.
[5]葉秀山 書法美學引論 寶文堂書店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