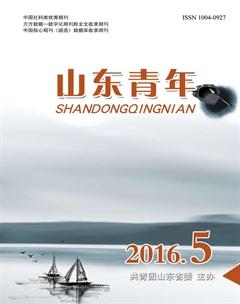日常生活審美化中出現的變異
張立偉
摘要:“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出現有其特定的現實和歷史文化語境,然而消費時代的審美并非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場美學潮流在帶來新的美學現象,營建了新的美學范式的同時,仍然有諸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本文主要從宏觀的角度思考消費時代日常生活審美化引發的審美問題——藝術生產過程中也出現了與傳統藝術創造相悖逆的問題:藝術的庸俗化與藝術的商品化現象。
關鍵詞:日常生活審美化;藝術庸俗化;藝術商品化
消費時代的到來,使得審美從高不可及的象牙塔中走出來,當審美走下圣壇,當消費取代政治成為藝術向前發展的邏輯時,它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猶如洪水猛獸吞噬著傳統審美文化,不僅如此,它也在重新謀劃傳統審美文化的發展道路,以強大的文化壓制力不斷改變藝術的面貌。“日常生活審美化”折射出審美回歸生活世界的趨向,現代人面對審美與生活界限日益模糊的現狀,有的學者投以質疑的眼光,有的學者對“日常生活審美化”持以親和的態度。由于“日常生活審美化”孽生于活躍于當前的“后現代社會”,相當于波德里亞提到的消費社會。因此,審美、日常生活便與消費文化發生關聯。商業運作背景的存在,使得“日常生活審美化”變得迷亂而復雜,因此任何片面的贊揚或否定都會顯示出不足,對“日常生活審美化”我們應辯證地看待和理解,給予客觀、理性、公正的評價。
現代社會人類的審美觀念轉向感知領域,美開始轉向以感覺為核心的生產,追求視覺快感成為人們基本的審美需求。更為可怕的是人們找不到美的風向標,陷入了迷亂的審美幻覺中,誤以為奢侈的、浮華的、絢麗奪目的、能夠帶來感官滿足的對象就是美的,比如在都市環境中,審美化意味著浮華、炫目、時尚的風行。而在自我設計中如(美容、美體),審美化則意味著漂亮、生活時尚化。
客觀事物的美,不論是鮮亮的色彩、迷人的形態總是會引起人們感官上的愉悅,我們不能否認美必須具有一定的感性形式,美感確實與官能感覺密切相關。美的最初含義里確實含有能引起人的感官愉悅的成分,當下散落在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的美更多地帶有愉悅感官的庸俗色彩,緣于“舊常生活審美化”孽生于消費主義的土壤,審美與消費的聯姻勢必使傳統審美沾染功利氣息。文化工業與生俱來地具有一種培育浮華美的傾向,從商店櫥窗里各種閃亮的衣飾到T臺上富有魅力的性感女郎,從設計精美的時尚畫冊到奪人眼球的商品廣告,文化工業力圖以一切別出心裁的形式和變化翻新的內容吸引大眾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最終服務于自身運行邏輯。消費主義享樂傾向正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蔓延開來,與此相應,日常產品的庸俗化傾向愈演愈烈,這種無限膨脹的浮華之美在激起大眾潛在的欲望的同時,也就以其夸張虛假的視覺效果鈍化著大眾的審美感受力。
藝術作品進入日常生活,被日常生活的保守性、惰性所同化,不免沾染庸俗功利的色彩。傳統審美中,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嚴格受制于人的內在的自然的尺度,這是人類理解外在世界的內在規定。然而在當代文化工業生產中,技術的進步具有放大一切的無限可能性,打破了把握世界的自然的藩籬和界限,使得本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在公共領域的東西淋漓盡致地暴露出來。技術自身的強大的話語權拆除了私人話語空間與公共話語空間之間的高墻,以往蜷縮在私密空間的內容:色情、暴力、虛榮,攀比等一系列暴露人性丑的東西被毫不留情地推到了生活世界的前臺。藝術生產沾染了庸俗化的色彩,我們會發現當代藝術生產中充斥著兩種有著深刻關聯的欲望:暴露與窺隱,文化工業以其特有的視覺震撼力刺激并滿足大眾欲說還休的欲望,大眾不顧一切地窺視,從大眾和文化工業相互對望的眼神中,彼此秘密就已心照不宣。
可見,日常生活主體并不能通過藝術作品與對象、與人生、與世界建立起自覺的審美關系,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數時刻里,電影、電視、廣告等大眾傳播媒介也不能激起日常生活主體對生命意義的沉思、對人生價值的體認,更多地被當做無聊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和彌補。悅耳悅目的精神性被感官享樂的物質性所替代,當傳統體驗過程中應有的感官愉悅被感官快適所替代,藝術作品便缺失了能夠營養其生命的精神養料。
除此之外,在技術革命浪潮的推動下,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奔向日常生活的藝術還表現出商品化的傾向。藝術“不再是單獨的、孤立的現實,它進入了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現實,都可歸于藝術之記號下,從而都可以成為審美的。”\+①當下的藝術魯莽草率地作出與現實擁抱的決定,對審美和消費主義的聯姻不加反省,藝術大眾化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商品化的傾向,藝術的商品化折射和傳播的是資本對技術的操縱,從而也凸顯了藝術在當代文化生產中的令人失望的一面:貪婪性。藝術的商品化由來已久,科技工藝在其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伴隨著藝術作品幾近瘋狂地無休止地復制生產,藝術的商品化過程接近頂峰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技術使作品進入自己的事實,藝術作品一腳踏進了形式的王國,“這種形式與藝術在社會中的新職能是相適應的:提供節目、更深的、也許更真實和更美好的東西;滿足平常工作和娛樂中無法滿足的需要,因此是令人愉悅的。”\+②這正如馬爾庫塞指出的,藝術發揮一種超越性的作用并成為與現實現存秩序同流合污的力量,商品化的藝術為大眾創造一個與真實的現實大相徑庭的另一個現實:充滿快樂、美、激動。日常生活因美學因素的蔓延獲得一種形式,新形式的獲得使得現實成為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潛心制造的審美氣泡,藝術制造了一個美的幻想王國,“是在不自由的現實之上那種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的氣球。這種想象的生活似乎超越了現實,但實際上卻是在一個虛幻的形式中逃離了現實。”\+③藝術用幻想的令人迷醉的幸福虛假性地構筑了一個避難所,商品化的藝術成為現實的裝飾品,“藝術是異化”。\+④
歸根結底,技術理性的背后是資本的操縱,現代社會是一個被物質充斥和占領的世界,空氣里彌漫的是消費氣息,消費自然而然成為安置在日常生活上空的氣溫調節器,日常生活憑借美學因素的浸染只在表面上呈現出安然有序的樣態。現代文化的矛盾是物質文化日益發達,精神文化日益萎縮,傳統的精神生產葆有的特性已被神秘而又神性的技術力量驅趕得煙消云散,我們看到精致、靈性正逐漸被淡化,藝術不再是精神性、飽含靈性的創作,己然失落的傳統的精神內涵。
最后,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精神意義的缺失為我們審視當前的文化處境打開了一扇窗戶,我們正處在社會文化轉型的過程中,站在文化轉型的門檻上,我們不難發現對人生意義的終極追尋的忽略和擱置正凸顯出技術一工具理性對感性生命個體心靈的侵蝕以及對主體精神自由的壓制和剝脫。
[參考文獻]
①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一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頁。
②湯因比等:《藝術的未來》,王治河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
③楊小濱:《否定的美學—法蘭克福學派的文藝理論和文化批評》,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
④湯因比等:《藝術的未來》,王治河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