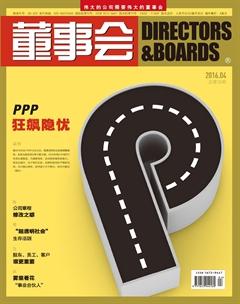債轉(zhuǎn)股是苦藥而非蜜糖
史晨昱
債轉(zhuǎn)股實(shí)施的深層次意義不僅僅是企業(yè)財(cái)務(wù)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換, 更為重要的是要進(jìn)行企業(yè)內(nèi)部治理結(jié)構(gòu)的再造,必然涉及公司經(jīng)理人員的調(diào)整, 甚至是大換血,或者大面積的公司裁員,否則起不到應(yīng)有的作用。圍繞著金融資源支配權(quán)及企業(yè)控制權(quán),利益主體將展開一系列利益沖突和斗爭的博弈過程。
有消息稱,中國將于近期出臺相關(guān)文件,允許商業(yè)銀行在不良資產(chǎn)處置領(lǐng)域?qū)嵤﹤D(zhuǎn)股,以支持實(shí)體經(jīng)濟(jì)。而在實(shí)際操作中,被債務(wù)壓力圍困的企業(yè),更迫切地希望股轉(zhuǎn)債政策的實(shí)施。日前,華榮能源(即原熔盛重工)已先一步提出了該公司債務(wù)處理計(jì)劃,擬向中國銀行發(fā)行27.5億股股票以抵消27.5億元債務(wù)。此次債轉(zhuǎn)股完成后,中國銀行將成為其最大股東,持股比例將高達(dá)14%。
債轉(zhuǎn)股對于中國金融體系并不陌生。1998年金融危機(jī)中,國有企業(yè)大面積虧損和銀行巨額爛賬,推動政府實(shí)施了以債轉(zhuǎn)股為核心的不良資產(chǎn)處置框架。1999年國務(wù)院公布《關(guān)于實(shí)施債權(quán)轉(zhuǎn)股權(quán)的若干意見方案》,并推薦了601 戶債轉(zhuǎn)股企業(yè)。由于實(shí)施于上述背景,債轉(zhuǎn)股一直被作為特定時期的產(chǎn)物,對其普遍存在著認(rèn)識上的誤區(qū)。其實(shí),債轉(zhuǎn)股是不良處置的常見方式之一。實(shí)施債轉(zhuǎn)股的目的,是以剝離不良資產(chǎn)來減輕企業(yè)和銀行負(fù)擔(dān)為契機(jī),贏得時間來完善國企經(jīng)營機(jī)制和治理結(jié)構(gòu),恢復(fù)和重建銀行企業(yè)間正常的信貸關(guān)系,最終使整個企業(yè)步入市場化正常發(fā)展軌道。
當(dāng)前去產(chǎn)能推升信用風(fēng)險,資產(chǎn)質(zhì)量壓力再次成為懸在銀行頭上的“達(dá)摩克利斯之劍”。但中國處在金融發(fā)展的大時代,金融混業(yè)步伐加快,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風(fēng)生水起,機(jī)構(gòu)投資者大量涌現(xiàn),為化解金融風(fēng)險提供了寬松的土壤。與之相適應(yīng),中國銀行體系治理不良資產(chǎn)應(yīng)更具差異化,更加多樣性,應(yīng)涌現(xiàn)出更具時代特色的新方法。重啟債轉(zhuǎn)股,無疑是這種思路的具體體現(xiàn)。債轉(zhuǎn)股應(yīng)還原為一種不良資產(chǎn)處置的新型渠道,而不是特定時期對僵尸企業(yè)的行政式捆綁安排。雖然根據(jù)現(xiàn)行《商業(yè)銀行法》,商業(yè)銀行在境內(nèi)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jīng)營業(yè)務(wù),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chǎn)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jī)構(gòu)和企業(yè)投資,然而隨著混業(yè)經(jīng)營的推進(jìn),商業(yè)銀行各類分業(yè)子公司為債轉(zhuǎn)股提供了合法的實(shí)施條件。
與上世紀(jì)相比,本輪債轉(zhuǎn)股的內(nèi)外部環(huán)境與體制背景已經(jīng)大相徑庭。首先,不良資產(chǎn)的風(fēng)險可控。中國銀行業(yè)不良貸款率從1995年的21.4%上升到2000年的29.2%。2015年年末,銀行業(yè)不良貸款余額12744億元,不良貸款率1.67%。其次,債轉(zhuǎn)股主體的預(yù)算硬約束已極大增強(qiáng)。上世紀(jì)末,中國以銀行向四大資產(chǎn)管理公司劃轉(zhuǎn)資產(chǎn)的方式處理銀行壞賬,不良貸款產(chǎn)生的最大原因是政企不分。如今無論是商業(yè)銀行、資產(chǎn)管理公司,還是貸款企業(yè),都已經(jīng)成為規(guī)范的獨(dú)立法人,并且大多已經(jīng)上市成為公眾公司。當(dāng)前產(chǎn)能過剩行業(yè)最大的問題并非產(chǎn)能過剩,而是產(chǎn)能過于分散,導(dǎo)致一系列惡性競爭和產(chǎn)能分布不合理等結(jié)構(gòu)問題。這決定了債轉(zhuǎn)股只是不良資產(chǎn)處置手段的必要補(bǔ)充,而非未來的決定因素。
不過,新事物的運(yùn)作總有兩面性。債轉(zhuǎn)股代表了中國商業(yè)銀行與企業(yè)之間關(guān)系的新變化。銀行不良資產(chǎn)可以采取多種保全方式, 這些措施包括催收、一般性重組、債務(wù)重組、債轉(zhuǎn)股和破產(chǎn)起訴。這五種保全措施是按照企業(yè)問題的嚴(yán)重程度從輕到重的順序排列的。其中債轉(zhuǎn)股意味著常規(guī)回收已經(jīng)難以奏效。債轉(zhuǎn)股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即重組成功可能使得回收明顯高于預(yù)期值, 而重組不成功可能會再度陷入破產(chǎn)清盤以至回收更少。從理論上講, 這項(xiàng)措施實(shí)施的深層次意義不僅僅是企業(yè)財(cái)務(wù)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換, 更為重要的是要進(jìn)行企業(yè)內(nèi)部治理結(jié)構(gòu)的再造,必然涉及公司經(jīng)理人員的調(diào)整, 甚至是大換血,或者大面積的公司裁員,否則起不到應(yīng)有的作用。圍繞著金融資源支配權(quán)及企業(yè)控制權(quán),利益主體將展開一系列利益沖突和斗爭的博弈過程。因此, 債轉(zhuǎn)股對債務(wù)人來講是一劑苦藥,而絕非巧克力糖。此外,商業(yè)銀行將不良資產(chǎn)轉(zhuǎn)變?yōu)楣蓹?quán)時,其資本占用將增加。根據(jù)《商業(yè)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規(guī)定,商業(yè)銀行被動持有的對工商企業(yè)股權(quán)投資在法律規(guī)定處分期限內(nèi)的風(fēng)險權(quán)重為400%,而商業(yè)銀行因政策性原因并經(jīng)國務(wù)院特別批準(zhǔn)的對工商企業(yè)股權(quán)投資的風(fēng)險權(quán)重為400%,遠(yuǎn)高于貸款風(fēng)險權(quán)。
債轉(zhuǎn)股安排是一個十分廣泛且復(fù)雜的體系,它一方面化解風(fēng)險, 另一方面又可能滋生新的風(fēng)險。中國的債轉(zhuǎn)股運(yùn)作應(yīng)該賦予的深層內(nèi)涵是對債轉(zhuǎn)股中涉及的相關(guān)利益主體進(jìn)行重新調(diào)整,并按照市場經(jīng)濟(jì)規(guī)則完善企業(yè)治理機(jī)制和現(xiàn)代銀行制度,盡可能減少債轉(zhuǎn)股風(fēng)險和損失。債轉(zhuǎn)股在推進(jìn)國有企業(yè)和國有銀行改革的同時, 還對國企和國有銀行制度變遷的廣度和深度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依賴。為了確保債轉(zhuǎn)股最終預(yù)期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應(yīng)總結(jié)國內(nèi)外債轉(zhuǎn)股的操作模式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為最小化債轉(zhuǎn)股風(fēng)險設(shè)計(jì)更為科學(xué)的機(jī)制安排,如嚴(yán)格掌握債轉(zhuǎn)股企業(yè)的甄選條件和標(biāo)準(zhǔn),以及建立與完善債轉(zhuǎn)股中的監(jiān)督和信息披露機(jī)制,從而硬化債轉(zhuǎn)股的產(chǎn)權(quán)約束, 防范道德風(fēng)險和內(nèi)部人控制造成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