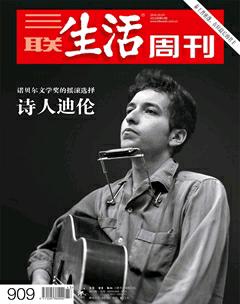鮑勃?迪倫與哲學
薛巍
美國作家多克托羅在《經典》一文中說:“我對歌曲想得越多,它們就越變得不可思議。它們作為某些時期的精神史留存在我們心里;憑著歌詞和一行行旋律,它們有能力再現戰爭及其他災難、精神歷程、經驗的收獲,還有,如同祈禱一般,超越損失的撫慰。”一些哲學教授認為,鮑勃·迪倫的歌曲還能啟發人們做更深入的思考。
存在主義的迪倫
2005年,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彼得·威尼士主編了《鮑勃·迪倫與哲學》一書,收入了18位哲學家對鮑勃·迪倫的道德立場、性別觀、宗教觀的分析。他們首先要解釋,為什么有理由這么做?哲學是理性地思考的藝術,鮑勃·迪倫是一個歌手或詩人,而詩人比哲學家更多地依賴直覺。哲學家凱文·克雷恩說:“跟所有偉大的詩人一樣,迪倫努力言說那些不可言說的東西,去把握模糊的情緒和稍縱即逝的圖像。但跟所有復雜的藝術家一樣,迪倫在依賴直覺和潛意識中的情緒時,并不反哲學或反概念。說迪倫不是哲學家,并不等于說他的許多歌曲沒有哲學性,他的許多歌曲都能激發某種哲學思考,比如《每一粒沙子》就能讓人思考命運、偶然、自由等主題,還有的歌曲則會讓人思考責任和正義問題。”
美國歷史學家杰弗里·布雷謝斯(Jefrey Breshears)說,迪倫留下了一筆存在主義的遺產。他在《鮑勃·迪倫的存在主義之旅》一文中寫道:“‘貓王是一個聲音,但主要是一個形象,而且這個形象永遠被冰封在了50年代。披頭士60年代主導了流行音樂和文化,那時他們的影響令迪倫相形見絀,但慢慢地他們的地位開始衰退。迪倫的影響卻沒有降低。他比20世紀其他歌手吸引了更多的學者的注意。作為歌曲創作者和唱片藝術家,迪倫的職業生涯有著驚人的遺產。但更重要的是他對美國文化的普遍影響,即他的哲學遺產。”
布雷謝斯承認,迪倫不是正式的哲學家,也不是一個特別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但他認為迪倫對哲學的方向產生了影響。這在娛樂界人士中確實比較罕見:“‘貓王跟他之前的辛納特拉一樣,沒有留下什么哲學遺產。披頭士代表了不受約束的年輕人的享樂主義和藝術家的放縱——這兩者都沒有創造性或不值得注意。滾石樂隊跟馬龍·白蘭度等流行偶像一樣,勤奮地樹立反叛、虛無主義的形象,但這種不成熟的、反社會的立場只會感動那些天真的青少年和永遠長不大的成年人。類似地,麥當娜和小甜甜撩人的裸露癖也許會展現她們的靈魂,但對思想領域毫無貢獻。推動文化的是觀念,迪倫的貢獻就在觀念領域。迪倫呈現了一個存在主義的反英雄的形象,他是文化上的反叛者,但他是一個有奮斗目標的反叛者。起初,他的目標是60年代初標準的左翼的議程:和平、正義和民權。后來他的目標是他個人的自由。雖然他60年代中期的一些音樂好像是在歌頌混亂,但他從不是哲學上的虛無主義者。他是一個好戰的獨立的存在主義者,他規劃自己的人生道路,不響應任何更高的權威。”
后現代主義的迪倫
鮑勃·迪倫不僅在某一方面跟薩特、跟克爾凱郭爾等存在主義者相通,還有人說,他跟德里達、福柯等也有不謀而合之處。美國哲學家喬迪·羅切雷奧(Jordy Rocheleau)說:“迪倫的抗議歌曲展現了啟蒙運動的社會哲學,而他那個階段之后的作品則引入后現代主義的政治洞察與含混。”
啟蒙哲學家康德號召人使用理性不斷地提升自己,并擴展自由和確保幸福。理性的規則對所有人都一樣,所以應該平等對待所有人。康德相信人類的反思和社會行動能夠克服那些損害自由、平等、和平和幸福的傳統與權力。康德知道人類距離這些理想還很遠,但人類有能力理解不公正并實現進步。迪倫早期的抗議歌曲指責美國的體制未能達到他們聲稱的啟蒙運動的平等理想。他在《颶風》中寫道:“看著他遭受那些顯而易見的陷害,我不禁為生活于這片土地而感到羞恥。在這里公正是兒戲。”他意識到進步面臨強大的阻力,但他認為道德反思最終會指明正確的道路:“如果你不能大聲地反對這種事情,這種不公正的罪行,你的心靈就充滿了灰塵。”

?1969年8月31日,英國懷特島舉行國際音樂節期間,一名參加音樂節的男子正在看晚報。當天的晚報頭條是關于鮑勃·迪倫的
后現代主義不像啟蒙運動那樣,認為普遍的真理和價值觀是人類進步的基礎。迪倫放棄抗議可以說是一種后現代的轉向。他突然開始懷疑平等原則的意義:“我說出‘平等一詞,就像是婚禮誓詞,但我那時太老,現在我比那時年輕。”這段副歌的含義是,平等的理想很天真,不能像他曾經以為的那樣構成清晰的進步之路。
迪倫跟德里達是同代人,他跟法國哲學家一樣懷疑理性的理解能力。他雖然博覽群書,但也搞不懂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很迷惘。宗教、教育和政治除了令人困惑,也提供不了什么東西。“傳教士講述邪惡的命運,老師們說知識就在手邊。”在荒蕪的街區,盲眼的行政官提供不了什么幫助。西方的理性和文化上的偶像們都顯得很滑稽,或者筋疲力盡。莎士比亞在小巷里跟一個法國女孩交談,愛因斯坦扮成羅賓漢,伽利略的數學書被扔向戴利拉,龐德和艾略特只能用暴力解決他們的紛爭,“在船長的塔里打了起來”。
啟蒙運動有一個教義是,人類的理性能帶來進步和人類的逐漸提高。迪倫對進步表示質疑,他宣稱人類頭腦的成就如登月實際上埋下了毀滅的種子:“人類發明了他們的厄運,第一步是觸月。”人性不但沒有不斷提高,世界反而被暴力統治著,“人的自我膨脹了,他的法則過時了,他們不再運用這些法則,每個人的良心都很卑鄙、墮落”。
后現代主義者一個問題是,他們的行動跟他們的結論是矛盾的,按照他們的看法,就不存在批評現有社會的立場,但他們一直是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們抗議啟蒙運動的理想,那就等于認為沒有這些原則會更好。這仍然包含價值判斷。他們批評用理性去追求自由,但他們仍試圖把人類從理性中解放出來。為啟蒙運動辯護的人說,后現代主義有著內在的矛盾,它預設了它所批評的理性和自由的理想。后現代主義有沒有辦法既開展批評又保持一致呢?一個辦法是,只描述社會結構以及理性的限度,但不提出改革方法,由此避免在否認進步的可能性的同時展示進步的前景。可以把這種方法叫作描述性的后現代主義。這正是迪倫在《沒事兒媽媽(我不過是在流血)》《瘦子之歌》等他最陰郁的那些歌里描述的圖景。他拒絕做道德判斷,并且不會說既然沒有好壞,我們就應該相互寬容。
德里達和福柯都試圖在不主張任何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真理的情況下進行社會批評。德里達稱這種做法為解構,因為它揭示真理主張中的含混和權力。福柯把這種批判立場稱為問題化,不用明確的理想來評判社會,而是展示當前理想中包含的矛盾、含混和操控。但無論是解構還是問題化,都包含某種道德判斷。提出應該拒斥當前的理想,就是說我們應該擺脫錯誤的理想,我們可以做出其他更好的選擇。迪倫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雖然他遠離了抗議歌曲,但他的作品仍然在關心自由和正義。他在《政治世界》中感嘆“智慧被丟進了監獄”“勇敢成了過往之物”,在《黑眼睛》中感嘆“美沒被認出來”,說明他相信美仍然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