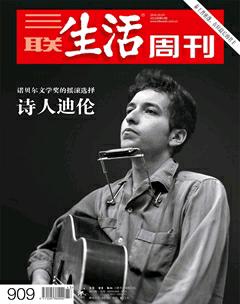盜獵鳥網:蘆葦蕩里的殺戮
劉敏
這次在天津僥幸被解救下網的那些小鳥,馬上又會飛到江蘇連云港、江西鄱陽湖、廣東雷州半島……一路等待它們的,也許還是場生死劫。
蘆葦蕩里的鳥網
下午16點半,天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漸漸著急起來。他領了兩車的志愿者到天津寧河區郊外,已經轉了半個多小時了。

10月11日,天津林業部門的工作人員在市郊清理大量鳥網,救助還存活的候鳥
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兩側是見不到邊際的荒地,蘆葦長了一人多高。晚風一吹,輕柔的蘆花左右搖晃,連聲音都沒有。王建民把車開上了一條土路,往蘆葦蕩的深處駛去:“這里面一定有鳥網。”
在最近的十幾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鳥的鳥網成了全國熱點新聞:從9月29日開始,在國慶期間,57歲的攝影師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們發現了兩大片、有2萬多米的鳥網。此前的幾年,志愿者們也會在秋天例行地去尋找林地、稻田里農民們偷偷豎起的鳥網,“每年拆一兩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蘆葦蕩里,天津人王建明完全被震驚了:他知道鳥網肯定屢禁不止,但沒想到能發現2萬米之多,上面足足掛了5000多只死鳥,近3000只活鳥,而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部分。
這些鳥,都是秋季途經天津的候鳥。
全球一共有8條候鳥遷徙路線,其中有3條經過中國,又有2條途經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灣濱海濕地是鳥類群集的天然補給地。其中東亞-澳大利亞遷徙路線有178種候鳥,是鳥種最多的一條路線。每年農歷八月十五開始,大批最遠來自西伯利亞、阿拉斯加的鳥群南下,在這里停歇、覓食,陸陸續續再向南飛去,最遠可以到達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
候鳥是什么樣子的?很快,蘆葦蕩用一種最慘烈的方式告訴了我們答案。
王建民把車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遠鏡下,他看到了蘆葦叢中樹立的竹竿。再一找,在完全無人開發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條明顯的小路。我們拿著剪子下了車,沿著小路走進去,很快就發現了一條分叉道:水溝里藏著一座木板做獨木橋,過了橋一拐,蘆葦叢中赫然出現了一塊2米寬的空地。
第一眼只能看見竹竿,再定睛一看,才發現竹竿間掛著一層輕薄的絲網,每根線都跟頭發絲一樣細,織著2厘米見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樣,“霧網”,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鳥一頭撞上,稍一撲騰就被纏住了羽毛,再掙扎,就會越纏越緊,毫無生還可能。
眼前的鳥網上已經粘住了幾十只小鳥,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類、雀類的小型鳥。垂著頭一動不動的是死鳥,剛剛撞上的都在撲騰,翅膀徒勞地飛快顫動,那是一種眼看著就能體會的絕望。
“天啊!”剛剛還在閑聊的志愿者們全驚住了。
所有人此前都在新聞里見過鳥網的照片,當沖過去把掙扎的小鳥抓住,心里頓時還是一顫: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鳥暖熱的體溫,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纖弱,驚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撲通撲通的心跳——這是一條正在消逝的生命。
沿著最初的小路繼續向里走,大約每隔50米就有一個分叉,每個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鳥網。捕獵者用除草劑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許因為近日嚴厲的清剿行動,鳥網下沒有發現誘鳥器、電池和做誘餌的籠鳥,獵捕者只留下這些鳥網懶得收走。
天漸漸黑下來,鳥網越找越多,風輕輕地吹動著霧網,帶著死鳥來回搖晃。就在大城市的郊外,安靜的秋天傍晚,這些只用竹竿和絲網豎起的鳥網,正在造成一場無聲的、巨大的殺戮。
野味
我從鳥網上剪下來的第一只鳥是只棕頭鴉雀,這種小型雀比一個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溫順,還是已經掙扎到脫力,小家伙老老實實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動不動。
鳥網已經纏得它全身都是,脖頸下、羽毛里面都是網,兩只爪子因為抓撓纏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點一點挑開。這個過程尤其費人工,志愿者們解開一只鳥平均要七八分鐘,最后還要拉開翅膀,檢查有沒有任何遺留,否則小鳥一旦放飛,還是會因為無法獵食而迅速死去。
直到網全解開,鴉雀嚇得還是不敢動,我把它放在地上,幾秒鐘后小鳥才反應過來,撲啦啦飛走了。
更多的鳥已經死了,有些鳥剪到一半就已經沒了呼吸。掙扎時間一長,小鳥就會因為脫水、懸吊而死。再兇猛的鳥也不行,我們解下一只棕背伯勞,體長約30厘米,伯勞是一種攻擊性強的小猛禽,擅長打斗,解網的過程中一直大聲叫個不停,還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們不解救,這只伯勞最后也只能困在鳥網上等死。

王建民判斷這只奄奄一息的蒼鷺是誤食了農藥毒餌
看著長網上遠近高低、正在無助掙扎的小鳥,我實在很難想象:捕鳥人每天來摘鳥時,難道是抱著一種豐收的心情嗎?
跟志愿者們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盜獵者、鳥販子對野生候鳥的態度,就像是對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
就在10月12日當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們剛剛在唐山市蘆臺經濟開發區海北鎮小海北村端掉了一個窩點。蘆臺經濟開發區地處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內的唯一一塊“飛地”,對于候鳥來說,這也是一個“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訴我,越是在這種責權難以判斷的地界,越容易有鳥販子。
一大早,志愿者們守在鳥販子家外,雖然有線人確鑿的報告,但大家不能私闖民宅,等著唐山林業行政綜合執法大隊和公安部門的人員到齊才能一起行動。從外觀看,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戶人家,進門后推開一間老房子的房門才聽到嘰嘰喳喳的鳥叫聲。
這簡直是一間養雞場:屋子里彌漫著濃重的鳥糞味兒,長方形的鳥箱一直堆到了屋頂,每個有1米長,半米寬,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個箱子里有1245只活鳥,每七八只鳥放在一起。這些野生鳥完全不能適應如此狹小的生活空間。不管有沒有人在,那些南方朱雀、黃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來跳去,叫個不停。
鳥箱里裝著谷子和飲用水,目的是給這些候鳥催肥。經過長途跋涉,候鳥到天津時已經掉了很多體重,人工飼養谷子、打抗生素后,這些籠中鳥的腹部會長出一層油脂,體重一增加,飼養者就會把它們放在塑料袋中悶死,冷凍,變成鳥干。
在房間的兩個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凍的鳥干,還有已經扒了皮無法辨認的鳥肉。
在蘆葦蕩的鳥網上,我們摘下了雨燕、紅脅藍尾鴝、鴉雀、紅喉歌鴝、普通朱雀等鳥種,其中還有一只是觀鳥愛好者也很難觀測到的文須雀。在圈養窩點里,除了活著的黃胸鹀、紅腹歌鴝單獨圈養,其他的小鹀、青頭鹀、紅頭鹀、伯勞等,統統被混雜在一起,因為最終的用途已經跟它們的品種毫無關系了。
這些鳥干都會被運到廣東等南方省份,變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廣東民間認為“寧食飛禽一兩,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是黃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試圖馴服禾花雀,但一旦關進籠子里,這種小鳥就變得顏色黯淡、萎靡厭食,這本來是野生動物難以馴養的表現,卻又被民間推論為禾花雀是“天上人參”的迷信結論,又臆測出禾花雀能補腎壯陽的功效。
在這個家庭飼養窩點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黃胸鹀。在天津,鳥販子收一只黃胸鹀是15塊錢,運到廣東,再以每只30元的價格賣給飯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已經將禾花雀(黃胸鹀)由“易危”級別提升至“瀕危”級別,與大熊貓同一級別。但在廣東,最后端上餐桌時,這種瀕危鳥類,只不過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檔野味。
供給和需求
蘆臺這家飼養點的主人跑了,當天一共收繳了近4000只鳥,活鳥被當場放飛,鳥干被帶走,將做無害化填埋處理。
“這只是個小鳥販子,大的,我們今年抓到過有上萬只的。”王建民說。
現場的每個記者都在問,這個逃竄的鳥販會被處以什么刑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個規模的倒賣野生鳥類已構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獵野生動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獵區”或者“禁獵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獵的,應認定為非法狩獵罪。犯非法狩獵罪,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這看起來并不是多么嚴重的判罰。王建民說,農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鳥網,如果運氣好,一天就能賺到2000塊錢。“他們種棉花,一畝地一年賺2000塊已經算暴利了。”即便志愿者反復宣傳,野生鳥會捕食昆蟲、保護農田,但捕鳥的金錢刺激看來更加直接。
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鳥者打過交道,自己也張過網、收過鳥,他知道真正架網的都是純粹的本地農民。“地地道道老實巴交的農民,都不是壞人。一年靠捕鳥能賺兩三萬元,就算被逮了,他們壓根兒不覺得這事兒丟人,覺得捕鳥就是老祖宗傳下來靠天吃飯的手藝。”
“就是弱勢群體里最弱勢的一群人!想想你們去拆網,起早貪黑鉆大野地里多費勁,他們去摘鳥也費勁,有錢人誰干這個?”李青說。
王建民今年幫著林業局、公安局搗毀了五六個窩點,有些人工催肥點的情況讓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腦血栓,沒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鳥養鳥。第二家也是個農戶,女的一看我們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開始嚎啕大哭,嚇得不知道怎么辦;第三家老人有腦梗,在床上還打點滴呢,家里聽了鳥販子的話,給他們養鳥賺錢,我臨走都想給他塞幾百塊錢,又覺得以我們的身份做這個不合適。”
警方去了這種黑窩點,必然是要放飛活鳥,沒收死鳥和飼料,并把所有的鳥籠拆毀。這幾個窩點都是中間渠道,從捕鳥的農民手里6塊錢一只收了鳥,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塊錢一只再賣給上游鳥販。如同養雞一樣,這些人以為自己賺的就是個辛苦錢,卻沒意識到從收鳥那一刻起,這就是個違法的勾當。
“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糧食,偷家里養的小雞,大家都知道這不對。現在偷著抓天上飛的野生鳥,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天上白給的,自己沒偷沒搶啊!”李青說,包括很多基層警察也是這個心態,站到鳥網旁邊,也不知道這有什么好管的。
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劉懿丹一起去遼寧盤錦做巡護,發現一戶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個鳥網,劉懿丹一定要報案,李青看著快80歲的戶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覺得讓老頭把網摘了就行了,沒必要找警察。兩人吵了半天最后還是報了警,結果警察幾小時后才來,“用一種看神經病一樣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現在也總愛把這件事兒拿出來開劉懿丹的玩笑,這是一種很現實的倫理沖突:基層警方就是覺得志愿者在小題大做,他們對盜獵沒有概念,而盜獵者也覺得飛到我院子里的鳥,難道不就是我的?
得利最大的是中間做批發的鳥販子,他們通過飼養點分散了自己的責任,又因為眼線眾多,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罰跟每年倒賣野生候鳥的暴利相比完全沒有震懾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紅喉歌鴝,甚至可以賣到10萬塊錢。
跟盜獵者、鳥販子高效產業化的流水線一條龍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顯得效率格外低。在隨后的幾天,我們隨著王建民每天早上8點鐘出門找鳥,在天津漢沽區周圍,鉆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區,在每一片途經的荒地、蘆葦蕩、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經質地用望遠鏡、航拍無人機在田野中尋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時整整一天也毫無收獲。
此前參加巡護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劉懿丹等志愿者一車三五個人,早上4點就出門,在捕鳥的高峰期時間去堵鳥網,很多鳥網是流動性的,如果七八點再去,獵捕者已經把鳥裝好了拿去賣了。
今年因為新聞集中報道,很多記者、志愿者都集中過來,找網的隊伍浩大起來,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篩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幾名主力的誤工,都是不小的開銷。
況且,林業部門的人手也不夠,有些區的林業站只有兩三名員工,完全查不過來。寧河區林業局的執法小伙兒告訴我,天津除了薊縣,其他區域都沒有森林公安。林業局只有行政權沒有執法權,抓到人沒法拘留,也會讓執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礎的信息篩查,幾乎都是依賴志愿者們自己去大海撈針地找。
在蘆臺的窩點,后院的志愿者們一邊把鳥籠踩塌,一邊恨恨地說:“這群人發財也是邪財,早晚有報應!”
前面的主街上,周圍居民圍在警車邊,他們臉上沒有驚訝,也沒有憤慨,就是單純地看熱鬧。一包志愿者買的勞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撿走,火速幾個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鳥干裝在麻袋里,放在前廳,總有村民進去動一動,被志愿者呵斥再訕訕地走出來。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臺階上守著幾麻袋鳥干:怕沒人看著,轉眼就被拎跑了。
斗爭的智慧
從9月29日到10月15日,志愿者們在天津的鳥網上共發現9只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東方角鸮,其中有5只已經死亡,余下的4只當場放飛了3只,1只因軟組織挫傷無法飛行,被送到了唐山的救助站。
在唐山海港區大清河鹽場的野生動物收容救治站,我看見了那只最近被新聞反復播放的東方角鸮。
東方角鸮是中國體型最小的一種貓頭鷹,成年角鸮也只有人兩個拳頭疊起來這么高,以昆蟲、鼠類、小鳥為食。站長田志偉每天給這只小貓頭鷹喂雞肉條,十幾天下來,小家伙已經精神多了。
47歲的田志偉從2010年開始全職做救助站,救治天津、唐山等地受傷的野生鳥類,就在今年6月份,科研人員從撿鳥蛋人手里沒收了209枚反嘴鷸鳥蛋,全都送到了田志偉這里。老田和妻子用孵化器一共人工孵化出80多只幼鳥,“晚上1點睡,早上4點起,一天喂6遍”。最后有一半都成功野化放飛,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人工孵化反嘴鷸的紀錄。
現在的救助站里有救治的雕鸮、白鷺、黑天鵝、孔雀、翹鼻麻鴨、反嘴鷸等受傷野生鳥,田志偉從鹽場引過來淡水,自己挖了一條水系,幾個帶網的池子分別給不同鳥種做野化。他興致勃勃地讓我看監控錄像,每天后半夜,救助站的露天水池里就飛過來一大批水鳥,密密匝匝地在水面上游來游去,一大早5點鐘,又撲啦啦成群飛走了。“到了冬天水鳥更多。”田志偉很得意,“來我這白吃、白喝、白住,哈哈!”
這些監控其實也是田志偉保護自己和病鳥的工具:從我們進房間開始,病鳥的治療室、觀察室、戶外野外區域,都安裝了監控。老田出門也帶著一沓“野生動物接受憑證”,和唐山林業局“關于建立唐山市大清河鹽場野生動物收容救護站的批復”復印件,收到病鳥后一式兩份給對方存底。做志愿工作不是僅靠一腔熱血就能堅持下來的,這些做記錄的流程,會讓田志偉這樣單打獨斗的志愿者避免更多的麻煩。
田志偉算是當地森林公安的協警,這也是幫助他護鳥的一個兼職身份。晚上19點多,老田叫上了一名志愿者,開著越野車出了城——今天刮了一天風,這正是盜獵者抓猛禽的天氣。
還沒真正出城,我們就在港口附近的市政綠化樹林里看見了兩束手電筒光,上下來回晃動,伴隨著狗叫和摩托車發動機聲。
“抓野兔的。”老田把越野車開到人行道上,關了火,跟志愿者兩個人對著樹林大吼了一聲“出來!”就要往里面跑。
里面的盜獵者已經發現了動靜,手忙腳亂地來不及收手電筒,兩個摩托車轟鳴著突然加速沖出小樹林,擦著田志偉身邊逃了出去,跟車跑出的獵犬慌得一路狂吠,雞飛狗跳地一溜煙跑遠了。
剛剛兇神惡煞的老田一下子放松下來,笑嘻嘻地回到車上——如果盜獵者的摩托車停在外面,他會先悄悄把車鑰匙擰下來,再守株待兔地抓人,像這種正騎著車的,老田一看就知道攔不住,叫兩嗓子嚇唬走就行。
“他們摩托騎那么快,你把他拽下來肯定是要受傷。要再開車去攆,出事了怎么辦?”田志偉說,有些志愿者不考慮后果,凌晨三四點在山路上攔鳥販子,“大黑天突然沖出來個人抓他,他都得以為是攔路搶劫,一緊張沖到山下不就出人命了?”
護鳥宣傳、抓人入刑是一種辦法,對于田志偉、王建民這樣堅持了多年的志愿者來說,更多的尋常日子里依靠的是民間智慧。
當晚在鄉下,我們巡視了幾片稻田,沒有發現盜獵者。志愿者一路都在拿手電照稻田,看是否有豎起的竹竿,老田常常在田間突然停下車,豎起耳朵聽有沒有誘鳥器放鳥鳴的錄音。“離老遠聽見我們汽車的聲兒,人早就跑了,我到這就把東西給他收了。去年這附近有個村一直有人抓鳥,我挨著個去了一個月,前半夜、后半夜不定時地來看,最后消停了。”
田志偉統計了一下,一套完整的捕鳥設備需要一個50塊錢的電瓶,一個30塊錢的功放器,四五個單價10塊錢的喇叭,每米1塊錢、至少150米連喇叭的電線,2塊錢一根的竹竿,和8塊錢20米、一插插好幾百米的鳥網。“你收一次,他至少損失四五百塊錢,來回多收幾次,他一算這個賬就再也不買了。”田志偉的救助站里現在堆了一大堆鳥網和音箱,天津獵人習慣用插U盤的低音炮,唐山人是用讀卡器,老田又開玩笑:“回頭我給你個功放器,拴一圈喇叭,晚上你去廣場跳舞。”
田里的水稻馬上就要割了,一只鵪鶉被田志偉的手電筒光嚇住,半天才反應過來,照著直線飛走了。“這放一條狗就直接逮住了,還有人放鷂子,就是松雀鷹,專門在田里抓鵪鶉。”
等到稻田割完,又是抓猛禽的季節。盜獵者用地網,拴一只鴿子或者另一只猛禽做誘餌,自己在田里挖個坑躲在旁邊,猛禽一過來就拉繩,把鳥整個扣在里面。巡護就是要用望遠鏡先看一遍稻田,如果干干凈凈的田里突然多出來一只不飛的鴿子或猛禽,遠遠把車繞著開過去,準能看見抓鳥的人。“但是我們一過去,提前得有150米吧,這人準跑了。有一次我帶了一個派出所所長一起追,給我們累的,所長最后氣瘋了,說逮著這個人非得打他一頓。”
去年11月中旬,田志偉終于抓住了一名盜獵者,在田埂上堵住了對方的車,叫警察把人帶走了,最后把人拘留了5天。
持久戰
每年從八月十五開始,天津、唐山就開始有候鳥陸續抵達。先來黃胸鹀,然后是麻鷯(南朱雀)、栗鹀、紅眉鹀、小鹀、青頭鹀;9月4、5日來紅喉歌鴝、藍喉歌鴝;10月1日前后,來云雀;10月5、6日,來燕雀(“燕雀不值錢,沒人逮。”李青說)。11月來東方白鸛,東方白鸛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全世界只有3000多只,在中國能觀測到的也就1500只左右。
2012年11月,天津北大港濕地自然保護區發生了東方白鸛投毒案件,有人用農藥克百威毒殺這種珍稀的大型水鳥,以高價賣給餐館。王建民、田志偉等志愿者搶時間解救了13只中毒的東方白鸛,最后成功放飛。
11月馬上就要到了,這一輪拆鳥網的活動剛剛告一段落,田志偉、王建民又要開始準備檢查濕地的投毒情況。就在這幾天,在郊區的魚塘,劉懿丹就發現了三只被農藥下毒的蒼鷺,其中兩只已經死亡。在10月10日,科研學者在曹妃甸的水域里發現了80多只死鳥,這些死鳥被判斷是因病而死,老田跟志愿者們就把鳥都埋了,但老田不太相信病死的解釋:那些死掉的翹鼻麻鴨、反嘴鷸、綠翅鴨都離奇地出現在同一片水域,而且個個體型不小,不像生病的樣子,死鳥出現的時間也很集中,恐怕還是因為被下了毒。
10月14日,田志偉又開車去了趟曹妃甸,在上次埋死鳥的區域,他又撿回來兩只病怏怏的翹鼻麻鴨、一只綠翅鴨。這幾只鳥在淺灘上奄奄一息,只有基本的應激反應,一抱起來,整個腦袋都無力地直直垂下。
田志偉現場給鳥注射了阿托品,這是解農藥最有效的一種針劑。他當場量了一只翹鼻麻鴨的體重,2.77公斤,“多肥,這不可能是自己生的病”,其他幾只死去的翹鼻麻鴨被老田當場埋了。這種水鳥羽毛潔白,非常顯眼,老田怕有人過來撿走,也怕有猛禽撲過來吃,如果有農藥,對人對鳥都會導致二次中毒。
而那些被毒殺的鳥,就是帶著身體里的農藥被送到了餐館。從鍍鋅的廠子里帶出的氰化鈉、從農田里帶出來的克百威,泡上小魚、玉米,被撒在天津填海造陸中已經在急速縮小的濕地水域,變成了候鳥的致命誘餌。
在一年又一年的重復工作中,志愿者們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王建民記得這些年每一輪媒體的集中熱點報道,在每一次大規模討論、集中抓捕后,獵鳥的風氣會暫時削減一段時間,時隔一兩年又會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