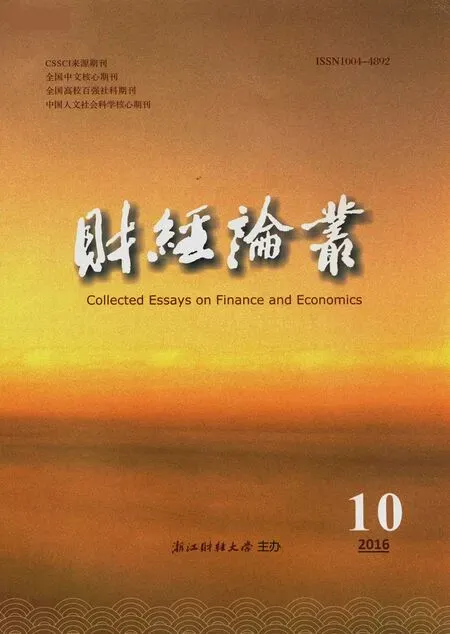晉升激勵、金融市場化與擔保圈現象
劉海明,曹廷求
(1.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山東 濟南 250014; 2.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山東 濟南 250100)
?
晉升激勵、金融市場化與擔保圈現象
劉海明1,曹廷求2
(1.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山東濟南250014; 2.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山東濟南250100)
近年來,擔保圈現象成為影響公司穩健運行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大問題,本文研究了擔保圈問題的形成機理。結果發現,晉升激勵越大、金融市場化水平越低,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可能性越大。控股股東的侵占風險越高,晉升激勵和金融市場化水平影響擔保圈形成的作用更強。晉升激勵主要影響國企加入擔保圈的行為,而金融市場化水平主要影響非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行為。本文揭示了擔保圈的形成機理,對于新常態下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治理提升信貸資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啟示。
擔保圈現象;制度環境;晉升激勵;公司治理
一、引 言
擔保圈是指公司之間由于信用擔保合約相互連接形成的網絡組織。自2001年起,擔保圈現象成為學術界和監管當局關注的重點,包括上海擔保圈、湖南擔保圈、河北擔保圈、濰坊擔保圈等不同地區的擔保圈對上市公司穩健運行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擔保圈現象的一個特征是,一旦一家公司出現問題,風險將沿著擔保鏈條呈現多米諾骨牌式地發展,導致整個擔保圈中的企業陷入危機。典型的擔保圈現象如圖1所示。近幾年來,擔保圈問題開始向非上市企業蔓延,成為影響企業運行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大問題。鑒于此,2014年7月,銀監會下發了《關于加強企業擔保圈貸款風險防范和化解工作的通知》,對治理和防范擔保圈風險問題做出了具體規定。
信用擔保的本意是利用擔保人的信息優勢對借款人進行監督,提高信貸資源配置效率[1]。然而,實踐中的擔保圈問題卻出現了悖反的現象。由于信用擔保的廣泛存在,擔保圈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基于此,許多研究對擔保圈現象進行分析。比如,萬良勇和魏明海(2009)以河北擔保圈為例從金融生態的角度探究擔保圈問題的根源[3];吳寶等(2012)針對擔保圈內部的傳染問題進行研究[4];陳道富(2015)以某商業銀行臺賬為基礎繪制了擔保圈關系圖并對擔保圈的分布情況進行統計分析[2];王永欽等(2014)以某地級市數據為樣本分析擔保圈對公司融資的影響[5]。然而,已有的研究更多地使用案例分析方法探討擔保圈問題,并且更多地涉及其經濟后果的研究。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擔保圈是怎么形成的?在存在如此嚴重負面效應的情況下,為什么擔保圈形成并且普遍存在?從制度環境的角度看,擔保圈的形成遵循什么樣的邏輯?
不同于以往使用案例分析或者某一地級市數據的方法,本文以上市公司對外擔保數據為基礎利用社會網絡軟件UNICET生成了上市公司之間詳細的擔保圈數據,克服了之前只能使用案例或者某一地區數據的限制,能更加深入地討論擔保圈問題。本文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金融市場化兩個制度視角剖析擔保圈形成機理,并結合內部治理機制和所有制進行分析。與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創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擔保圈數據,拓展了該領域的研究方法;第二,本文基于擔保圈形成機理這一新問題進行探討,拓展了擔保圈問題的研究視角。此外,由于信用擔保以及擔保圈現象涉及信貸資源配置,對于擔保圈形成機理的研究具有較強的實踐價值,有利于通過改善政企關系模式、深化金融改革等途徑解決擔保圈問題,對于新常態下通過深化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二、研究假設
擔保圈的形成以信用擔保的廣泛存在為基礎。信貸市場中,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引發企業的道德風險以及事前的逆向選擇問題,提高金融機構的監督成本和交易成本[6]。基于此,金融合約中通常要求借款企業提供一定程度的擔保,包括信用擔保。信用擔保以第三方支付能力或信譽為基礎對貸款進行擔保,在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的情況下,銀行可以要求擔保人代為償還。經典的理論認為,信用擔保可以將金融機構面臨的道德風險轉嫁給擔保人[7]。相對于金融機構而言,處在借款人關系網絡中的擔保人更具信息優勢,能夠有效地利用這些信息對借款人進行監督。比如,當借款人和擔保人處在上下游關系時,如果借款人發生違約,擔保人會迅速將這一違約信息擴散至借款人企業所在的圈子,降低企業聲譽,進而降低借款人的公司價值[8]。所以,傳統觀點認為,信用擔保能夠解決信息問題,進而提高信貸資源配置效率[1][9]。當信用擔保廣泛使用時,企業之間通過擔保鏈條相互連接構成了擔保圈,作為企業關系資源的固化形式,擔保網絡也應該能夠提高借款人的融資能力和盈利能力[5]。然而,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信用擔保的使用以及擔保圈的形成遵循著一套獨特的模式,使得其本有的功能被異化[3],造成了實踐中擔保圈問題不斷。
首先,政治激勵影響著信用擔保的使用以及擔保圈的形成。自North(1981)以來,政治激勵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被廣泛關注[10]。在中國,地方官員在晉升激勵下圍繞GDP增長開展競爭[11],促成了爭奪金融資源推動本地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的現實需求[12]。地方政府對信貸行為的干預直接影響信貸資源配置效率。作為增信措施,信用擔保是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重要途徑,在政治激勵下,地方政府具有撮合本地企業之間達成相互擔保關系以獲取更多融資的沖動[3],實踐中擔保圈也具有明顯的地理集聚特征,即往往集中于某一個地區。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壓力越大,其對企業信用擔保行為的干預沖動越強,企業之間在政府撮合下通過信用擔保獲得貸款的可能性越大,這同時提高了企業之間通過擔保鏈條相互連接進而構成擔保圈的可能性。然而,在政府干預下形成的擔保圈并不符合經典理論的要求,政府撮合下的企業之間可能并不了解,擔保人相對于銀行不具備信息優勢,這會加劇借款企業的道德風險問題,使信用擔保本有的功能被異化。
其次,金融市場化也會影響擔保圈的形成。在銀行業改革中,一個關鍵的改革機制就是放權改革,貸款決策由原來的集體負責制改為個人負責制,分支機構的貸款負責人和經理人在貸款決策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13]。由于商業銀行總部與分支機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不良貸款的顯現具有時滯,分支機構貸款負責人和經理人有能力隱瞞貸款信息,在個人利益動機下存在過度放貸的沖動[3]。此外,長期利率管制下產生的存貸差促成了商業銀行單純通過增加貸款總量以獲得增長的粗放模式。在分支機構過度放貸沖動的條件下,那些面臨融資約束的企業之間有可能通過兩兩互保的方式套取銀行貸款資金[14]。這一問題在擔保圈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由于分支機構相對于銀行總部的信息優勢,貸款負責人具有過度放貸的沖動,并且傾向于發放在形式上符合條件但實質上存在較高風險的貸款。所以,金融市場化改革的現狀使得分支機構經理人存在過度發放信用擔保貸款的傾向,激勵那些面臨融資約束企業通過兩兩之間互相擔保獲取資金,這提高了擔保圈形成的可能性。然而,上述行為可能對信貸資源配置產生負面影響。在這些信用擔保貸款中,擔保人和借款人之間可能不具備信息優勢,即使相互之間更為了解,也沒有動力進行監督。這扭曲了信用擔保本有的功能,導致其負面效應的產生。金融市場化水平越低,總部對分支機構的信息優勢和控制能力越差,分支機構的過度放貸沖動越大,上述現象越明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晉升壓力越大,或者金融市場化水平越低,本地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可能性越大。
在探討了制度環境對擔保圈形成的影響之后,進一步分析內部治理機制對擔保圈形成的影響。一方面,已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對外擔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控股股東的私利,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的現金流量權越小,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越多,對上市公司價值的負面影響越大[15]。控股股東通過對外擔保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現象不僅體現在上市公司對母公司的擔保上[16][17],也體現在其對其他關聯方以及子公司的擔保上[18],還包括對非關聯方的擔保。另一方面,擁有私利動機的控股股東也會推動上市公司通過信用擔保獲取更多融資。這意味著控股股東在公司中的現金流量權越小,上市公司加入擔保圈的可能性越大。
進一步地,控股股東的私利動機可能與較差的制度環境相互交織。從官員晉升激勵的角度看,國有企業控股股東的掏空動機與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具有目標一致性[3]。控股股東在企業中的現金流量權越低,掏空激勵越強,促使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動力越大,這契合了官員晉升激勵對企業加入擔保圈、獲取融資的現實需求,進而放大了晉升激勵對加入擔保圈行為的正向效應。
從金融市場化的角度看,在金融市場化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銀行短期內過度放貸沖動易與上市公司大股東形成合謀,使得那些侵占風險高的上市公司更易獲得信貸資金支持[19]。控股股東的掏空激勵越強,上市公司參與信用擔保越頻繁,這迎合了在金融市場化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過度放貸的現實需要。所以,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中的現金流量權越低,金融市場化水平影響企業加入擔保圈的效應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控股股東在企業中的現金流量權越低,晉升壓力或者金融市場化水平對企業加入擔保圈傾向的影響越大。
最后,分析不同所有制情況下擔保圈的形成機理。對于國有企業而言,由于政府對企業直接的所有權控制,其更可能受制于政策目標的影響。羅黨論和唐清泉(2007)發現,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越高,地方國企的對外擔保行為越多[20]。而與國企相比,民營企業較少受到地方政府目標的影響。因此,晉升激勵對擔保圈形成的影響集中在國有企業上。
與國企不同,民營企業往往面臨信貸歧視,受到更強的融資約束[21]。相對于國企而言,民營企業擁有更高的激勵通過各種手段獲取銀行信貸。當金融市場化水平較低時,商業銀行存在過度放貸沖動,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兩兩互保的方式達到銀行貸款的形式要求進而緩解其融資約束,而國有企業則較少地受到融資約束問題的困擾。因此,金融市場化水平主要影響民營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晉升激勵主要影響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而金融市場化水平主要影響民營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
三、研究設計
(一)擔保圈數據
本文基于Wind數據庫構建了上市公司之間的擔保圈數據。使用上市公司之間的擔保圈數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對外擔保是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披露的信息,基于對外擔保數據可以描繪出上市公司之間的擔保網絡圖;第二,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相對全面,這為研究擔保圈的形成機理提供了數據支持。本文使用這一數據庫克服了之前只能采用案例分析或者某一地區數據進行研究的局限。
我們從Wind擔保數據庫中獲取了2003-2012年所有參與擔保的上市公司共45205筆信用擔保合約信息。然后將原始的擔保合約進行篩選,遴選出上市公司之間的擔保合約,共4229筆;其次,將上述合約從年度層面運用社會網絡軟件UCINET進行匯總,得到每個年度的上市公司擔保網絡圖。我們將包含3家以及3家以上公司的網絡稱為擔保圈。樣本期間一共有806個公司-年度樣本位于擔保圈中,擔保圈數目共計155個。
圖1列示了樣本期間的一個擔保圈。圖中的節點代表上市公司,線條代表擔保關系。可以看到,這一擔保圈中共包含18家上市公司。箭頭指向的方向代表被擔保方,雙向箭頭代表兩家企業存在互相擔保,比如華源發展和中油龍昌之間存在互相擔保,福建三農和華通天香之間也存在互相擔保。部分企業之間通過擔保鏈條連接形成了封閉的環狀結構,比如神州學人-華通天香-福建三農-福建三木之間形成了一個環狀結構。圖中某一節點相連的鏈條數代表與該企業存在擔保關系的企業數目。在這一擔保圈中,福建三木與多達7家上市公司存在信用擔保關系。圖1列示的擔保圈是一個非常典型和復雜的上市公司擔保圈。從圖1看出,擔保圈這一形態結構將非關聯的企業之間聯系在一起,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為之后風險傳染和爆發埋下了伏筆。

圖1 某一擔保圈示例圖
(二)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Logit模型進行分析,基本模型設定如下:

β5*assetit+β6*debtit+β7*stateit+β8*listit+β9*blockit+industry+εit
其中,P代表上市公司在t+1年加入擔保圈(即Circlet+1=1)的概率。被解釋變量為上市公司是否加入擔保圈Circle,如果某家上市公司某一年度加入擔保圈,取值為1,否則為0。主要解釋變量為promotion和financial,分別代表晉升激勵和金融市場化水平。晉升激勵方面,本文借鑒錢先航等(2011)、羅黨論和唐清泉(2007),主要從地級市層面的GDP增長率、失業率以及財政赤字率這三個層面生成晉升激勵指標。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官員的考核機制由政治指標轉向經濟指標,而近年來民生問題也成為考核重點,因此經濟增長、就業情況以及財政收支成為地方政府關注的焦點,也成為晉升的關鍵標尺[22][20]。我們借鑒錢先航等(2011),將反映政治激勵的三個指標在年度水平上求平均值,如果GDP增長率低于均值、失業率高于均值或者財政赤字率高于均值,分別取1,否則取0[22]。然后將三個指標相加,構建晉升激勵指數promotion,promotion越大,說明所在地區的官員晉升壓力越大。金融市場化水平取自樊綱等(2011)的“金融市場化水平”分指數[23]。
控制變量方面,我們控制了上市公司總資產收益率ROA、融資約束水平EFD、公司總資產asset、資產負債率debt、是否國有state、公司上市時間list、控股股東現金流量權block,其中,融資約束指標EFD借鑒喻坤等(2014)[24]。此外,我們還控制了行業層面的虛擬變量。為了控制可能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將所有解釋變量做滯后一期處理。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相關性分析
本部分對主要變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circle與promotion的相關系數為0.05,且在1%水平上顯著;circle與financial的相關系數為-0.1,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些結果與基本假設一致,即企業加入擔保圈與晉升激勵正相關而與金融市場化負相關。circle與ROA之間顯著負相關,表明績效好的企業更不可能加入擔保圈。circle與EFD之間顯著正相關,即加入擔保圈與企業融資約束存在正相關。

表1 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注:“* ”、“** ”、“*** ”分別代表在10%、5%、1%水平上顯著。
(二)制度環境與擔保圈形成
本部分利用基本模型進行Logit回歸分析,以驗證假設1。回歸結果如表2前3列所示,其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別匯報了promotion或者financial作為主要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列在回歸分析中加入上述兩個變量進行分析。從1、3兩列結果看,promotion的系數顯著為正,即晉升激勵越強,上市公司加入擔保圈的可能性越大,擔保圈越可能形成,這與假設1一致。在晉升激勵下,地方官員擁有動機促使本地企業通過信用擔保方式獲得貸款,以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這加大了本地區擔保圈形成的可能性。從2、3兩列的結果看,financial的系數顯著為負,即金融市場化水平越低,上市公司加入擔保圈的可能性越大,擔保圈形成的可能性越大,這與假設1一致。已有的金融制度造成了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過度放貸沖動,金融市場化水平越低,銀行放貸沖動越強,企業之間通過信用擔保獲取貸款的動力越大,擔保圈形成的可能性越大。上述實證結果從制度環境層面給出了擔保圈形成的一個解釋。晉升激勵使得企業更可能被推動使用信用擔保獲取貸款,而較低的金融市場化水平加大了銀行的放貸沖動,促使企業更加方便地通過信用擔保獲取融資,這加大了擔保圈形成的可能性。然而,制度因素的影響使得信用擔保合約不滿足正常運轉的條件,進而造成擔保圈問題頻發。

表2 制度環境與擔保圈形成
注:“* ”、“** ”、“*** ”分別代表在10%、5%、1%水平上顯著;方程采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最后一行是偽R2;前三列是全樣本回歸結果,第四列匯報了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結果,第五列匯報了非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結果。
(三)控股股東侵占動機、制度環境與擔保圈形成
下面我們分析控股股東侵占動機與制度環境在擔保圈形成中的作用。我們的策略是在基本模型中分別加入晉升激勵promotion、金融市場化水平financial與控股股東在公司中的現金流量權block的交叉項,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在回歸分析中,我們針對上述變量及其交互項進行中心化處理。第1列匯報了晉升激勵與現金流量權的結果,第2列匯報了金融市場化水平與現金流量權的結果,第3列將兩個交互項同時加入回歸方程中。在第1列和第3列中,promotion*block的系數顯著為負,控股股東在公司中的現金流量權越小,晉升激勵對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影響越大,這與假設2一致。在上市公司中,控股股東的掏空動機與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在信用擔保行為中具有目標一致性,前者是為了促使上市公司獲取融資以謀取私利,而后者則是為了促使本地企業獲取融資以支持本地經濟增長和就業。治理機制與政治激勵互相協同是導致擔保圈產生和問題頻發的原因之一。
在第2列和第3列中,financial*block的系數顯著正,控股股東在公司中的現金流量權越小,金融市場化水平對企業加入擔保圈的負面影響越大,這與假設2一致。較低的金融市場化水平促進了商業銀行的過度放貸沖動,這與控股股東促使上市公司獲取更多融資以謀取私利的動機協同,進而降低了信貸資源配置效率。

表3 控股股東現金流量權、制度環境與擔保圈形成
注:由于篇幅限制,本表未報告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要。
(四)所有制、制度環境與擔保圈形成
本部分討論不同所有制情況下制度環境對擔保圈形成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2后兩列所示。其中第4列匯報了國有企業的回歸結果,第5列匯報了非國有企業的回歸結果。promotion的系數在國有企業回歸中顯著,而在非國有企業中不顯著,這意味著晉升激勵主要影響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這與假設3一致。由于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具有直接的所有權控制,其晉升激勵更可能影響到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從financial的回歸結果看,其系數在國有組和非國有組均顯著為負。為了對比金融市場化水平是否更多地影響民營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將上述兩個方程進行ols回歸,并且用卡方檢驗分析financial系數的差異性,結果發現,financial的系數絕對值在民營企業組更大,并且卡方檢驗在1%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金融市場化水平更多地影響非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由于非國有企面臨更強的融資約束,其利用商業銀行過度放貸沖動通過信用擔保獲取融資的傾向更強,所以金融市場化水平更多地影響非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
五、主要結論與啟示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擔保數據、利用社會網絡軟件UNICET繪制了上市公司的擔保網絡圖,并以此為基礎分析擔保圈的形成機理。結果表明,制度環境是影響擔保圈形成的重要因素,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越大或者金融市場化水平越低,上市公司加入擔保圈的傾向越大。從異質性角度看,控股股東的掏空動機越強,制度環境影響擔保圈形成的作用越大。晉升激勵主要影響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而金融市場化水平更多地影響非國有企業加入擔保圈的傾向。
基于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第一,解決擔保圈問題應當首先從深化改革、改善制度環境方面入手。應當加快改革官員考核機制,將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等增長質量指標納入官員晉升的考核范圍;同時,加快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降低總部與分支機構的信息問題,提高商業銀行風險防范和控制能力。制度環境的改善能夠糾正信用擔保契約在實踐中的扭曲現象,進而有效解決擔保圈問題。第二,解決擔保圈問題的第二條途徑是完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提高投資者保護水平。治理機制與制度環境相互交織可能造成信用擔保的濫用和擔保圈問題頻發,因此,完善內部治理機制有利于解決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占動機,從而緩解擔保圈中問題。第三,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深化改革是提高信貸資源配置、實現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手段。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在制度環境較差時,金融契約(包括信用擔保契約)的運行可能發生扭曲,進而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而通過深化改革,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進金融改革,能夠有效地實現信貸資源的高效配置,進而有利于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
[1] Besanko D., Thakor A. V.. Collateral and rationing: Sorting equilibria in monopolistic and competitive credit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7, 28(3): 671-689.
[2]陳道富. 我國擔保圈大數據分析的初步發現[J].中國發展觀察, 2015, (1): 71-75.
[3]萬良勇, 魏明海. 金融生態、利益輸送與信貸資源配置效率——基于河北擔保圈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5): 6-16.
[4]吳寶, 李正衛, 池仁勇. 社會資本、融資結網與企業間風險傳染——浙江案例研究[J]. 社會學研究, 2011, (3): 84-105.
[5]王永欽, 米晉宏, 袁志剛, 周群力. 擔保網絡如何影響信貸市場——來自中國的證據[J]. 金融研究, 2014, (10): 116-132.
[6]尹志超, 甘犁. 信息不對稱、企業異質性與信貸風險[J]. 經濟研究, 2011, (9): 121-132.
[7]Merton R. C., Bodie Z.. On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guarantees[J].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92, 21(4):87-109.
[8]盛丹, 王永進. “企業間關系” 是否會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J]. 世界經濟, 2014, (10): 104-122.
[9]Arnott R., Stiglitz J. E.. Moral hazard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Dysfunctional crowding out of peer monitoring?[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1): 179-190.
[10]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Z]. SSRN Working Paper, 1981.
[11]周黎安. 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 經濟研究, 2007, (7): 36-50.
[12]巴曙松, 劉孝紅, 牛播坤. 轉型時期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地方治理與銀行改革的互動研究[J]. 金融研究, 2005, (5): 25-37.
[13]Qian J., Strahan P. E., Yang Z.. The impact of incentives and communication costs o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use: Evidence from bank lending[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4):1457-1493.
[14]馬亞軍, 馮根福. 上市公司擔保行為分析[J]. 證券市場導報, 2005, (5): 58-64.
[15]Berkman H., Cole R. A., Fu L. J.. Expropriation through loan guarantees to related parties: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9, 33(1): 141-156.
[16]鄭建明, 范黎波, 朱媚. 關聯擔保、隧道效應與公司價值[J]. 中國工業經濟, 2008, (5):64-70.
[17]高雷, 宋順林. 掏空、財富效應與投資者保護——基于上市公司關聯擔保的經驗證據[J]. 中國會計評論, 2007, (1): 21-42.
[18]饒育蕾, 張媛, 彭疊峰. 股權比例、過度擔保與隱蔽掏空——來自我國上市公司對子公司擔保的證據[J]. 南開管理評論, 2008, (1): 31-38.
[19]萬良勇. 銀行道德風險、利益侵占與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金融研究, 2010, (4): 177-190.
[20]羅黨論, 唐清泉. 政府控制、銀企關系與企業擔保行為研究[J]. 金融研究, 2007, (3): 151-161
[21]盧峰, 姚洋. 金融壓抑下的法治、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J]. 中國社會科學, 2004, (1): 42-55
[22]錢先航, 曹廷求, 李維安. 晉升壓力、官員任期與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J]. 經濟研究, 2011, (12): 72-85.
[23]樊綱, 王小魯, 朱恒鵬. 中國市場指數——各省區市場化相對進程 2011 年度報告[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11.
[24]喻坤, 李治國, 張曉蓉, 徐劍剛. 企業投資效率之謎: 融資約束假說與貨幣政策沖擊[J]. 經濟研究, 2014, (5): 106-120.
(責任編輯:原蘊)
Promotion Incentives,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and Guarantee Circle
LIU Hai-ming1, CAO Ting-qiu2
(1.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guarantee circle phenomenon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that negatively affects corporat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of the guarantee network formati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promotion incentive of one province is larger or its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level is lower, firms located in that province are more likely to join in the guarantee circle. Furthermore, when expropriation risk of block shareholders is higher, the above-mentioned effect is larger. Promotion incentives mainly affect the state-owned firms while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level mainly affects the non-state-owned firms.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uarantee circle, and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credit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guarantee circ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motion incentives;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5-09-14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2&ZD06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272119)
劉海明(1988-),男,山東濰坊人,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講師;曹廷求(1968-),男,安徽安慶人,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F830.5
A
1004-4892(2016)10-0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