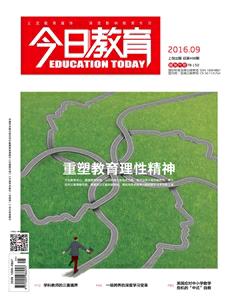用批判性思維塑造教育理性精神
鄧文圣
重塑教育理性精神的要義是思維方式的重塑。這就要求不同層面的教育主體從教育改革、教育發展、教育實踐等不同方面生成理性精神,推動教育朝著合理的方向持續改進。諸如,在教育改革方面,如何處理好觀念變革、制度變革與文化變革,單點突破與系統重構,持續微創新與顛覆式創新的關系;在教育發展方面,如何處理好傳承與創新、本土傳統與外來引進、規模擴張與質量效益的關系;在教育實踐方面,如何處理好統一規范與個性創生、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關系等等,都需要全面、客觀、辯證地進行思考和分析,學會運用批判性思維,充分認識各種思維方式的優勢和局限性,在自由、包容、協同、融合、創生中塑造自己的理性精神。
我們需要時刻保留那份“批判性”。任何“批判”的思維都必須以充分的事實材料為依據,以“理性”為基石。看待任何事物都要客觀公正,因為真理只與事實有關。
“沒有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一位英國外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中國學生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問題”。
中國學生的“沒有問題”,顯然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不會提出問題,其二是不愿不想去提出問題。究其根本,其實就是缺少“批判性”意識,習慣于接受,被灌注。當然,缺少“批判性”并非僅僅是中國學生,在歐美那些相對先進的國家,學生也需要加強“批判”意識的培養。因此,世界教育的共識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這是“明天教育”的主旋律。
“批判的”(critical)源于希臘文kriticos(提問、理解某物的意義和有能力分析,即“辨明或判斷的能力”)和kriterion(標準)。從語源上說,“批判性思維”是暗示發展“基于標準的有辨識能力的判斷”。
“批判性思維”作為一個技能的概念提出,可追溯到杜威的“反省性思維”(reflective thinking)——批判性思維的探究模型——“能動、持續和細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識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進一步指向的結論”。
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批判性思維”應貫穿于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沒有學科邊界,它沒有禁地和真空,是敢于從批判性的視角來審查任何涉及智力或想象的論題。這與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想人格的建構 “不謀而合”。
我們追尋和提倡“批判性思維”培養的同時,一定要特別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批判性思維”應該是基于事實基礎上的,辯證、客觀、全面地看問題,要在能看到并肯定對方觀點的合理因素的情況下,再理性地平和地尊重地闡述證明自己的見解。
隨著技術革新的快速推進,網絡已經走入千家萬戶。興許是法律的寬容,興許是沒有了“面對面的尷尬”,當下,有些人士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偏解“批判性思維”的精髓,討論問題直接丟棄“理性”,缺乏分析問題以及與人辯論的基本素養,往往一言不合便叫罵起來,以致很多所謂的網絡辯論不堪入目。他們有一個“通病”——先有立場后有問題。
社會上缺乏理性的“批判性思維”觀,同樣表現在某些教育人對教育問題的“批判性”解讀上。當一年一度的高考進行時,圍繞高考的話題可謂是“東方風來滿眼春”。對于大別山深處的“毛坦廠中學”模式,有人譴責是粗暴、原始、功利性極強的教育方式的代表,對其宗教儀式般的送考架勢,有人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然而他們不去捫心自問:那些學生為什么會自覺地為改變家庭命運而讀書,愿意采取以時間換分數的低級戰術?為什么依然選擇如此辛苦的道路而不肯放棄?
毛坦廠中學的確存在一些違背“新式教育”理念的地方,經不起細細推敲,但之所以有這么多學生還愿意來到這兒,擠相對公平的高考獨木橋,是他們除此之外缺乏更多更好的階層流動通道,這是底層社會自發演化出來的一種自我拯救。正如央視主持人在專題評論中所說:當我們思考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等宏大話題的時候,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應該要關注毛坦廠中學所代表的一群人,而不能將他們當成“落后事物”拋棄,必須直面階層流動存在淤塞的現實,而不是架空現實地談“理想”。
全盤“批判”毛坦廠,鄙視它和它的學生家長,顯然是不“理性”的,是不利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大方向的,改變教育不僅僅是審丑,幫助和引導其實更重要。
當河北涿鹿縣委叫停“三疑三探”教學改革,該縣教科局原任局長郝金倫決定“不去領導這項工作”,毅然激情辭職之后。又是“一窩蜂”地批評“改革失敗,是過于激進”,“行政強推的模式化課改必敗無疑”。有的似乎是出于善意,提醒教改推行者“教改要有激情,但更要專業,先讓更多人認同和支持,改革才能夠照進現實”。其實,我們誰都知道,改革哪有坦途,如果追求“四平八穩”還能有創新嗎?試想,如果涿鹿的改革還在繼續,且有了成績,他們又會怎么說呢?如果不去“理性”地看待改革中遇到的障礙,留給改革創新的“氛圍”是何等的“嚴苛”,還有多少人會去改革?敢去改革?
特別還記得,一年前那次“中英教學方式之爭”。五名中國中學老師到英國漢普郡一所頂級中學,對該校的學生進行一個月的“中國式教學”,結果,中國老師明顯“水土不服”的事件見諸網絡報刊,而對“中國式教學”的批判幾乎是“鋪天蓋地”,斥責中國教師的古板教條和沒有尊重學生人性的愛心,斥責“中國式教學”是“盲目自信”“麻木和無趣”,害了孩子的天性。似乎“中國式教學”已經“一無是處”,早該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可一年后的2016年7月,英國教育部宣布,英格蘭半數小學將采用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上海的數學教學方法。當時的一些“痛罵”者,又說“中式教育重視基本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是中國教育的自信”。這種“批判”或“肯定”又有多少是“理性”的呢?
杜威說:沒有思想的自由,何來“完整的精神”,又何談生長?又何能成為 “活潑潑的,能改良社會的,能生產的個人”? “自由和超越才是作為人的根本所在”。人類文化的傳承和社會的進步離不開“批判性思維”,離不開對陳舊的“否定”,不破不立。在當前,教育人以及教育人教育學生,必須具有“敢于否定”的“獨立思想”,才有利于形成批判性、想象力和創造力。同時,“敢于否定”的“批判”永遠不能離開“理性”的軌道,“批判性思維”絕不等于“全盤否定性思維”。評論教育問題或與同仁研討甚至辯論,不管是當面,還是在網絡上的自由表達,都不要忘記美國哲學家布魯斯·沃勒在《優雅的辯論》一書中給人們的六個建議:認真傾聽他人的意見,不要隨意貼標簽,拒絕“稻草人謬誤”(即故意曲解、夸大或歪曲對方論點或立場,使其更容易受到攻擊),不搞人身攻擊,警惕折中的解決方案,努力欣賞你反對的觀點中最好的理由。
未來的社會,需要會提出問題,有問題才會促成去探尋結論,沒有問題的確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時刻保留那份“批判性”。我們得記住,任何“批判”的思維都必須以充分的事實材料為依據,以“理性”為基石。看待任何事物都要客觀公正,因為真理只與事實有關。
作者系江蘇省海安大公教育中心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