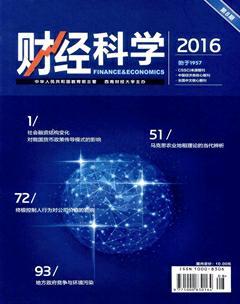契約執行效率、工資與勞動報酬份額
劉帥光



[內容摘要]理解契約執行效率改善對工資增長和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并存的影響機制,對于改善收入分配、提振內需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文將不完全契約理論引入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并發現契約執行效率通過影響要素價格而提升勞動邊際產出,從而提高工資水平,契約執行效率提升還通過產業結構效應導致勞動報酬份額下降。此外,本文還使用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1997—200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考察契約執行效率對工資和勞動報酬份額影響的經驗證據,并得到與理論模型一致的實證結果。
[關鍵詞]契約執行效率;工資;勞動報酬份額
一、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余載,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工資極大提高,人均名義工資收入從1978年的615元躍升至2012年的46769元,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工資也增長了15倍。但是,在經濟增長獲得階段性成功、平均工資持續增長的同時,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卻日益嚴重。一個重要的表現是中國的勞動報酬份額較低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下降,勞動報酬份額由1992年的58.96%下降至2012年的48.06%。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份額過低容易導致收入分配不均、消費率不足等問題,因此,探討在工資收入增長條件下勞動報酬份額的持續下降,是事關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和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重要問題。
就勞動報酬份額下降而言,主流觀點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統計口徑變化。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a)認為,2004年中國勞動收入份額驟降的主要原因是統計項目的調整,但在剔除統計口徑因素后,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仍然存在。二是產業結構調整。Young(2010)等根據結構分解方法,從產業內勞動報酬份額變動和產業結構變動兩個角度考察勞動報酬變動的原因,并認為產業結構變動是勞動報酬變動最重要的原因。與之類似,中國部分學者認為農業部門的收縮和非農部門的擴張,是導致勞動收入份額整體下降的重要原因。[1][3][4][5][6]李稻葵等(2009)基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提出了勞動收入份額與工業化進程之間潛在的U型關系,而中國現階段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則是因為處于U型的下降階段。三是技術的偏向性增長。黃先海、徐圣(2009)利用1989—2006年中國制造業29個行業的數據發現,中國的技術進步主要是勞動節約型的,這可解釋約70%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陳宇峰等(2013)也認為資本偏向型的技術進步才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長期下降的關鍵因素。四是全球化的影響。FDI的流入對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造成了不利影響,一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相互競爭提高了資本的議價能力,二是由于“回流型”FDI主要是看中了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故而勞動收入上升空間狹小。
但是,這些研究忽視了兩個問題。一是忽視了工資上漲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之間的緊密聯系。二是忽視了以契約執行效率為代表的制度建設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中國雖然在整體上遵循統一的法律規則,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以契約執行效率為代表的制度質量在各省區間有明顯的差別。許多學者在不完全契約框架下,考察了契約執行效率對要素價格、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等問題的影響,但鮮有學者考察契約執行效率差異對工資和勞動報酬份額的影響。
本文發現,契約執行效率不僅通過產業結構效應影響平均工資和勞動報酬份額,還可以同時解釋平均工資的上升和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本文認為,這種現象背后的機制在于:在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環境下,企業的經營發展與向銀行借款的成本息息相關。在不完全契約框架下,契約執行效率不足會導致企業在事后出于機會主義動機而出現延遲還款或其他違約現象,在事實上形成對銀行部門的敲竹杠,增加了銀行的損失風險。銀行部門為了彌補潛在損失,會在事前增加風險溢價、提高貸款利率,從而提高了企業資本的實際使用成本。因此,契約執行效率越高,資本要素使用成本越低,促進了資本深化,從而人均產出和人均工資上升。但是,由于不同部門的生產技術和融資依賴度不同,當契約執行效率提高使得資本成本下降時,資本密集型產業會獲得偏向性增長。若各部門內部的勞動收入份額相對穩定,則契約執行效率提高產生的資本密集型部門擴張和勞動密集型部門收縮的產業結構效應會使得勞動報酬份額在總體上下降。因此,本文認為契約執行效率的變化是同時解釋工資上升和勞動報酬份額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理論模型
(一)產品部門
最終產品由兩類中間產品組成:一是資本密集型產品。此類廠商使用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進行生產,并且企業需要在產品售出前預付資本要素報酬,因此,企業必須在期初為租用資本向銀行部門融資,并在期末將產品歸還貸款;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為簡化處理,假設此類廠商僅使用勞動進行生產,由于不需租用資本,因此不需要向銀行融資。由于本文中設定企業的資本要素需要向銀行部門融資,故而資本密集型廠商相對于勞動密集型廠商而言,其外部融資依賴性更強,對契約執行效率也更加敏感。假設社會有唯一的最終產品用于消費和投資,即由資本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復合成最終產品作為社會最終的消費和投資。
四、結論
本文通過建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論上闡釋了契約執行效率對工資增長和勞動報酬下降的作用機制,并分別使用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1997—200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對理論結果進行了實證檢驗,并得到與理論模型一致的結果。
本文的模型和實證結果表明以提高契約執行效率為代表的制度建設對收入分配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契約執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銀企合作中的摩擦,促進資本深化,增強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工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的融資特征差異,契約執行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勞動收入份額較低的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導致勞動收入份額整體下降。因此,中國各地政府在不斷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也應注意利用制度紅利進行合理的收入再分配,使得各階層共享經濟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