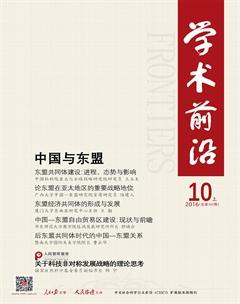東盟共同體建設:進程、態勢與影響
【摘要】 以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共同體為三大支柱的東盟共同體計劃自2003年10月正式提出以來,歷時12年,于2015年12月31日正式宣布建立,這標志著東盟一體化進程全面進入東盟共同體階段。衡量東盟共同體建設成效的并不應該只是完成比例的多少,而是東盟共同體是否具有一個清晰的輪廓,能否為未來共同體的建設確立一個具體框架,而合作領域的深化和敏感議題的談判則是后2015規劃中將重點關注的領域。
【關鍵詞】東盟 共同體 政治 安全 經濟 社會
【中圖分類號】 F114.4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9.001
以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共同體為三大支柱的東盟共同體計劃自2003年10月正式提出以來,歷時12年,于2015年12月31日正式宣布建立,標志著東盟一體化進程全面進入東盟共同體階段。東盟共同體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7年12月頒布的《東盟愿景2020》,但愿景側重于強調東盟身份的認同,以及對未來東盟共同體的憧憬,并沒有明確共同體的具體內涵和實現路徑。
盡管東盟如期宣布建立東盟共同體,但根據其制定的未來發展規劃,部分目標事實上已經順延至后2015議程中繼續推進。從東盟領導人會議開始有意淡化共同體建設的具體數據也可以看出,東盟共同體已經被東盟定義為一個進程性的目標,2015年底只是這個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而非終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再來強調共同體的具體完成比率已經沒有太大意義。本文認為真正衡量2015年底東盟共同體建設成效的并不是完成比例的多少,而是東盟共同體是否具有一個清晰的輪廓,能否為未來共同體的建設確立一個具體框架,合作領域的深化和敏感議題的談判則是后2015規劃中將重點關注的領域。
東盟共同體的特征分析
集體共識下的東盟政治安全領域合作。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是東盟下一階段政治和安全事務領域合作的總體框架和方向,旨在提升東盟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合作水平,確保成員國與域內外國家在一個較為公正和民主的和諧氛圍中共生。對于東盟而言,出于安全目的的合作是必要的,其本質上是政治行為。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不同于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盟,不會發展成為共同防衛條約和軍事聯盟。
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東盟通過達成以“東盟方式”為特征的集體共識,來應對區域內部沖突,并以此促進本地區安全合作的發展。①即東盟并不是通過加強集體防護能力或建立地區聯合軍事力量來維護本地區的共同安全,而是通過內部協調,集體形成某一共識,對危及和平的行為進行規范,降低沖突發生的可能性。第二,東盟的安全合作涉及對外關系,因此在政治安全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如處理與域外國家,特別是與大國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東盟將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原則——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身份平等、不干涉各國內部事務等,通過與域外國家展開對話合作的形式,擴展到整個東亞乃至亞太地區。例如東盟制定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并要求與東盟對話的合作伙伴都簽署這兩個條約,承諾遵守條約的原則。②也正是通過政治安全共同體的構建,東盟在嘗試塑造出一個團結合作的地區組織形象,相比于單個成員國而言,一些關鍵領域的安全利益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作為共同體建設核心內容的東盟經濟共同體。東盟共同體在規劃之初便確立了政治安全、經濟、社會文化這三大支柱,《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于2007年第13屆東盟峰會上簽署通過,另外兩個則于2009年第14屆峰會同時頒布。東盟沒有同時頒布這三個共同體的藍圖規劃,可能是因為:一方面,相對于政治安全和社會文化合作領域,成員國更為關注經濟層面的發展,經濟合作本身也是東盟關注的重點;另一方面,就最初階段的建設而言,在東盟自貿區十余年的建設經驗和成果基礎上,經濟共同體是三個支柱中相對容易推動的一個,見效也最快。東盟在共同體建設之初,將較多的資源用于開展經濟合作,推動經濟共同體藍圖在起步階段順利執行,有利于提升成員國對于最終建成東盟共同體的信心,反過來也有利于推進成員國在政治安全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合作。
為了更好的落實東盟共同體所規劃的目標,東盟列定了17個核心要素以及176個優先發展領域。東盟還制定了《東盟共同體2009~2015年路線圖宣言》,確立了自2008年起的四個2年計劃,明確了每一個領域的建設期限,并采用打分卡制度來監督東盟經濟共同體計劃的實施。從東盟為實現經濟共同體藍圖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可以看出,東盟經濟一體化已經從最初籠統的目標發展成了步驟、措施十分明確的戰略。東盟對一體化建設做出了詳細的時間框架規范,一方面深化和發展了既有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另一方面則對以往經濟合作中遺漏或者忽視的領域做出了明確規定和補充,使經濟共同體作為東盟一體化的實現形式更具可操作性,也為未來東盟共同體的最終創建打下堅實基礎。
旨在培養區域認同感的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建設。東盟對于社會文化共同體的設計超出了以往東盟在社會文化領域的合作范疇,其突出特征是不僅涉及傳統的社會公平和文化認同議題,還納入了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等內容,開始關注經濟一體化對社會和環境造成的影響。③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以人為本、有社會責任感的共同體,并以此促進整個東盟地區的團結和統一。通過在本地區塑造一個共同身份,改善東盟人民的生活和福祉,來構建一個充滿人文關懷和共享精神的包容和諧社會。④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具體建設任務包含六個方面:東盟人民發展;社會福利和保障;社會公平及公民權利;確保環境可持續發展;構建東盟身份;縮小成員國發展差距。針對每一個建設任務下的戰略目標,東盟總共制定了多達339個具體措施。
東盟前任秘書長塞韋里諾認為,從培養東南亞地區認同感、構建區域意識和促進東盟人民相互理解的角度來考量,東盟共同體的核心應該是社會文化共同體。⑤東盟身份和東盟意識的形成將對東盟共同體的構建有著極大的實質性作用: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建設有助于成員國接受共同規范、分享共同價值觀,推動在安全領域的地區合作順利開展;而互信互諒意識的培養,可以增加各國對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信心,促進經濟一體化建設。另一方面,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建設也起到一個信號傳遞的作用,即東盟不僅僅只關注傳統的政治、安全和經濟領域的合作,同時對本地區人民的福祉、弱勢群體的權益等議題也保持著極高關注度。
東盟共同體進程評估
自共同體建設路線圖宣言發布以來,目前既定目標東盟已基本完成。截止至2015年10月底,東盟已經完成路線圖所規定的97%的工作量,其中政治安全、社會文化和經濟等三大支柱預定目標的完成率分別達100%、100%和93%。⑥2015年11月,第27屆東盟峰會通過了《關于建立東盟共同體的2015吉隆坡宣言》,決定于12月31日正式宣布建立東盟共同體,同時承諾在《東盟憲章》的約束下加強后2015的共同體建設。宣言強調了共同體的建立在東盟一體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有助于維護本地區長期和平與穩定,提高經濟發展活力和一體化水平,從而構造一個兼收并蓄、以人為本的社會。
在構建互信中推動政治發展和安全合作。東盟在政治發展上取得的最顯著成就體現在人權的促進和保護方面。《東盟憲章》將人權以地區憲法的形式確立為東盟成員國的法律原則,2009年第15屆峰會通過了《關于成立政府間人權委員會的華欣宣言》,東盟政府間人權委員會(AICHR)機制正式啟動,東盟將其成立視作共同體建設進程中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⑦委員會成立后立即制定了2010~2015年的五年人權工作計劃,并著手于《東盟人權宣言(AHRD)》(以下簡稱《人權宣言》)的起草工作,最終于2012年金邊峰會上簽署通過。宣言從四個方面為東盟的人權合作構建了一個規范性的框架,即公民和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發展權利;和平權利。⑧
安全合作領域上,2003年《東盟協調一致第二宣言》首次明確提出東盟共同體愿景之時,東盟在安全合作領域可以遵循的章程文本限于《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以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安全對話機制也僅依托于1994年成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⑨東盟在共同體的建設進程中對上述條約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訂和補充,以推動這些宣言能夠更有效的執行。作為安全共同體行動計劃的一個重要成果,2006年5月東盟防長會議(ADMM)機制成立,成為討論地區安全問題的主要平臺。至此,東盟安全信心構建、預防沖突和防務合作機制主要依賴于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防長會議,前者作為東盟安全框架的核心,后者則是東盟最高防務機制。⑩東盟國防部長會議的召開便于各國防長就當前防務問題和安全威脅進行談論并交換意見,增加成員國防務透明度和互信水平。為指導合作,東盟自2008年起每三年制定一個工作計劃,合作和行動的重點領域包括加強區域防務與安全合作;加強現有合作,拓展防務與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加強與對話伙伴的聯系;規范的塑造與分享。在東盟防長會議機制下,東盟創建維和中心網絡,舉辦防務產業協作會,開展快速反應合作。
在政治安全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東盟既為傳統安全提供對話平臺,也重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如反恐和災難應對上的合作。反恐方面,東盟與所有對話伙伴國都發表了反恐合作的聯合宣言,并制定了相應的行動計劃。2007年簽署《東盟反恐公約》,為打擊和預防恐怖主義提供了一個區域合作框架,其目的在于深化執法部門和其他權力機構之間的反恐合作。東盟還制定了打擊跨國犯罪行動計劃、無毒品聯合宣言、打擊走私人口公約等一系列涉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聲明。
政治安全共同體的建設也離不開與域外國家和組織的互動,東盟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強化自己在東亞合作中的地位。東盟與外部的安全合作主要依托于東盟地區論壇(ARF)、東亞峰會(EAS)、“東盟+”會議以及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Plus)等機制來實現。其中ARF成員數已達27個,成為本地區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多邊政治和安全對話合作平臺。論壇目前正處于開展預防性外交階段,其標志是2011年7月簽署通過了《東盟地區論壇預防外交工作計劃》。?為支持共同體的建設,同時完善論壇的功能機制,ARF正倡導以行動為導向來檢驗預防性外交的成果,合作領域也正逐漸擴大并深化。另一方面,為繼續深化與對話伙伴在安全和防務問題上的合作,東盟于2010年10月在越南河內成立了ADMM-Plus機制,開展海洋安全、反恐、人道主義援助與災難應對、維和行動、軍事醫療以及后來補充的人道主義排雷行動等五個方面的合作。
作為進程的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關于東盟經濟共同體的總體建設情況,第27屆東盟峰會的主席聲明有意地淡化具體數據,一改歷屆主席聲明中明確完成比率的慣例,僅用了接近完成(near completion)藍圖規劃這樣模糊的描述。這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東盟在推行經濟共同體的過程中,在某些關鍵領域上進展的并不如預想的那樣順利。詳細的數據則在峰會發布的《東盟經濟共同體2015:進展與關鍵成果》中有所體現:截止到2015年10月31日,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完成率為92.7%,在所有506項行動安排中完成了469項。?具體地,四個支柱中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的建設中完成了256項(總計277項),構建競爭力的經濟區完成了154項(總計170項),其余兩個支柱均實現了100%的建成率。
關稅消減方面,在《東盟商品貿易協定(ATIGA)》的框架下,東盟6個老成員國計劃于2010年實現東盟內部貿易進口關稅全免,CLMV新四國則被放寬至2015~2018年。2014年ATIGA平均稅率已降至0.54%,而享受東盟最惠國待遇的域外國家所面臨的稅率則高達6.9%。截止到目前,東盟6國已取消了99.2%的區域內部貨物進口關稅,CLMV國家的這一比例也達到了90.86%。?僅關稅消減本身并不會帶來一個開放市場,為此東盟同時積極開展非關稅領域的合作,具體地有實施便利的原產地認證措施,制定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建立東盟貿易信息庫,消除非關稅貿易壁壘,開發東盟單一窗口系統以及簽署互認協議(MRAs)等。在東盟消減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的努力下,2014年東盟內部貿易額相比于2007年增加了58.9%,稍快于外部貿易額的增長,但內部貿易額占東盟貿易總額的比重仍維持在24.1%的較低水平。
在消減貨物貿易關稅的同時,東盟也在不斷加快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逐步取消服務貿易限制措施。東盟服務市場一體化是在《東盟服務貿易框架協議(AFAS)》下進行的,2014年東盟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已經形成了第九個一攬子計劃。目前,東盟至少有80個服務部門行業向外資開放,放寬了對外資股權的限制。到2015年前,東盟國家要達到至少70%的服務部門向外資開放。?在東盟不斷放寬服務領域投資限制的努力下,東盟服務部門出口增長迅速,貿易赤字已從2005年的273億美元減少至2014年的82億。2013年東盟國家服務部門對實際產出的貢獻接近一半,一些相對發達的成員國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別達到了66.6%和55.2%。
投資自由化方面,2007年8月東盟投資區理事會(AIA Council)整合了1987年《東盟促進和保護投資協議》以及1998年《東盟投資區框架協議》為《東盟全面投資協議(ACIA)》。后者于2012年3月份正式生效,主要特征包含綜合的投資自由化和促進條款;與東盟經濟共同體相應的明確的投資自由化時間表;對在東盟投資設廠的外商獨資企業以更大的優惠;保留了東盟投資區特惠安排;旨在建立一個更加自由化、便利化、透明和競爭性的投資環境。?2014年東盟對ACIA做出了修訂和補充,逐步放寬或取消了投資限制,主要涉及制造業、農業、漁業、林業、采礦業和服務業等領域。東盟投資區已有十余年的建設經驗,在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上成就顯著。2014年東盟地區外資流入占全球比重達到了11%,而2007年這一數值為5%。區域內部FDI流量占比也達到了17.9%,僅次于歐盟對本地區的投資。
在融入全球經濟方面,東盟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0年1月,以東盟為中心的五個自由貿易區(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同時啟動。五個FTA包括了東亞峰會的16個初始成員國,以此為基礎,為進一步推動地區經濟合作,東盟于2011年第19屆峰會上提出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計劃,RCEP指導文件對其定位是現代化、綜合性、高水平的互惠型經濟合作,主要領域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知識產權、競爭機制、爭端解決機制等議題,水平將高于但不替代東盟現有的FTA,且保持開放性吸收其他愿意參加的國家加入談判。?
在培養東盟意識中強調人文關懷。社會文化共同體強調東盟身份的構建與認同,旨在提高東盟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自路線圖宣言發布以來,東盟成員國不斷在加強社會文化領域的合作,以促進東盟共同體建設的如期完成。社會文化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的一個突出貢獻是促進東盟身份的構建和認同,主要的方式是通過舉辦各類文化活動使民眾特別是青年人了解東盟及其成員國的國情。具體的有:利用主流媒體,網絡及新媒體作為東盟重要的溝通和互動工具,促進東盟意識的傳播;把教育作為主要手段,以青年人為主要受眾培養東盟身份認同意識,將東盟知識作為課程學習的一部分等。
東盟在促進人類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于提高東盟人民的幸福感和個人發展的平等機會。為了提高成員國教育水平,東盟依托于現有的教育合作組織和網絡來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優勢資源合作,一是依托成立于1965年的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東盟秘書處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秘書處通過召開會議,利用區域內外資源提升東盟教育水平。2011年,東盟推出《東盟教育五年規劃(2011~2015)》指導成員國發展教育事業。二是依托東盟于1995年成立的東盟大學網絡(AUN),AUN旨在通過促進優先發展領域的交流與研究,來加強東盟高校之間的合作,尤其是推動各國科學家和學者之間的合作,促進地區專業人才的人力資源開發。?根據東盟發布的社會文化共同體中期評估,東盟六國和CLMV國家的成人受教育的平均年限由2005年的7.5年和4.6年分別增加至2010年的8年和5年。青年識字率方面,東盟六國已接近100%,CLMV國家也取得了明顯的進步,2010年這一比例已達到92%。?人類發展指數(HDI)也顯示東盟六國和CLMV國家間的人類發展差距正在進一步縮小,由2005年25%的差距減少至2010年的22.9%。
2010年,東盟成立了促進和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委員會,旨在維護婦女兒童的社會福利和平等發展機會。自委員會成立后,已多次召開會議落實2012~2016年東盟地區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工作計劃。東盟還繼續加強對弱勢及社會邊緣群體的關注,第19屆東盟峰會將2011~2020年宣布為東盟殘疾人十年期,2010年東盟又設立了東盟兒童論壇。在環境保護方面,2015年第13次東盟環境部長會議在河內舉行,會議對2012年第12次會議起東南亞地區環境領域的各項合作安排的落實情況進行了評估,提出了共同體建成后東盟環境合作的建議和舉措。第26屆東盟峰會簽署的《關于進一步規范應對災害和氣候變化的措施宣言》,對于促進本地區協調持續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
后2015東盟共同體建設展望
作為一個由東南亞中小國家組成的區域性合作組織,東盟在復雜多樣的背景下創造性的探索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合作之路。東盟共同體自2003年正式提出以來,歷經十余年的建設,已成功將東盟打造成為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典范。但隨著共同體建設的深入,東盟也面臨著如成員國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宗教文化差異性等等越來越突出的挑戰。如何應對這些困難,相應的成為共同體建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也直接關系著東盟共同體水平的高低。
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挑戰。首先,東盟國家除泰國外二戰期間都曾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這些新興的國家對于主權的訴求較為強烈。東盟在長期合作中形成的以不干涉內政為特征之一的東盟方式,使得當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在涉及主權問題時,無法形成實質性的突破。這也就導致了在東盟在多邊層面的安全合作上,主要通過開展安全對話與合作論壇的形式,很難達成共同安全政策。?例如東盟2006年對于泰國軍事政變的失聲,側面說明了東盟的這一合作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所能達到的高度。
其次,由于歷史經驗的原因,東盟各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有所不同。成員國的經濟基礎和經濟水平極不平衡,各國發展差距過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3年東盟成員國中人均GDP最高的是新加坡,達到了55182美元,最低的柬埔寨為1007美元。人均GDP差距約為55倍,遠高于歐盟內部的15倍和北美自由貿易區5倍的差距水平。?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對東盟一體化目標的實現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目前,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完成率為92.7%,而最后一部分行動計劃的落實將會面臨較大的挑戰,涉及到知識產權貿易保護、非關稅貿易壁壘、勞動力自由流動以及統一東盟產品質量標準等議題,各國在這些深層次問題的分歧程度將對未來談判產生重要影響。事實上,盡管多種關稅已經大幅下調,但各國企業仍面臨非關稅壁壘所帶來的困難。此外,東盟各國基礎設施水平差異,增加了跨境貨物運輸的成本,弱化了成員國深化經濟合作的動力。
最后,東盟共同體的建設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認同和推動方式,東盟民眾對于共同體的認知還較為淺顯,許多企業及個人并不清楚共同體的建立會給他們帶來什么具體益處。越南工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高達80%的越企對經濟共同體知之甚少,僅有10%表示已做好準備應對其成立。迄今為止,東盟在共同體的社會宣傳和公民教育上相對于歐盟當初建立統一市場時所作的努力還有較大的差距。
后2015共同體建設規劃。早在2013年東盟已經著手規劃后2015共同體建設議題,第23屆和第25屆分別發布了“關于后2015東盟共同體愿景”的斯里巴加灣和內比都宣言。第27屆峰會期間東盟領導人簽署通過了《東盟邁向2025年吉隆坡宣言:團結奮進》,宣言規劃了東盟未來10年的發展路線圖,旨在建造一個邁向團結統一、和平穩定以及共享繁榮的共同體;在《東盟憲章》各項目標和原則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恪守法律,以人為本,有著較強凝聚力的共同體;提高東盟應對挑戰的能力,維護好其在東亞合作中的核心作用。為了配合下一階段東盟共同體的愿景規劃,東盟領導人還宣布通過改善運行程序和加強內部協作提升制度執行力,提高東盟內部各機構的工作效率,增強東盟秘書處的作用。
與此同時,意識到成員國之間極大的發展差距對于共同體建設的負面作用,東盟一體化倡議專責小組正在和各國著手制定東盟一體化倡議第三階段(IAI Work Plan III)的工作計劃。今后東盟縮小發展差距的合作將聚焦于糧食與農業、貿易便利化、中小微型企業發展、教育、衛生與福利等五大優先領域。對外經濟合作方面,東盟也在抓緊結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
根據東盟后2015共同體建設愿景的規劃,到2025年東盟將建成一個團結自強、包容性的政治安全共同體;密切聯系、競爭力強、創新活躍、融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東盟經濟共同體;吸引廣泛人民參與且給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的東盟文化社會共同體。這同時也是包容性、可持續發展、自強與活躍的共同體。
東盟共同體的進程化
回顧東盟共同體的建設歷程,可以看到,東盟將共同體進程化是其在推進共同體建設過程中被動調整的結果。從最初主動將共同體的建成時間提前,建立打分卡制度、定期發布共同體的建設進展,到每一屆峰會更新共同體的進度數據等等,東盟最開始是將共同體的建設作為一個非連續的、階段性目標來推進,即預想在2015年底至少要達到一個特定且具體的目標,如三個共同體均實現100%的完成率等。但隨著共同體建設的深化,在一些關鍵領域,如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消除非關稅壁壘等方面,成員國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地涉及邊界內議題,這與東盟一貫形成的不干涉內政等合作規范有所沖突,共同體建設的推動難度也越來越大,東盟逐漸意識到全面落實2015目標已漸行漸遠。
東盟共同體的進程化體現了東盟推行共同體建設的韌性和決心。在本地區深化合作遇到較大阻力的背景下,將共同體進程化可以督促成員國采取持續的行動,來推進東盟一體化進程。轉變以往對完成進度的強調,可以避免共同體建設陷入停滯的局面,有助于東盟形象的維護。
但另一方面,一個作為進程的東盟共同體建設,事實上也是東盟對諸如邊界內等敏感議題的妥協,這也對未來東盟能否盡快在這些領域實現實質性突破提出了考驗。不難看出,東盟共同體的進程化會對本地區的經濟合作造成一定的影響。進程化由于缺乏嚴格的時間安排機制,容易產生合作惰性,即習慣性地不斷將一些較為棘手的談判議題推后,其結果必然是放緩后2015東盟共同體的建設進度。而對于東盟所主導的RCEP談判,受東盟在本地區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的影響,東盟共同體中未能實現的目標,很難在RCEP談判中得到有效的推動,后者的談判質量也無法得到保證。因此,即使在共同體建設進程化的趨勢下,東盟仍然需要一個相對寬松但清晰的時間安排,以避免成員國陷入合作惰性,盡可能地加快后2015建設議程,確保共同體建設仍然在一個相當可控的框架下進行。
進程化意味著東盟共同體至少在中長期將是伴隨東盟合作的常態化目標,尤其是東盟消除內部發展差距、培養區域認同等目標的實現,都需要與對話伙伴與國際社會的互動與合作。一方面,合作、特別是互聯互通和產業領域的合作,是東盟經濟均衡發展難題的必要條件,而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對于塑造東盟身份也是一個不可少的過程。這對作為東盟近鄰和密切合作伙伴的中國,意味著持續的合作機遇,特別是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討務實合作的雙贏空間。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王偉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注釋
鄭先武:《“安全共同體”理論和東盟的實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5期,第23頁。
張蘊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75~76、148~150頁。
韋紅:《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建設及其對中國的意義》,《當代亞太》,2006年第5期,第54頁。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ocio-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June 2009: 2.
魯道夫·塞韋里諾著,王玉主譯:《東南亞共同體建設探源——來自東盟前任秘書長的洞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14頁。
《東盟秘書長黎梁明:東盟共同體建成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參見:http://zh.vietnamplus.vn/東盟秘書長黎梁明東盟共同體建成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44781.vnp,訪問時間:2016年7月20日。
ASEAN Secretariat, Cha-Am Hua Hin Declaration on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October 2009: 1.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and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the Adoption of the ASEAN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February 2013: 2.
駱永昆:《東盟共同體建設的進程、動因及前景》,《國際研究參考》,2016年第2期,第1~7頁。
周玉淵:《從東盟到東盟共同體:東盟決策的模式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第201頁。
趙海立:《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成就與問題》,《南洋問題研究》,2015年第4期,第44頁。
ASEAN Secretaria,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2015: Progress and Key Achievements,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November 2015: 17.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Integration Report 2015,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November 2015: 22.
王勤:《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的進程與成效》,《南洋問題研究》,2015年第4期,第6頁。
AIA Council,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Tenth ASEAN Investment Area Council Meeting, Makati City, 23 August 2007.
ASEAN Secretariat, Mid-Term Review of the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09-2015),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February 2014: 16.
馬孆:《東盟安全戰略的演變與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08年第2期,第60~64頁。
王偉:《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與發展評述》,《亞太經濟》,2015年第5期,第18頁。
張蘊嶺:《如何認識和理解東盟——包容性原則與東盟成功的經驗》,《當代亞太》,2015年第1期,第4~20頁。
欒鶴:《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尋求新突破》,《中國貿易報》,2016年2月4日,第2版。
《東盟各國就縮小發展差距的戰略優先達成一致》,參見:http://zh.vietnamplus.vn/東盟各國就縮小發展差距的戰略優先達成一致/49529.vnp,訪問時間:2016年7月21日。
王玉主:《東盟經濟共同體進展2014》,見陸建人、范祚軍主編:《中國—東盟合作發展報告(2014~201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59頁。
責 編/凌肖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