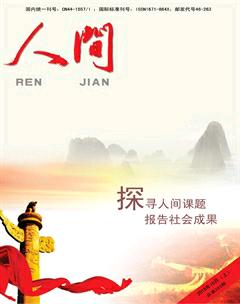試析20世紀日本對外戰略選擇
摘要:20世紀日本作為新興的大國,其對外戰略不僅與國家利益有關,而且與國際體系交相作用。在一個多世紀的崛起過程中,日本面臨著三種戰略選擇:和平擴張、軍事征服和商業福利。20世紀末期,日本積極爭取由經濟大國走向世界政治大國。日本的每一次對外戰略選擇都對地區和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關鍵詞:軍事擴張主義;“搭車”戰略;政治大國戰略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0-0027-02
自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崛起為亞洲強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獲勝后,日本奠定了亞洲第一強國地位。在一個多世紀的崛起過程中,日本面臨著三種戰略選擇:和平擴張、軍事征服和商業福利。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國內形成了和平擴張與軍國主義兩種對立的對外戰略主張,到世紀之交,在強大實力和帝國主義欲望的雙重刺激下,日本決定性的選擇了軍國主義道路,其權勢急劇擴張,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徹底覆滅;戰后,日本加入西方陣營,推行“搭車”戰略,一舉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并在世紀末努力向政治大國邁進。無論是軍事擴張主義,經濟立國戰略,還是當前的政治大國政策,日本對外戰略的基本目標始終是突破現狀,爭當世界大國。鑒于其國家規模和潛力,特別是鑒于其至今尚未深刻反省的擴展歷史和亞洲各國的沉痛回憶,日本爭當世界大國而不是中等強國,不僅對日本,而且對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含義。
一、軍事擴張主義及其破產
日本選擇對外軍事擴張,不僅源于國家實力的增強和全球視野的形成,而且源于日本的文化傳統及其對自身地緣戰略處境的認識。擴展思想是近代日本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脫亞入歐”的基本方針就含有擴張成份。福澤諭吉寫到:“我國不可猶豫,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辦法,不必顧其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①按照這個指導思想,日本要采取西洋人恃強凌弱、侵略擴張的辦法,將朝鮮和中國作為擴張目標。19世紀中晚期,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在日本流行,思想文化界的擴張主義者認為,在列強競爭面前,日本不能退守,必須進攻,主張向海外擴張勢力,侵略朝鮮和中國。日本政界和軍方也持有同樣的主張。他們從列強相互爭奪的國際現狀出發,認為領土擴張是建立現代強國的捷徑,每個民族都必須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曾任首相、陸軍大臣和內務大臣的山縣有朋反復強調,在列強競爭的國際環境中,日本國家安全的基本要求,在于絕不能讓中國或任何歐洲列強控制朝鮮,而是必須使其成為日本的勢力范圍。
1931年到1945年,日本為了轉嫁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發動并擴大對華戰爭,進攻太平洋,南下東南亞,企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根本沒有認識到日本作為島國的地緣戰略劣勢和經濟力量限制,同時與中國、英國、法國和美國四大國及其他亞洲各國為敵,最終遭到慘重失敗,其軍事擴張戰略宣告破產。
二、與美國結盟的“搭車”戰略
戰爭改變了日本的命運,而戰后的國際國內環境則帶來了日本對外戰略的革命。美國單獨占領日本,為防范日本東山再起,按美國模式實施民主化改革,整肅軍國主義勢力,審判戰犯,修改憲法,解散財閥,推行農地改革。隨著冷戰的形成和中國革命的節節勝利,美國改變對日政策,從懲罰轉向扶持,支持保守政治勢力,復興日本經濟,將日本納入遏制戰略的軌道,其結果是1950年9月的片面對日媾和以及美日軍事同盟的建立。在此過程中,日本所面臨的更為急迫的任務,是如何擺脫美國的軍事占領,恢復主權獨立,重建國家經濟。以吉田茂為代表的親美派清楚地認識到,日本是一個喪失了主權地位的戰敗國,國內經濟完全崩潰,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根本不可能通過軍事手段達到復興目的。另一方面,在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相互對峙的國際環境下,日本在國際舞臺上不可能有多大作為,日本必須加入西方陣營,以圖本國安全,恢復經濟,通過經濟和外交手段振興日本。②在此認識基礎上,吉田茂確立了“重經濟、輕軍事、向美一邊倒”,在外交上與美國結盟的“搭車”戰略,以美日關系為主軸,以經濟外交為手段,致力于日本的復興。
“搭車”戰略為日本帶來了豐厚的“和平紅利”。首先,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日本全力發展和恢復經濟。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特需的刺激以及20世紀60年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推動,經濟全面高速增長,一躍而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其次,日本開展經濟外交,大大推動了經濟發展。在亞洲,日本通過實施大規模的政府開發援助項目,既處理了與東南亞國家的戰爭賠償問題,又打開了東南亞市場;對歐美國家,日本則在美國的寬容下推行“民族主義的經濟外交”,通過高關稅、糧食進口限制和嚴格的外匯管理擴大進出口貿易,促進經濟迅速發展。③第三,日本重返國際舞臺,成為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世界的重要一員。
三、謀求政治大國地位
政治大國的概念首次由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提出。當年7月30日,他在一次競選演講中稱,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不僅要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份量。這是日本政府首次將爭當政治大國作為一項國家政策提出,此后的日本歷屆政府都將其作為對外戰略目標。隨著冷戰結束,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更趨明朗。日本外務省在1991年提出,日本要為構筑國際新秩序發揮影響,特別是在亞太地區起“中心作用”;1992年又提出,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日本不僅要在國家經濟領域發揮作用,而且要在政治方面和全球問題上發揮影響,“日本必須向國際社會闡明它爭取建立什么樣的世界,追求什么樣的目標,并且發揮與國力相稱的領導力量。”③與此相應,政治家和民間學者也認為,日本必須抓住國際關系正經歷著變化調整的大好機遇,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和影響,爭取成為“國際秩序的締結者”、“大國外交的推進者”、“國際社會的決策者”以及“國際關系的協調者”。
日本爭當政治大國的外交政策措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進一步加強日美關系。日本在全面崛起過程中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是如何處理對美關系。冷戰結束后,隨著共同敵人蘇聯的消失,美日同盟的原有基礎發生動搖,美日關系面臨新的挑戰。美國出現了“安保掛鉤輪”,即主張利用美國的安全保護換取日本的經濟讓步,由此出現了美國“敲打日本”現象。④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向美國說“不”的強烈呼聲和政策主張。盡管美日兩國間有相互不滿情緒,但它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大于經貿分歧,經過幾年的波折和磨合,日本政府明確指出,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美日關系是日本對外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在日本遇到威脅時,只有美國有能力并且愿意提供保護。第二,積極謀求亞太事務的領導權。日本的地緣戰略和經濟貿易利益,決定了亞太是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依托,因此,日本政府強調亞太是日本外交的關鍵,要在亞太地區發揮“中心作用”。一是以東盟為核心,促進東亞多邊合作,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二是推動建立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繼續加強與東盟安全論壇的對話,積極參與東北亞安全事務特別是朝鮮核危機的解決。三是重視發展日中關系,借重中國的政治影響走向世界,依靠中國的龐大市場發展經貿合作。第三,積極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日本首次提出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此后,日本加大了外交力度。一是日本政要和外務省專門機構積極游說各方同意擴大安理會,為日本最終成為常任理事國做鋪墊;二是增加對聯合國的財政貢獻,近年來承擔了聯合國20%的會費。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會費分攤國;三是積極爭取日本公民當選聯合國專門機構高級職務,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四是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
最近十多年來一系列事態表明,日本正在加緊走向政治大國。無論是派遣自衛隊到伊拉克,進一步推動軍事外向化,修改憲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還是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為了追求世界大國地位這個根本目標,這是日本對外戰略的總方向。
參考文獻:
[1]張雅麗.《戰后日本對外戰略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2][日]吉田茂.《激蕩的百年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頁.
[3]包霞琴、臧志軍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時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頁、第201頁.
[4]林華生.《亞洲“四級”經濟》,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
[5]勝天昭夫.《日本造》,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244頁.
作者簡介:張桂芬(1964----),女,廣東興寧人,中共安順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