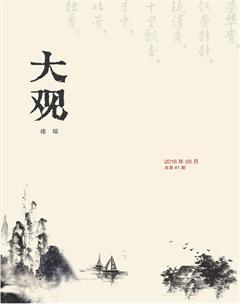民族精神與中國法治
摘要:薩維尼的民族精神論思想認為法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自給自足與自我演進的過程,法的本質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法的最好來源是習慣,主張從歷史的角度去建構具備民族精神的本土化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今天,法律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法律需要一定的獨立性,法律的獨立性要求法律本身應當有一套符合自身發展的完整體系。
關鍵詞:民族精神;精英法;法治
一、引言
薩維尼在《論立法及法學的當代使命》中提出,法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識的體現。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共同性格、共同意識, 因而他們的法律也自然是不相同的,適用于所有民族和任何時期的法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面臨的國家市場流動也很大,支持它的司法資源很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法治建設更需要重視立法:法律應源于民族共同意識和行為方式,法典必須通過科學手段達到全面與完美;立法必須審慎,必須確定立法原則,并要具備立法時機和立法條件。
二、法的起源與民族精神
(一)歷史背景
薩維尼首先闡述了本課題的背景,Napoleon的德國國家統一和社會政治的要求實現了后,以及相應的浪漫主義情懷。在這樣的背景下, 薩維尼對以瑞赫貝格和蒂博為代表的論戰雙方的觀點作了簡單的評述,立即發表《關于當代立法和法律的使命》這本小冊子,從本體論的角度來闡明他們對法律的看法,通過物權法的起源,也就是法律是民族精神對蒂博觀點的產品。它指出,在德國當時根本沒有制定法律的條件。可見,薩維尼認為法律是民族所特有的,法律必須體現本民族的共同信念。
薩維尼認為,法律的發展,就如同人類的語言,是有機的連續性,與國家共存亡,在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并沒有決定性的破碎的時刻,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沒有人為創造的痕跡。這樣的方式適用于人類文明的初始階段,在此階段習慣法是法律的最佳表達方式。薩維尼認為當時的德國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研究歷史,因為民族精神就體現在歷史當中,法律的根基也在歷史中,民族精神與法律是源與流的關系,而法律又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因此,要制定出完備的民法典就必須先研究歷史,在對歷史的研究中去探尋先哲們的智慧,從而掌握法律的精髓。
(二)民族精神與宗教意識
薩維尼在《論立法及法學的當代使命》中提出了法律起源的理論,他認為法律的起源是民族精神。①梁治平先生說,“探索法治的價值是發現法在開始真正的生活”。②這讓我想起了前幾天看過的一篇文章——楊小凱先生的《基督教與憲政》,講的就是宗教把人的價值改變了,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哪些行為不可以接受,而宗教信仰是人們對于一些宗教現象的主觀認識,是人們對宗教的主觀心理境界。美國當代著名的法學家伯爾曼說,法律不僅僅是工具,它還體現為一種價值、一種理想、一種人們為之奮斗的理想。③只有關注法律價值,才能培養起公民對法律的情感和信仰。“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④否則法治將難以實現。對法律的信仰便是這種民族精神最直接的體現。
三、法治之民族精神
薩維尼突出強調了法律的民族特性,他認為不存在具備普遍理性的自然法,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自然而然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只有民族精神與民族共同意識才是法律的真正創造者。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這種體現民族精神的法律形式是習慣法當文明逐漸發展以后,體現民族精神、社會意識的存在,以習慣法為法定假法學家之手制定,法律也因此而獲得了其獨特的科學性存在。”
按薩維尼的說法,藉由“民族的道德力量”,法律權威即可達臻圓融之境”⑤,只有根據歷史傳統,才會有具備民族精神的法治制度。然而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僅需要道德規范來加以調整,政治、法律、宗教以及各種有關的行政措施和規章制度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們之間的關系起著調整的作用。法治,不僅是我們平時對法治的認識在制度層面上的運作,更重要的是它此種文明以及與在其中生活中人們達到了一個環環相連的默契,形成一種絲絲入扣的磨合。
四、法治之精英法律
在今天看來,薩維尼的民族精神論提醒了人們在對本土法律傳統、法律文化與習慣關注的同時,面對當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矛盾。
薩維尼的“民族精神”法律思想是時代的產物,迎合了歷史的需要,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其特有的魅力。成功的東西往往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⑥立足于本民族,挖掘歷史,研究法律的沿襲脈絡才能為今天的法學探索樹立“鏡子”。同時,世界法律文明中也存在著某些共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原則和精神。當今的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表明,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在認知能力、理解能力、思維能力等方面都有類似的特點和規律。同時,人類面臨著生存和發展方面的,如環境、安全等多方面的共同問題。
同一時期不同的國家往往經濟發展不平衡,他們或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或處于同一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都不可能脫離世界法律文明發展的大道而發展。自有國家以來,幾乎任何形式的法律文化都避免不了法律之間的精英法移植問題,因為其大前提是國家民族的文化有互動的關系。
五、結語
立法的任務就是從歷史或者“潛在的影響力”中發現法律。薩維尼的民族精神說強調了民族法有其特殊的性格,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屬于自然的成長,而不是認為的制作;法的成長是隨“民族共同信念”這一有機體的成長而成長的……這都提醒我們,立法者在制定新法時,對傳統必須加以斟酌考量,以免使新法成為廢紙或成為民族成長的枷鎖。正確的法治模式應該是法治的普遍性原理與自己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在高度重視人們現代法律意識的培養的同時,逐漸形成對現代法治精神和價值取向的認同和接受,克服傳統法制觀念,達到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觀念性法律文化的內在協調。中國的法治建設之路是一個演進的過程,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法治的核心是合理性,我們不能片面的選擇某一種模式或者某一條道路,今天,在研究薩維尼的民族精神時,應該放大其民族的范疇,以民族為根,推動本民族法律的發展。
【注釋】
①薩維尼.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M].許章潤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11.
②梁治平.法辯[M].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196.
③田成友,肖麗萍.法治模式與中國法治之路[J].法學,1998(09).
④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北京:三聯書店,1991:16.
⑤薩維尼.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M].許章潤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18.
⑥楊小凱.《基督教與憲政》
【參考文獻】
[1]黎四奇.對薩維尼“民族精神”的解讀與評價[J].德國研究,2006(2).
[2]孟慶友.薩維尼“民族精神”說的政治智慧[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2).
[3]龐德.法理學/(美)羅斯科[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4]高江波.淺評薩維尼與民族精神[J].法治與社會,2008(08).
[5]馬凱.薩維尼“民族精神論”的迷思[J].平頂山學院學報,2008(6).
[6]邢元振,盧維良.論薩維尼的歷史法學觀[J].天府新論,2007(12).
[7]張繼宏,張菲菲.論法治現代化進程中法律文化的發展[J].政法行政,2009(2).
作者簡介:楊雪燕(1982—),女,河南省新鄭市人,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