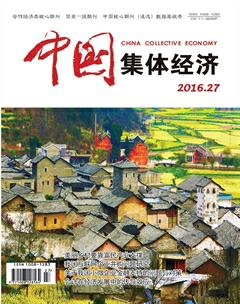運動式治理的社會效應探究
劉長生+裴越
摘要:運動式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進行群眾動員和專項整治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運動式治理以其快速高效、立竿見影解決特定問題的特點而使各級政府樂意為之并產生一定治理成果:另一方面,運動治理的諸如治理成本虛高、權力行使不規范、治理結果反彈等問題也日漸受到詬病和反思,文章通過辯證分析運動式治理的社會效應,以期引發人們對治理現代化的思考,
關鍵詞:運動式治理;社會效應;常規治理
一、引言
運動式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進行群眾動員和專項整治的重要方式,作為一種理論或模式則是近年來國內學者在研究公共突發事件中政府應急反應與治理能力的語境下提出的。根據筆者掌握的文獻,關于運動式治理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對運動式治理的概念界定與特征把握:2.從不同維度分析運動式治理的成因:3.關于運動式治理的優劣分析。在對運動式治理的社會效應分析方面,多數學者持“一邊倒”的態度,得出運動式治理應向常態治理、制度化治理轉變的結論。當然,也有一部分學者在論述運動式治理生成的必然性時,注意到運動式治理的某些優點,指出,該種治理手段是“在現有國家治理資源貧乏的限制性條件下政府的一種必然選擇”,有助于緩解轉型時期因國家治理資源不足而造成的困境。
綜合學界觀點,本部分從正功能、負功能兩個方面入手對運動式治理進行辯證分析。一方面,通過分析運動式治理在重大社會問題處理、疏導民意與向基層輸送合法性、對政治運轉的潤滑以及對政治改革的催化等方面的正功能,對運動式治理予以有限承認:;另一方面,基于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對運動式治理從開展到效果反饋做出全面的反思,對其助長投機心理和規則虛無主義、權力行使不規范、治理效果的低經濟性、與法治精神相悖等負功能予以揭露。在此基礎上筆者做出簡單的思考——對運動式治理有限承認,更對運動式治理與專業化、制度化、常態化治理的內在張力作出分析,同時對運動式治理活動化予以評析,最終說明運動式治理之于治理現代化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二、運動式治理的正功能
盡管運動式治理近年來飽受詬病,但基于中國制度化不足、社會資源匱乏的現實背景以及特有的政治、文化結構,這一機制也在治理實踐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一)在疏導民意和重大問題處理方面彰顯有效性
運動式治理是與“群眾路線”密切相關的,在某些重大問題的解決方面,運動式治理是民眾議程設置的結果。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政府在解決公共問題、制定公共政策上的選擇性。當一項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重視以致積重難返、民怨沸騰時,參與的制度化不足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導致群體性事件。此時政府以專項運動的形式自上而下集中整治、重點突破,“療程短,見效快”,可以較為有效的疏導民意,滿足民眾訴求。同時,自上而下的動員也為廣大民眾政治參與、利益表達開辟了一個特殊渠道。當運動式治理是為作為利益相關方的民眾而發動,那么其公共性就較強,且官方的治理目標與民眾的預期結果越一致,公民的參與熱情與參與程度越高。
從治理實踐來看,主要分為兩類:第一,對于社會頑疾的定期專項治理,第二,對于突發事件、公共危機的特別治理。以強力的方式修復被突發事件破壞的秩序,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群眾心理秩序恢復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彰顯政府的權威和執行力。
(二)推動國家向基層輸送合法性
運動式治理一定程度上是對基層意識形態自主性的挑戰,有助于向基層輸送國家政治體系的權威與合法性。長期以來,國家政治體系的權威與合法性都沒有很成功地深入基層,基層民眾具有自發的、異于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規則,尤其是當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與基層的傳統觀念存在沖突情況下,基層自發的規則秩序相比于國家的法律規章更具話語權。學者張靜將之稱為“鄉規民約下的村莊治權”。每一次自上而下的運動式治理也就成為國家政權向基層輸送合法性,更新基層民主意識形態的過程。作為政治體系的末梢,基層受到運動式治理的影響可能并沒有很顯著的效果,但每一次運動式模式的治理活動都沖擊著傳統的“鄉規民約”,與城鎮化相伴,日漸改變著基層的政治意識和生態,使得國家權力在縱向深度上推進。
(三)政治運轉的潤滑劑
首先,運動式治理提高了國家的汲取能力,緩解了治理資源不足的困境。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提高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治理資源貧乏的狀況,但面對超大的社會結構中國的社會治理資源仍然比較緊缺,特別是建立在部門分割的基礎上,用于常規治理的資源極其有限。運動式治理針對特定治理目標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自上而下實現國家意志,產生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效果,諸如奧運會、世博會以及近期舉辦的APEC會議,都是通過“大會戰”式的運動式治理,舉社會之力增強國家能力,贏得民眾認同。
其次,運動式治理是對科層制下結構僵化、治理失靈的一種潤滑與糾偏。常規治理是通過科層制的分工來完成的,但其在中國政治系統中的畸形發展造成結構鋼化、邊界高筑,運動式治理正是因為常規機制的失敗而啟動。第一,為達成治理目標,運動式治理以其全面聯動的形式較為有效的促進了各部門的合作,彌補了官僚體制內條塊矛盾、機構冗雜重疊、職能劃分不明確等一系列缺陷:第二,運動式治理作為一種自上而下貫徹國家意志的治理行為,有助于克服中國官僚體制的人格化傾向和部門政治利益,打破因信息不對稱、權力尋租等而形成的官僚自主性,一定程度上保證政令的暢通,是對“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現象的回應。
(四)政治改革的催化劑
由于長期積弊和制度創新的成本,偶發的運動式治理作為常規治理的輔助手段和外部救濟措施,還承擔著探索更優治理路徑的功能,期間有可能孕育著新的規則,為制度改革和治理的專業化、常規化掃清障礙。因為運動式治理集中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以暴風雨式的行動對某一社會問題專項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障礙和格局,從而為構造新的治理秩序鋪設道路。運動式治理與常規治理好比“治標”與“治本”的關系,“治標”為“治本”掃除障礙、鋪平道路。
三、運動式治理的負效應
作為一種非常規的治理手段,運動式治理從發起到過程開展,再到效果反饋,都顯現著對治理制度化、現代化的負功能以及對法治精神的相悖。
(一)助長投機心理,漠視規則制度
“暴風驟雨”式的運動式治理為治理主體與客體都創造了投機取巧的機會。首先,由于運動式治理具有“療程短,見效快”的特點,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在畸形政績觀主導下,治理主體往往對一些潛在問題不聞不問,對已經顯露苗頭的公共問題視而不見,直至他們惡性發展至一定程度,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時才開展專項治理活動,通過宣傳造勢與集中行動博取眼球,營造大政績。其次,對于治理治理客體而言,由于把握了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運動偏好和運動周期,所以會有策略的與治理主體“打游擊”——運動尚未開展則肆意而為,擾亂社會正常秩序,運動開始前又因大張旗鼓的宣傳可以聞風停止作案、銷毀證據,運動風聲一過很快死灰復燃。這也是為何一些社會問題屢治屢犯,治標不治本的一個關鍵原因。
然而,更為惡劣的影響是運動式治理模式下的社會將產生一種對規則、制度的漠視。政府有能力卻不作為,只等問題突出、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焦點才重點整治一番,這等惰政行為使得已有的常規治理手段不被啟動而柬之高閣,而在運動式治理過程中由于需要多方聯動又會突破常規界限,使得制度精神很難發揮,喪失了制度設計的初衷。另一方面,周期性運動式治理的對常規制度的打破還會使得制度在民眾心中無足輕重、形同虛設,從而很難使民眾產生對法律、制度和規章的敬畏,而這是治理現代化、法治化的頭號敵人。
(二)權力行使不規范,導致治理扭曲
運動式治理追求行動高效,必然打破常規制度,謀求權力的非程序化使用。首先,運動式治理的目標預定性導致主要負責人很可能根據主觀臆斷發號施令而不顧地方實際,造成壓力體制下各級治理主體逢迎上級喜好,追求面子工程:其次,權力具有擴張性,運動式治理是一個自上而下任務層層分解執行的治理過程,這使得掌握全權的地方治理主體為超額完成任務或追求個人私利,層層加碼,不斷擴大目標范圍和執行的力度以至于達到嚴苛的地步:再次,權力的任意性使得治理主體在界定治理客體和治理范圍上具有選擇性。由于各級治理主體同時也可能是被治理對象,所以治理主體會設法打政策的擦邊球,以種種借口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由于治理主體掌握著圈定治理范圍的權力,部分既得利益者很可能通過權錢交易的方式規避運動的風浪,不僅導致治理流于形式,還滋生了權力腐敗。即使發起運動式治理的初衷是好的,也很難達到預期效果。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運動式治理的過程是將政治性凌駕于專業性之上,它極大地破壞了官僚科層制的穩定結構。治理的現代化將專業性至于首要位置,并一定程度上要求價值客觀公正性。而運動式治理與壓力體制的結合,致使“以紅統專”,政治忠誠成為首要考核指標,而治理成效則置于其次,這與治理現代化背道而馳。此外,運動式治理打破了常規的行政系統邊界,破壞了科層劃分下部門的日常職能和穩定結構。
(三)治理效果的低經濟性
常規治理是制度化、經濟性的治理行為,十分注重治理的成本和效益。而運動式治理在治理的成本與成效的評估方面多是一筆糊涂賬。首先,治理成本虛高,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運動式治理往往在缺乏對事態全面、科學評估的狀態下就盲目調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專項整治,且隨著治理的層層加碼,投入的資源數量更加巨大。巨大的資源投入在調撥與使用中多沒有公開、公示制度把關,不能不懷疑其中存在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等行為。
其次,從治理效果而言,運動式治理雖然是立竿見影,但絕不能忽視治理結果的反復性。運動式治理的反彈與反復,不僅是一次次資源的重復投入與浪費,更是對政府威信的挑戰,民眾將因此質疑政府的施政能力,政府公信力受到威脅。而由于運動式治理造成的“規則虛無主義”,政府常規治理的權威也難以保障。運動式治理雖然為民眾參與開辟了特殊渠道,也為國家向基層輸送合法性提供了可能,但是這一切都取決于運動式治理行動、目標與民眾預期一致的程度。當二者趨于一致時,運動式治理尚能發揮較為理想的效果,當二者不一致甚至有所沖突時,運動式治理不僅不能實現政治參與和合法性灌輸的功能,還會威脅社會因公共問題而已經脆弱的正常秩序。特別是在制度化水平不足的情況下,被動員起來的民意得不到滿足有可能造成政治秩序的動蕩。巨大的資源投入與有限的治理成效共同構成了運動式治理的低經濟性。
四、對運動式治理的總結與思考
首先,運動式治理基于特定機制而產生,應有限承認。運動式治理產生于特定的實踐機制,是既有體制下治理資源不足的被迫選擇,在危機應對、重點公共問題處理以及民眾動員、統一行動等方面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部分運動式治理其次,運動式治理與常規治理存在張力,悖于治理現代化。
其次,常規治理即治理的專業化、制度化、常態化,運動式治理在這幾方面都對治理現代化構成挑戰。第一,運動式治理的“以紅統專”使得政治化凌駕于專業化基礎之上,可能導致外行指揮內行,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泛政治化。第二,運動式治理在助長投機心理的同時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對規則的漠視,治理本身也是對日常制度的打破。此外,常規治理要求權力有限制、受監督,這與運動式治理權力的全權性、隨意性以及不受監督形成反照。第三,運動式治理由于集中力量,從嚴從重,很可能在打破沉疴的同時波及正常社會經濟秩序,其對法律、規則的態度也是工具主義的。運動式治理與常態化的現代化治理具有內在的張力和沖突,這也決定了運動式治理向常態治理轉變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鴻溝。
再次,要密切關注運動式治理的“變體”——活動。由于運動式治理近年來飽受詬病,各級政府也在有意識的規避這一治理手段的稱呼和使用,但在探索制度化治理的過程中,運動式治理與活動相扭結,有“移花接木”的可能。為運動式的治理手段套上活動的外衣,以活動的方式來整肅秩序、整合資源,之后又力圖將經驗成果模板化,嘗試建立類似日常化的長效機制,這點在執政黨作風建設和意識形態宣教方面表現得尤其典型。作為運動式治理的翻版,活動的經驗誠然能為日常化治理提供借鑒,但不可忽視其中政治權威的推動力以及短時期對物質、人力資源的聚集,而日常化的機制則無法時刻運用領導的權威來集中大批資源用于全面治理。所以,實現治理現代化要轉變運動思維,從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人手,打破路徑依賴,而不是“老樹開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