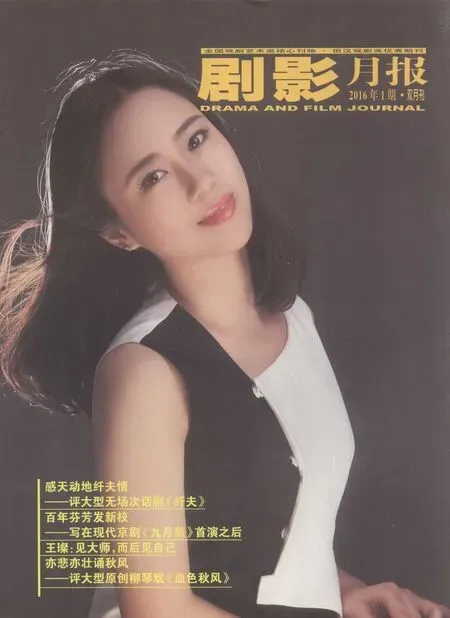亦悲亦壯誦秋風——評大型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
■朱蓓蕾
?
亦悲亦壯誦秋風——評大型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
■朱蓓蕾
大型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作為國家公祭選調劇目,去年12月在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上演。該劇由朱正亞編劇、張建強導演、江蘇省柳琴劇院演出。央視十一頻道對全場演出進行了采錄,并對編劇、導演、主演和制作人分別做了采訪。
當晚,南京人民大會堂座無虛席,觀眾報以連續不斷熱烈的掌聲,無疑是對演出成功的褒獎。省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對該劇給予了一致的好評并且寄予期望。
據了解,此劇自去年9月份付排公演,已經巡回演出十幾場,所到之處,無不受到廣泛的好評和強烈的反響。一部戲曲作品,能在眾多同類題材中脫穎而出,并且經過了市場檢驗,可貴的是,這個戲能引起年輕觀眾群體的共鳴。之所以被選調為2015年“12.13”國家公祭紀念活動展演劇目,觀看后方知,的確有它的獨到之處。
一.歷久彌新的劇本
《血色秋風》文學本,創作于1995年,并在當年《劇本》雜志第12期發表。編劇笑說:“‘待字閨中’整整20年,其間,雖也有幾次‘媒聘’,終究無果。還是江蘇省柳琴劇院,不嫌‘大齡剩女’,‘迎娶’了去,這才讓‘丑媳婦見了公婆’”。機緣巧合么?當然,卻也不全然。我們知道,戲曲現代戲劇本,往往局限于時效。一個擱置案頭20年之久的現代戲曲文本還能搬上舞臺,而且受到廣泛歡迎,這本身就是故事了。而故事之所以可以發生,應該是這個劇本的存活力所致。
著名作家楊守松先生在評點編劇的一部中篇小說的文章中,特意提及了這個劇本。他認為編劇寫了一個經歷了“在抗戰年代睿智的抗爭與悲壯的洗禮”的小人物,這個小人物就是劇中的解文柏。編劇介紹,這個舞臺形象是有史實原型的。雖然名不見經傳,也無史料記載,但是,老一輩敘說他的傳奇經歷,的確栩栩如生。一個販豬賣肉的生意人,戰火硝煙的年代,為了生存,打躬作揖,笑臉迎送,大把撒錢,八面玲瓏。起點于江湖義氣,堅持在人格底線。但他明確是非,區分正邪。正義和善良促使他有了選擇,有了傾向。講句場面上的話,艱苦卓絕的抗戰,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后的勝利,不正是有千千萬萬解文柏這樣的中國人不畏死的奮爭嗎?!可以這樣認為,這個戲詮釋了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重要意義之一,這就是國家危亡之際中華民族的覺醒!
雖然很多的先輩,當時并沒將自己的行為上升到民族大義、民族精神的高度。但是,他們選擇去做了,乃至義無反顧。所以,緬懷先烈,以崇敬之情唱誦他們的舍命業績,應當是我們不可推卻的責任。像是套話,但言出由衷。
演出本比較文學本,已經大相徑庭。雖然還是原來的那些劇中人,但是現在舞臺呈現的,已經是許多人的智慧疊加,尤其是初排演出后,南京專家論證會上的意見和建議,使得這個戲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再次看了演出的專家和同行均認為“越改越好”了。所以,大型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或許有每演每新的期待。
二.起伏跌宕的劇情
大型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給我們講述了這樣的感人故事: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寇屠城,30余萬同胞罹難!解文柏和顧家駒,曾經的同門師兄弟,一個是生意人,一個是國軍營長。顧家駒戰場逃生,和解文柏在逃生途中相遇,并得到共產黨人孫敬亭救護,逃回微山湖畔老家。四年后,顧家駒做了“皇協軍”團長,解文柏則憑著膽識、睿智,夾縫里謀生,生意人靈活的特質,使得他游刃于八路軍地方武裝和日偽之間而企求平安。
然而,大義面前,解文柏主動或被動的同情革命,敬佩共產黨人,傾向抗戰。不顧妻子儲二蘭勸阻,就有了“狼窩贖人”、“土地廟交心、“夤夜結拜”等舉動。終因小舅子儲三喜出賣,親眼目睹愛女解紅菱死于鬼子刺刀之下,與中共里堡區區長孫敬亭一同被捕。孫敬亭經受酷刑的大義凜然,加上親身經歷的殘酷現實,使得解文柏發出“國破哪有家興旺”的吶喊。“獄中入黨”,個人信義升華為民族大義。
當年被迫嫁給顧家駒的呂云娟,曾與解文柏相互愛慕,對比之下,顧家駒的窮兇極惡,迫使呂云娟搏命刺殺顧家駒,被顧家駒槍殺。解文柏再次被捕,慘遭活埋……
柳琴戲《血色秋風》之所以引人入勝,在于復雜交錯的人物關系的設置,主線和副線清晰明了,呼應得當。因此,就構成了好看的戲劇情節,步步推進,環環相扣。跌宕而合乎情理,起伏而出乎意料。讓觀眾始終為人物的命運走向所吸引,為之感動,為之喝彩。尤其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對于劇中解文柏水到渠成的最終抉擇,不少觀眾熱淚盈眶,乃至起立鼓掌。既是對演員精彩演繹的認可,換一個角度,也是對英烈們價值觀的敬仰。
“寓教于戲”,可能是這臺劇目的又一收獲。
三.個性獨特的人物
《血色秋風》塑造了一群鮮活的舞臺人物形象,解文柏更是獨具特點。他不同于阿慶嫂,不同于李玉和,更不是一些“神劇”里無所不能的“飛俠”。解文柏應該是無名烈士中的“這一個”。行內都知道,能夠塑造出“這一個”,整臺戲就成功了一半。而“這一個”常常又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難得。這就使我們相信,《血色秋風》之所以反應熱烈,用今天流行的話說,那就是“接地氣”,血肉豐滿,真實確信,因而才會引起觀眾的共鳴。
以點及面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和特定的時代背景,不斷“逼迫”解文柏做出相應的選擇,所以有了好看的劇情發展。解文柏的思想起點并不高,“四處作揖買路走”,為的只是求得小家的平安,他以生意人的玲瓏,貼切地表現了戰爭年代小人物無奈的生存狀態。但是,曾經死里逃生的經歷,促使他自覺不自覺地有了心理偏向,所以他不齒于同門師兄顧家駒的數典忘宗,因敬佩孫敬亭而不斷做出義舉。其動因是由衷的,最終的抉擇,是那么堅定,毫不矯情。觀眾的喝彩叫好,是最有力的的佐證。
這樣看來,《劇本》雜志多年前就發表了《血色秋風》文學本,應該是肯定了解文柏這個人物的獨特性。主演孟浩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演員,遇到這樣的角色,實在是一種幸運。”
當然,經過十幾稿的反復修改、排練,孫敬亭、呂云娟、儲二蘭等人物形象也都鮮活鮮明,各具色彩。
追求個性,一人一面。劇中人物隨著劇情的推進,各自都在行為走向上有著個性化的發展。孫敬亭的豪爽粗獷,卻也有著鐵漢柔情;呂云娟由羸弱無奈,到逼迫搏命殺賊;儲二蘭從膽小怕事,成長為抗敵戰士等等,均以可信的依據凸顯著人物的個性特征。即便對反面人物顧家駒的描述,也努力不去臉譜化,以人物的“前史”作為參照,外化人物的內心。總之,鮮活的人物形象,必須具有個性特點,而個性獨特的基礎是藝術真實的可信。
還是應了那句老話,文學是人學,戲曲也不例外。
四.精益求情的再創
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2015年7月份建組,9月初彩排、公演,幾乎是在不停的改進中完成的。
張建強導演認為,《血色秋風》在成功塑造人物的同時,其創意或許對今天的一些信仰缺失也提出了反思。所以,該劇不是一般的“應景”產物,應當可以做成一部舞臺藝術佳品力作。
沖著這樣的目標,首先對劇本逐字逐句反復推敲,繼而做了大量案頭,對舞美、作曲、造型及服、化、道等均提出要求。潛心竭力,摳人物、摳細節、摳調度、摳環節。孜孜以求“小制作”不失大氣的演出效果。
舉例為證,柳琴戲是一個地方劇種,很少演武戲。導演認為劇情需要,加入了武打設計,雖然份量不重,目前看起來還不算完美,但是,增加了觀賞性是毋庸置疑的。
整個創作團隊,不存在誰是“中心”之說。不斷有意見和建議,不斷磨合與提高。融洽的創作氛圍,一群忘我的“戲癡”。
唱腔設計孫柏樺先生和張曉霞女士,他們都是老前輩了,但是為了這個戲仍然甘愿付出心血。是那么謙虛地征求編、導、演的建議,公演后,甚至詢問觀眾,征求改進意見。
舞美設計也是先后數易其稿,具有特色的立柱設計簡潔明快,烘托劇情恰如其分。
燈光設計、造型設計、樂隊演奏乃至伴唱、合唱,方方面面都在給這個戲加分。
江蘇省柳琴劇院,老中青三代藝術家聯袂演繹。柳琴戲特有的高亢嘹亮的“拉魂腔”,在相當吻合劇情呈現的同時,以其獨特的魅力,引人入勝。值得一提的是,演員們排練、演出中一絲不茍的表現,令人尊敬。據了解,9月初在進劇場響排、彩排、錄像、公演的那幾個緊張的日子里,所有演職人員無不兢兢業業,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的“過戲”,而且熱情洋溢。正是因為精益求精的二度再創作,才有了現在精彩的舞臺呈現。這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江蘇省柳琴劇院的團隊精神。
劇院總經理韓梅女士說:“我們這個戲不能和別人比投入資金,但我們還是有底氣比一比劇場效應和社會效益。”
獨特的視角、獨特的人物、獨特的創意、獨特的呈現。大型原創柳琴戲《血色秋風》,收獲了應該的成功。或許還沒達到最理想的目標,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劇院表示,在接下來的演出中,還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不斷修改。已經獲得的普遍認可,再有南京調演的促進,相信會在精心打磨中日趨完善,帶給我們更多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