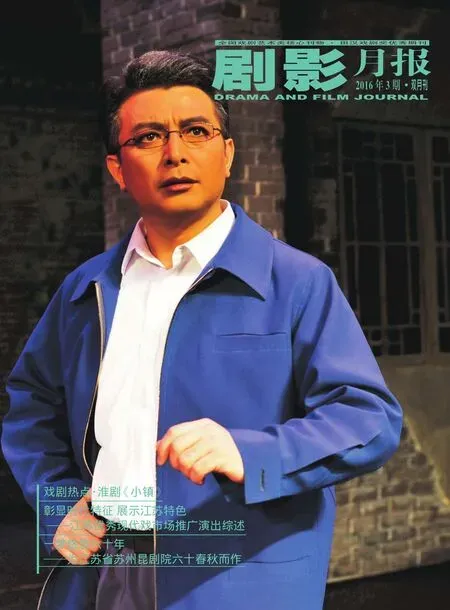聽曲新翻楊柳枝——淮劇《小鎮》簡評
■武丹丹 黎繼德
聽曲新翻楊柳枝——淮劇《小鎮》簡評
■武丹丹黎繼德
由徐新華編劇、江蘇省淮劇團演出的《小鎮》堪稱戲劇佳作。讀到這個劇本之初,筆者就說過:“我們的戲離世界名劇很遠,但這一部有可能比較近。”說《小鎮》離名劇比較近,首先是因為它取材的馬克·吐溫的中篇小說《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本身就是世界名著。這部小說,以精巧的構思、絕妙的故事、犀利的諷刺、天才的幽默、深刻的描寫,揭示了人類對金錢的欲望,撕開了偽善的華麗外衣,拉下了“世代光榮的最后一塊遮羞布”,戳穿了“誠實”、“清高”、“廉潔”的赫德萊堡(實際是人類社會象征)的假面具,將“請勿讓我們受誘惑”(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的謊言還原為“請讓我們受誘惑”(LEADUS INTO TEMPTATION),從而完成了一幅人類貪欲的肖像畫。為此,它成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中學和大學的教材。
毫無疑問,《小鎮》的創作受到了《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的深刻影響。作者曾坦言,《小鎮》就是受到了這部小說的強烈震撼,花費八年時間構思完成的。因此,如何認識《小鎮》的改編,如何認識兩部作品的異同,成為評價《小鎮》的關鍵。
客觀地說,這兩部作品都是“外鄉人”在“道德模范小鎮”尋找“恩人”,都采用了寫信的方式,都在信里透露出相當于接頭暗號證實身份的“那句話”,都有冒領了金幣或金錢的人,都有人(牧師或朱老爹)庇護冒領者(理查茲夫婦或朱文軒夫婦),都有主人公(理查茲或朱文軒)的內省和懺悔,從而搭建了作品的主要情節框架。可以說,從故事層面講,兩部作品確有相似乃至相同之處。
但是,改編作品的最大價值,不在于和原作有多少相同,而在于有多少不同,在于改編者或取材者能否點石成金、妙筆生花、為我所用、新意迭出。《哈姆雷特》和《奧賽羅》均有所本,但經過莎士比亞的“金手指”,就成了不朽的名著;川劇《金子》改編自話劇《原野》,但改編者為演員做戲,將主角仇虎“移位”于金子,就有了新的解讀和視角,帶給人們新的風貌。尤其是將外國名著改編為中國戲劇,更非易事。百余年來,從最早的話劇《黑奴吁天錄》到最近的兒童劇《小飛俠彼得·潘》,從較早的昆曲《血手記》、黃梅戲《無事生非》到最近的評劇《城邦恩仇》、豫劇《朱麗小姐》,依樣畫葫蘆者有之,換湯不換藥者有之,改頭換面者有之,脫胎換骨者亦有之,話劇的作品相對多,戲曲的作品相對少,成功的例子不算多,失敗的例子不算少。這種改編,最大的問題是容易邯鄲學步、食洋不化、盲目嫁接、非驢非馬,既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性,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趣味。這當然怪不得改編者,因為其中涉及到民族、歷史、文化、宗教、哲學、審美、藝術、生活等諸多問題。不過,這種改編,如能化洋為中、化古為今、打碎重鑄、鳳凰涅槃,也就與原創庶幾近之了。
《小鎮》的創作,走的就是這樣的路子,并相當成功地做到了以下幾方面的轉化。首先是社會、時代的轉化。社會和時代是決定一部作品氣質、風貌、走向、意味的根本因素。不同的社會和時代,必然賦予人們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表達方式,也一般地決定了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埃斯庫羅斯的戲劇只能產生在雅典奴隸民主制時期的古希臘,莎士比亞的戲劇只能產生在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元雜劇也只能產生在蒙古族統治下的封建主義時期的中國。《敗壞赫德萊堡的人》描寫的是19世紀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小鎮》描寫的是21世紀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兩者都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既有本質區別,也不可能互換。而且,對中國受眾來說,前者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總有這樣那樣的隔膜,而《小鎮》卻回到了自己生活的環境,那充滿著叫賣聲、生活氣息濃厚的天元鎮老街,是那樣地熟悉,那樣地親切。雖是取材或改編,他們卻相信故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活動在其中的人物也與自己有著同樣的生活、同樣的情感、同樣的觀念。不僅如此,即便都是“道德模范小鎮”,都有令人驕傲的光榮歷史,都有“首要公民”或模范人物,兩者也不可相提并論。這種社會和時代的轉化,必然對全劇的故事、人物、立意、表現產生重大的影響。
其次是文化的轉化。文化的轉化,是此類改編能否成功的關鍵。很多改編作品因為缺少文化土壤,在中國顯得水土不服。《小鎮》的文化轉化則非常自然。比如,《敗壞赫德萊堡的人》是外鄉人來報復,《小鎮》則是外鄉人來報恩,一字之差,天壤之別。這種動機的不同,不僅實現了中西方文化的轉化,也區別了兩部作品的文化風貌。從古希臘戲劇開始,“復仇”便是西方戲劇的常見主題,如古希臘的《美狄亞》、古羅馬的《腓尼基少女》、英國的《哈姆雷特》、法國的《費德拉》、瑞士的《貴婦還鄉》,而中國戲劇盡管也有許多“復仇”之作,如《趙貞女》《伍員吹簫》《趙氏孤兒》《竇娥冤》《臥薪嘗膽》《紅梅記》《原野》,但中華民族更認同“和為貴”的社會理想,更推崇“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為人之道。《小鎮》中外鄉人的報恩之舉,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此外,《小鎮》中不斷穿插的《三字經》和《弟子規》,力圖詮釋薪火相傳的中國傳統道德,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表現。
再次是主題的轉化。《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與《小鎮》的立意完全不同。前者是為了揭穿赫德萊堡的拜金主義本質和虛偽的道德面目,所以充滿了諷刺、幽默、調侃;后者則是表現了千年古鎮從假相到真相、從掩飾到公開、從舊道德到新道德的轉化與升華的過程,所以充滿了溫情、憐憫、贊許。這一點,在各自的兩位主要人物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的伯杰斯庇護理查茲,無非是出自一己之私,因為理查茲有恩于他;而理查茲臨終前的坦白,與其說是出自良心,不如說是出自恐懼,并且因恐懼而亡。赫德萊堡的最后一位“圣人”,最后也在恐懼中成為金錢和虛偽的犧牲品。正是在此,馬克·吐溫完成了對赫德萊堡的揭露和批判。《小鎮》的朱老爹庇護朱文軒,卻是為了維護小鎮的舊道德形象,一如他自己為這形象償還心債四十年。而且,他還希望朱文軒和自己一樣,將錯就錯,委曲求全,成為小鎮的新的衛道士。而朱文軒在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拒絕了朱老爹的提議,毅然決然地當著鎮內外所有人說出了真相,解剖了自己,摒棄了虛假,回歸了真實,在更高的層面上重建了小鎮新的真正的道德形象。于是,舊有的大鐘崩裂了,新的大鐘冉冉升起,敲響在人們的心里。如果說,《敗壞了赫得萊堡的人》在嬉笑怒罵、真相大白以后給人以悲哀的感覺,《小鎮》就在真相大白之后給人以積極向上的感覺,因為人們在道德的重建中不僅看到了人的本質力量,還看到了小鎮未來的希望。
最后是人物的轉化。《小鎮》里的人物,一不是叱咤風云的英雄,二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更不是什么“首要公民”,就是普普通通實實在在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老百姓。《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中除了死去的“恩人”古德遜,幾乎全無好人;《小鎮》不僅塑造了知恩圖報的“外鄉人”、純潔可愛的姚瑤、熱情助人的“快嘴王”等一系列正面人物,更塑造了勇于擔當、敢于“問責”、犧牲自己、成全小鎮道德形象的朱老爹,以及既表現出人性弱點、更顯示出人性光輝、經過痛苦的靈魂拷問和掙扎、最終鳳凰涅槃的朱文軒這樣一個有血有肉、富有變化、飽滿有力、發人深省的戲劇人物。這兩個人物,也許化自原小說的伯杰斯和理查茲,但已經做了根本的改造,是中國戲曲舞臺上少見的當代中國公民的典型形象。即便是其他冒領者,也以各種方式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懺悔。盡管全劇仍具有寓言的性質、象征的意味,卻傳達出對生活、對世界、對人生的巨大的善意,蘊涵著積極的意義。
由此可見,《小鎮》盡管取材于《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但已中國化、民族化、本土化,成為一部創造性的作品,不可與一般性的改編混為一談。
《小鎮》的價值,還在于它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戲,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達到了較高的美學層次。現代戲的本質特征是現代性。所謂現代性,并非僅指現代題材,關鍵是如何理解、處理現代題材,作品是否具有現代意識、現代思維、現代觀念、現代審美、現代表現。有的現代戲,題材是現代的,但意識、思想、觀念卻可能是陳舊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有的現代戲,故事是現實的、現代的,但價值取向卻可能是封建主義的甚至奴隸主義的;有的現代戲,人物是現在時的,但審美卻可能是過去時的。所有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現代戲,無非是“新瓶裝舊酒”罷了。
《小鎮》的現代性,主要表現在對人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精細描寫,對人的內心矛盾、糾結、掙扎、蛻變的真實刻畫,對新舊道德、真假道德交集、博弈、轉化的深刻透視上。它不像許多偽現代戲,只是演員穿著現代服裝在舞臺上演戲而已,充滿了概念,充斥著口號,要么就妥協,要么就躲閃,流于光滑,失之淺薄,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甚至打著傳統美德的旗號,傳遞腐朽觀念的信息,掛著英模人物的招牌,掀起造神運動的波瀾。《小鎮》這個戲寫了人,寫了人性,寫了人性的多樣多變多側面,更寫了人性的崇高——當眾撕下自己的面具,展示了“自我超越”這一人性中最崇高的品質,給人帶來審美的愉悅和震撼。這種崇高,也是《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中沒有的。設身處地問一問,面對唾手可得的500萬,所有人是否能心靜如水?是否能比朱文軒更不糾結?是否能戰勝內心的僥幸與貪婪?其實,重要的不在于人(包括模范人物)有無動搖、糾結、瑕疵、過失,而在于如何面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這才真實可信。而《小鎮》最后的自我救贖,就描繪了人面對自己內心時的掙扎和反復,凸顯了朱文軒的勇氣和決心,完成了劇中人物形象和小鎮道德形象。
除此而外,《小鎮》對淮劇也頗有意義。淮劇歷史悠久,表演內容簡單純樸,藝術詼諧風趣,生活氣息濃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同時也有編演現代戲的傳統。抗日戰爭以來,淮劇創演過上千出現代戲,可謂豐富多彩。但是,在諸多淮劇劇目中,更多是好玩的、好看的,注重情節的鋪排、感情的抒發,受眾的感受幾乎都是“春到溪頭薺菜花”,質樸、清新,也足夠家常,像《小鎮》這樣取材西方名著、彰顯人性的幾乎沒有。可以說,《小鎮》刷新了淮劇的內容、拓展了淮劇的題材。實踐證明,這樣的選擇可以有。淮劇這樣的劇種,固然可以演繹家長里短、愛恨情仇,可以演繹家國情懷、把臂同游,但更可以演繹靈魂過山車般的“心理抒情戲”,呈現出更大、更廣闊的氣象。《小鎮》這只“螃蟹”,味道好,分量足,必然會成為“新淮劇”的代表性作品。
江蘇作為戲劇大省,劇種眾多,人才輩出,舞劇、滑稽劇、話劇均有劇目獲得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的榮譽,但就戲曲而言,始終沒有一部代表江蘇劇種并稱雄于全國戲劇界的精品力作,因而也難以出現像越劇、豫劇、黃梅戲那樣跳出屬地演區,沖向全國,走向國際大舞臺的地方劇。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也對淮劇《小鎮》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