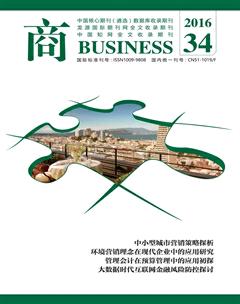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社會文化基礎
方光之
摘 要:當前中國正處于一個歷史的新階段,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各項矛盾與問題不斷,一些人由此出現道德淪陷、個人價值破滅等現象,沉迷于物質的快感中而不能自拔,不同程度的受到虛化價值觀的侵蝕。這在當前的社會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人民群眾精神狀態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發揮,因而本文力圖追溯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得以滋生文化起源,找到破解歷史虛無主義侵蝕的辦法。
關鍵詞:中國;傳播;虛無主義;社會文化基礎
一、虛無主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體現
(一)老莊哲學的虛無取向
作為道家學說的代表人物,“無為而治”是老莊哲學的思想核心。戰國時期,面對天下諸侯紛爭,百姓生活困苦的現實狀況,老子和莊子從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出發,對于人生現實,極盡否定與蔑視,“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老莊認為人應該擺脫現實生活的枷鎖,順應自然、順應本性,實現不受現實約束的自我解放狀態,可以說,這種消極無為的生活態度被中國后世的隱士們一直奉為圭臬,也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虛無主義的最初肇始之地。戰國時期,由于周禮的“退出”,一時間各種新的價值學說層出不窮,各個學派各執己見、爭論不休,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價值觀混亂的狀態之中,因此莊子懷疑客觀價值標準的存在,提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觀點,即如果相互對立的彼此都可以是是非標準的話,那么,整個社會就沒有統一的是非標準,也就是否認是非標準存在的客觀事實,大家的思想和行為都失去了客觀依據。這種看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主觀性的是非確實難以統一,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無序價值導向必定會使人們陷入思想的混亂中,在懷疑一切中否定一切,并最后衍生出價值虛無主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老莊這種消極避世思想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密不可分。戰國時期,諸國爭霸,統治者出于自身利益以及統治的需要,常常對百姓橫征暴斂,而作為社會底層的百姓在面對這些強加的“責任”時,往往毫無反抗之力,生活的困頓逼迫著他們只能轉而追求一種精神上的自由。老莊哲學的出現反映了時代的要求與特征,面對利益復雜的社會,虛無那些所謂的繁文縟節與“社會責任”,否定人生存在確切的是非善惡觀,轉而追求人生的灑脫本性。
(二)魏晉玄學的復興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后,儒學開始逐漸成為求取功名的工具,內容日漸趨于繁瑣,并且與老莊哲學相比,魏晉玄學產生的社會背景更加復雜,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人們面對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時,內心的疑慮與困苦更多,而舊有的經學教條已經失去了安撫人心的功用,魏晉玄學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條件下產生的學術思想,并逐漸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成為魏晉時期的主流哲學,它以《周易》、《老子》和《莊子》為基本經典,通過對本末、有無、動靜、言意、性情及名教與自然的“清談”論辨,來探索現象世界背后的本質,究極宇宙人生之理。“玄學者,所以宅心空虛,靜觀物化,融合佛老之說而成一高尚之哲理者也,”玄學這種以佛老之說為依托,探討形而上的學術,在繼承老莊哲學的基礎上,也自然而然的表現出價值虛無主義的特征。其中以王弼的《老子注》最為突出,“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于無也。”在《老子注》中,王弼宣揚一種“無”的思想,認為世界萬物有生有亡,從其產生開始,都是以“無”作為其存在的依據。
但是相對于老莊的消極避世主義而言,魏晉玄學不僅僅是追求玄之又玄的道德體系構建,更多的則是意圖通過對人性的思考,來批判現實境況。玄學認為只有率真、灑脫的人性才是這世間真正的自然名教,因此為了人的健康發展,必須擺脫束縛,回歸自然、回歸本性,“越名教而任自然”。
從以上可以看出,古代價值虛無主義流行,往往其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在社會面臨變革之時,舊有的價值體系遭遇破壞,社會矛盾與利益糾紛愈加復雜,人們在這種動蕩的環境中,生存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各種失望、不安、焦慮的情緒充斥著整個精神世界。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出于自保,往往會選擇一種消極反抗的避世態度來企求解脫。在否定過去的基礎上否定現實,并通過抨擊現實道德體系來打擊現實政治統治,從而表達出自己不滿的情緒。
二、“五四運動”中的歷史虛無主義隱患
從根本上說,歷史虛無主義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在五四時期,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誕生于“無政府主義”以及“全盤西化”論。
(一)無政府主義衍生出的新虛無主義思潮
五四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宣傳主要以朱謙之、易家鉞、杜冰坡、劉石心等人為代表,他們往往打著宣揚“社會主義”的旗號,向大眾灌輸歷史虛無主義,從而走上了一條根本有別于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在反對清王朝建立的腐敗政府的同時,卻否定建立列寧式的革命之統一政黨,否定階級斗爭在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國家是伴隨著社會歷史發展而產生的階級統治工具,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倡導的是,推翻舊有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統治,從而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并非無政府主義者所理解的拋開歷史的事實,建立一個無法律、無軍隊、無宗教的社會。無政府主義所提出的口號,這不僅脫離了當時的歷史現實,徹底否定了人類自古以來建立的文明成果,本質上更是對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破壞。而由無政府主義衍生出的新虛無主義,甚至提出推翻世界的宇宙革命論,認為世界萬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強權,主張廢除現世存在的一切萬物,一切制度,最終實現無人無物的最高境界,而這些都是符合虛無主義的極端主張。
(二)“全盤西化”理論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
近代以來,封建王朝的沒落使得中國在面對“船堅炮利”的西洋入侵者時,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局面,這種國力上的貧乏引發了人們對于民族自身的懷疑,認為中國事事不如西方,并進而引發了一種文化自卑感,特別是在新文化運動中,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高喊“科學”與“民主”的口號,提出中國學習西方不能僅僅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更應該從改善國民劣根性的角度出發,得出只有對自身文化進行徹底否定,才能更好的接受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西方的思維邏輯與價值觀念的結論。陳獨秀曾強烈表示:“祖宗之所遺留,圣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不可否認的是,“全盤西化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對中國的歷史發展以及文化的“吐故納新”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否真的應該將西方文化全部拿來照搬照抄呢?徹底的拋棄傳統,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的做法,必然要陷入歷史虛無的陷阱。
文化作為一種人們長期社會生活創造的產物,其本質也是一種社會歷史的沉淀物,“全盤西化”論的出現無疑是在特殊的語境下出現的一種悲劇心理,是在面臨民族危機時產生的一種對于本民族文化的抵觸心理。究其本質來說,”全盤西化”的理論出發點還是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企圖在現實的困境中找到一條救亡救國之路,只不過其理論弊端明顯,不能真正帶領中國上一條復興之路。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面對傳統文化,我們應該采取的是辯證否定的方法,既不能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不能對西方文化“照單全收”,對于文化遺產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的繼承,然后在實踐中推陳出新。而最后的實踐結果也證明,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人們才慢慢樹立了正確的文化觀,并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改變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命運,并最終實現了人民解放,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三)后現代主義文化語境下的歷史虛無主義
作為對“現代”一詞的繼承,“后現代”最早出現于1917年德國哲學家魯道爾夫·潘維茲的《歐洲文化的危機》一書,主要用來指代彌漫于20世紀西方文化中的虛無主義思潮。后現代主義反傳統,反理式、反本質、反規律,以至于最后反對它自己的傳統、理式。美國學者勞倫斯·卡胡恩在《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文集中對后現代主義的特征做了一個總結,就是批判在場、批判本原、批判統一、批判范式的超驗性,以及建構的“他者性”。而后現代主義的這種反叛的特性必定使它最終批判自己的傳統、理式、本質與規律,最后陷入一片虛無中,也注定了它不能長久的未來。而后現代主義被大量引入中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也開始加快了現代化的步伐,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價值權威也受到了挑戰。在當代的中國社會中,經濟理性的泛濫、物質主義的擴展以及娛樂至死的流行等等都使中國文化的陷入了危機之中。
1、經濟繁榮下的文化生態危機
隨著“發展就是硬道理”原則的確立,可以說改革開放后的這幾十年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騰飛的新時代,GDP的持續增長帶動了所有經濟領域的發展,但是中國的人文環境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在一場“數字”增長的狂歡過后,長期以來積累的體制、文化與生態矛盾問題終于陸續顯現出來。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在2012年發布的《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中清晰的指出,在中國目前迅速發展的外衣之下隱藏著一場巨大的社會危機:逐年擴大的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底層群眾不滿日益增加;官民沖突、社會犯罪現象加劇,社會成員安全感的缺失日益嚴重。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中國政府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是:在社會道德體系崩潰的現實下,政府還未能建立一個得到廣泛認同的主流價值觀;民主化進程緩慢,自由獨立的公民意識還未建立起來;官員腐敗、環境污染現象層出不窮等等,這一系列現實狀況讓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充滿著一種危機感,這主要表現出以高端知識分子和財富群體為代表的中產階層正在逐漸“退出”中國,而缺乏保障機制的低層“草根”卻由于自身經濟以及知識能力的貧乏,從而導致了他們內心不安焦躁的情緒,并且被“有心的”政治思潮以及利益集團所利用,正逐漸積累成憤怒,已經開始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和諧。
2、消費主義洪流下的大眾審美扭曲
消費主義最初在發達國家產生并流行起來,指的是人們把消費當做人生最高目的的一種價值觀。人們在消費主義的指引下,往往毫無節制的消耗物質與自然資源,而其在文化領域的表征就是在物欲和商業利益的驅動下,消費主義對于傳統文化秩序的消解,意圖打破傳統經典文化永恒性、藝術性的至高地位,從而將過去通常被認為是神圣永恒的一切進行不計后果的商品化以供人們進行消費。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與完善,中國社會的文化結構也隨之歷經一場深刻變革,而其中“去經典化”的文化傾向便是其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在現代化的都市王國中,市場經濟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一個質變領域。現代城市中隨處可見的巨幅廣告牌、奢華的購物中心以及爆炸式的媒體信息無一不在誘發著人們內心的物欲,大眾被不斷鼓勵去追求一種形而下的身體感官快樂,從而忽視了自身的精神追求。這種低俗的審美品格使我們同時喪失了藝術的內涵,人類文化的精神創新為高新技術的包裝所取代,人們不再追求文化的本質,轉而迷醉于外觀的光怪陸離,這種表征意識催生了一種對道德和理性的中立情態,使主體放無原則的放棄了價值判斷,認同于形象的標新立異。
參考文獻:
論文
[1] 《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虛無研究》閆世東
[2] 《魏晉玄學及其學術地位的確立-劉師培論魏晉玄學》李孝遷
[3] 《論王弼<老子注>思想之歸屬》劉季東
[4] 《五四時期“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之影響及其探討》周良書
[5] 《歷史虛無主義與文化種族主義》劉仰
書籍
[1] 《后現代文化景觀》陸揚
[2] 《文化正義—消費時代的文化生態與審美倫理研究》傅守祥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