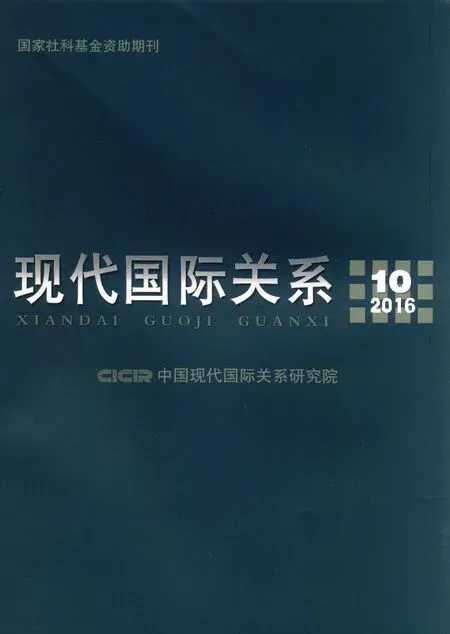構建中美核武器領域戰略穩定
吳日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新美國安全中心羅伯特·蓋茨高級研究員)
構建中美核武器領域戰略穩定
吳日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新美國安全中心羅伯特·蓋茨高級研究員)
中方觀點。中國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嚇阻核打擊或核強制。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2015年5月。中國建造核武器的決策起源并成型于1950年代被美國和1969年被蘇聯“核訛詐”的經歷。中國領導人相信由于核禁忌的存在,核武器的真實使用可能性不大。因此,核武器的政治使用,即核強制,是比核打擊更現實的威脅。④李彬:“中國核戰略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9期,第16~22頁。與這一核哲學相一致,中國一直維持獨特的核態勢,即“只用于核報復的解除戒備狀態的小規模核力量”。⑤Gregory Kulacki,“Chickens Talking with Ducks:The U.S.-Chinese Nuclear Dialogue”,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11_10/ U.S._Chinese_Nuclear_Dialogue.(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0日)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核威懾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美國導彈防御系統。導彈防御可能抵消中國的核報復能力。美國稱其本土導彈防御系統是用來防御朝鮮而不是中國的,但由于地理上鄰近,針對朝鮮的導彈防御系統天然具有針對中國戰略導彈的攔截能力。鑒于中國核武庫規模較小,假定美國發動先發制人打擊,即使一個小規模的導彈防御系統也具有抵消中國核威懾的潛力。一般認為,由于難以識別真實彈頭和誘餌,當前反導系統的效能有限。中國擔心的是反導能力不可預測的未來。美國盡管頻繁表示愿意就此跟中國討論,但一直拒絕接受有關導彈防御的任何限制。
在中國看來,中國與美國的核關系將導向兩種可能的結局。如果兩國都能夠限制其戰略力量的發展,那么美國的戰略導彈防御系統將保持小規模和低效能,同時中國的核武庫也保持較小規模。①Wu Riqiang,“China’s Anxiety About US Missile Defence:A Solution”,Survival,Vol.55,No.5,October–November 2013,pp.29-52.否則,世界將會看到一個大規模、高效能的美國反導系統與一個更大規模的中國核武庫針鋒相對。第一種結局符合兩國利益,但是其實現的可能性取決于中美互動與合作。目前,中美兩軍已開始就設立一個新的有關戰略穩定的對話展開接觸,這一對話必然會包括核關系。但光有戰略對話是不夠的。為了維持戰略穩定并避免軍備競賽,戰略進攻和防御能力的相互克制是關鍵。鑒于美國反復表態愿意對話但不接受任何限制,在核領域進行深度合作的前景看上去很黯淡。
美方觀點。美國長期以來視中國為其亞洲戰略的核心因素,開始是作為一個敵手,接著是抗衡蘇聯力量的砝碼,現在是地區和國際社會的關鍵角色。197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鼓勵、幫助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以期將中國納入現有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盡管仍然希望中國終將成為一個建設性的利益攸關方,美國及多數亞太國家都對中國軍事態勢和政策抱以深深的擔憂。因此,在過去十年里,美國執行了戰略對沖政策,一方面接觸中國以努力盤活有共識的領域,另一方面維持強大的能力來嚇阻、阻絕、并且在必要的時候擊敗中國。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力量的增長和態度漸趨強勢,美國開始重新評估對沖政策的可取性,其政策討論開始趨向傳統雙軌政策的制衡一端,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映了這一轉變。美國軍方領導人和相關專家認為,如果美國希望在西太平洋維持一個有利于己的常規平衡,應對中國的崛起,需要在高端軍事能力上進行大規模持續的投資。這一認知正在不斷轉化為具體的項目和部署。②Robert O.Work,“The Third U.S.Offset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tners and Allies”,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41/the-third-us-offset-strategy-andits-implications-for-partners-and-allies.(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0日)未來,中國的崛起很可能是美國的防務計劃、采辦和外交中的一個核心因素,如果不是決定性因素的話。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核政策有重要影響。鑒于蘇聯的崩潰、美國軍事能力的技術優勢以及意識形態對手的消失,在過去幾十年里常規力量是美國在東亞的防務計劃中和態勢上的主要焦點。③Elbridge Colby,“U.S.Nuclear Weapons Policy and Policymaking:The Asian Experience”,in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and NATO,ed.Tom Nichols et al.,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12,pp.75–105.當前核武器在美國亞太戰略中扮演著相對有限的角色,主要是用于嚇阻敵人的核打擊、應對極端情況以及對盟友提供保護,然而這些可能發生變化。決定核武器在美國亞太戰略態勢中重要性的核心因素是中國,更具體地說,就是中國對美國安全利益構成了多大的軍事挑戰。④Elbridge Colby,“Asia Goes Nuclear”,National Interest,January/February 2015;Paul Bracken,The Second Nuclear Age:Strategy,Danger,and the New Power Politic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2012,pp.189–213.如果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放慢或美國能夠維持可靠的針對中國的常規軍力優勢,美國核力量很有可能將繼續扮演相對沉默的角色。相反,如果地區常規軍事力量平衡變得對中國有利,那么核武器將很有可能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變得更重要。避免這種可能性,正是美國在其常規力量現代化上投入巨資的原因之一。
中美雙方已經達成諸多共識。盡管中國和美國的利益并不一致,但中美都將從以戰略穩定這一概念為基礎的中美戰略對話中受益。中美戰略穩定可以定義為雙方部署的核力量均可以:在第一次打擊中生存下來;令人信服地表明彼此當前和未來的能力都不能阻絕對方的戰略威懾。
從戰略穩定路徑出發,中國和美國能夠在以下方面達成一致:當前,核武器領域的中美關系是相對穩定的;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不是針對中國而設計的,亞太地區導彈防御是為了對付朝鮮的遠程彈道導彈和核武器項目;盡管如此,用來對付洲際系統的導彈防御具有削弱另一方第二次打擊能力的潛力,應當鼓勵一方向對方證明導彈防御不能威脅其第二次打擊能力;戰區導彈防御的部署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必然削弱戰略穩定,但這一系統的部件有威脅戰略導彈的潛力,或者可能被認為有這一潛力,雙方應努力區分其戰區防御系統和國家防御系統,應當鼓勵一方向對方證明戰區反導系統不具備對付遠程導彈的能力;朝鮮的導彈與核項目正在驅動美國亞太地區的國家導彈防御發展,圓滿解決這些問題是東北亞穩定的關鍵;中美間的常規沖突將導致嚴重的升級風險,重大常規沖突將導致核升級風險。因此,雙方應該努力確保各自的軍事計劃、能力、條令及態勢不致于鼓勵另一方的核升級。
建議中美可采取如下措施以提升戰略穩定:加強對話,以更好地理解雙方有關核武器角色和潛在使用、各自紅線和關鍵利益的認知、升級等的想法;對雙方的國家導彈防御設施、軍用反應堆、鈾濃縮和后處理設施進行互訪;相互通報導彈防御和高超音速武器發射試驗;互派觀察員參加導彈防御演習和試驗,探討分享攔截彈關機速度數據的可能性;美國邀請中國派遣觀察員參與在美國的美俄軍控核查;交流核查技術;討論彈道導彈核潛艇安全問題;對戰略穩定的概念進行共同定義;聯合研究關鍵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