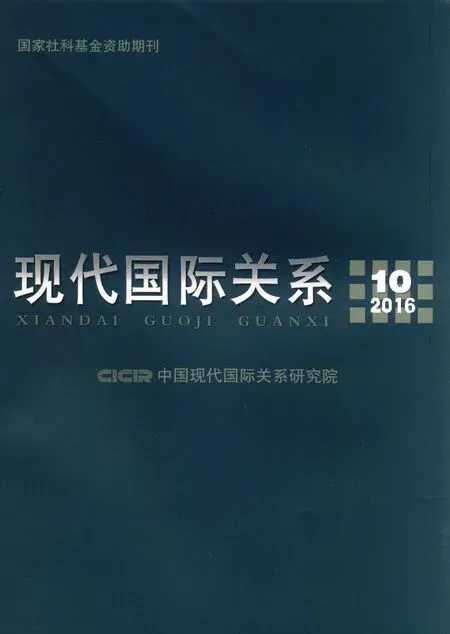發展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五大障礙
徐輝(國防大學教授)
發展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五大障礙
徐輝(國防大學教授)
2013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一致同意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后不久,兩軍達成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共識。2015年6月,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訪美期間首次提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核心內涵應該是“互信、合作、不沖突、可持續”。其中互信是前提,合作是目標,不沖突是底線,可持續是保障。具體地說,沒有互信就不會真誠合作;合作多了互信就會增強;有了互信與合作,才有可能不發生沖突,實現可持續發展。②“范長龍訪美首提中美新型軍事關系內涵”,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6-13/7341991.shtml(上網時間:2016年5月17日)
建立新型兩軍關系,既是中方的一種愿景,也是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需要。然而,就目前的兩軍關系現狀而言,距離這一愿景的實現尚有很大差距,其根本的障礙,來自美國某些舊有的觀念和政策選擇。
一是冷戰遏制思維。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雖然公開聲稱歡迎中國崛起,但實質上一直是執行在接觸中遏制的政策,美國對華“接觸加遏制”政策在美國國內有堅實的政治基礎③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11,pp.115-119.,美國甚至有學者指出,“美國對華政策并不是接觸與遏制,所謂的接觸只是另一種遏制的繼續”④Layne,Christopher:“A House of cards: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China”,World Policy Journal,Fall 1997,pp.77-95.。雖然美國政府一再強調中國不同于蘇聯、美國不尋求對華遏制政策,但在具體對華政策實踐中,仍有許多當年對蘇政策的影子。美國防部長卡特2016年5月23日在美國海軍軍官學校發表演講,多次提及中國,把美對華戰略態勢比喻成“宛如與蘇聯持續近50年的冷戰對峙”。①Ashton Carter,“Remarks at U.S.Naval Acedemy Commencement”,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83891/remarks-at-us-naval-academy-commencement.(上網時間:2016年10月8日)這種有“遏制”色彩的行為很難讓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相信美國真正歡迎中國的發展與強大。遏制思維的來源之一,是美中意識形態分歧。因為美國是反共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國家,從意識形態上很難容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穩固和崛起。②王緝思:“‘遏制’還是‘交往’”,《國際問題研究》,1996年第1期,第3頁。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法案限制中美軍事交流,阻撓中國與歐盟國家的軍事技術交流,堅持要在韓國部署薩的系統,都是這種冷戰遏制思維的體現。
二是美臺不正常的關系。按照國際法或國際慣例,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后,不應與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臺灣保持任何政治和軍事關系。然而,美國視臺灣為“不沉沒的航母”,對美國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一直憑借其強權實力,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同臺灣當局保持著不正常的軍政關系。這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嚴重威脅,并成為發展兩國、兩軍關系的最嚴重障礙。每當美國對臺出售武器或插手干預臺海事務,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時,都會嚴重損害中美兩軍關系發展,甚至造成危機。
三是軍事透明困境。“軍事透明”問題一直是困擾中美軍事關系發展的一個焦點。一方面,美國將軍事透明與建立開放的信息機制,加強軍事互信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與其心目中的對手的交往中,美國常常把軍事透明度作為謀取話語優勢,獲取軍事情報、向對手進行政治打壓、維護美國主導地位的一種手段和政策工具。其實,早在冷戰時期美國提出軍事透明政策之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12號文件》就為其設置了主基調,即將軍事透明作為工具而非目標③徐輝、韓曉峰:“美國軍事透明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外交評論》,2014年第2期,第80頁。。其目的是利用對手的“透明困境”(如果對手接受美國的透明標準,將使國家安全面臨威脅,如果拒絕,則被指責缺乏透明度),迫使對手在“透明”博弈中采取拒絕的方式,達成妖魔化對手的目的。從某種程度講,對蘇軍事透明政策是美國遏制戰略的重要一環,為贏得冷戰勝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④徐輝、韓曉峰:“美國軍事透明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外交評論》,2014年第2期,第83頁。有學者直接坦言,在推動建立信心措施名義下的軍事透明,已成為美國與其心目中的對手之間進行強權政治博弈的政策工具。⑤James J.Marquardt,Transparency and American Primacy in World Politics,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1,p.93.近年來,美國這種動機的“軍事透明”訴求,已經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惡化了中國周邊環境,成為中美“戰略互疑”的主要因素之一。⑥徐輝、韓曉峰:“美國軍事透明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外交評論》,2014年第2期,第89~90頁。
四是過度航行自由。長期以來,美軍為保持自身軍事行動的自由,一直以航行自由的名義派軍艦、飛機對中國沿海及周邊地區進行頻繁的抵近偵察和襲擾。2001年4月美軍EP-3偵察機對華實施抵近偵察,最后釀成撞機事件,嚴重影響了兩軍關系的正常發展。近年來,美軍加大了對中國南海島嶼的抵近偵察力度,2013年美軍考彭斯號巡洋艦和中國遼寧號航母在南海對峙;2015年11月美軍還派出B-52轟炸機飛臨中國南海島礁上空挑釁;2015年10月以來,美軍就已有美軍“拉森”號、“威爾伯”號和“勞倫斯”號導彈驅逐艦分別駛入南海中國島礁附近水域。據報道,美軍飛機對中國的抵近偵察一年可達500架次左右,且每次偵察留空時間相當長,超過10個小時。⑦“美軍機對中國偵察每年約500架次,每次留空超10小時”,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27/c1002-25545168.html.(上網時間:2016年5月15日)。有學者指出,美軍在南海用力過頭,過度的航行自由已構成對中國的羞辱,從而迫使中國加力反擊。從此,南海緊張局勢或步入螺旋上升,中美沖突可能性大增。這已危及東亞和平、穩定與發展。⑧薛力:“致奧巴馬的一封信”,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7611?full=y.(上網時間:2016年5月20日)。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兩國為防止海空意外,建立了一系列海空相遇的戰術技術規則。但不可否認的是,戰術技術規則雖然很重要,但只能解決戰術技術問題,而美國頻繁高調的海空抵近偵察行為,發送的卻是戰略信號,后果很嚴重。往輕里說,這讓對方感受到來自美國的敵意和威脅;往重里講,則很可能導致沖突和戰爭。冷戰結束以來的情況表明,美軍在全球擁有的前所未有的“航行自由”,帶來的未必是和平。
五是對盟友的過度承諾。奧巴馬總統曾明確表示,美國“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并做好準備,以確保美國及其地區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會受到負面影響。”①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43.美方在2012年6月的香格里拉對話上重申,要加強與美國傳統盟友的關系,強化在亞太的軍事部署②Leon Panetta,“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ld12-43d9/first-plenary-session-2749/leon-panetta-d67b.(上網時間:2016年5月12日)。。上述言論似乎表明,對盟友的承諾自動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采取軍事行動提供了“正當性”理由。然而,這種“正當性”并不意味著公道和正義,更不一定會帶來地區和平,因為美國的亞太同盟并未涵蓋所有地區國家,只保障同盟成員的安全利益。更何況美國這種承諾,經常表現為在爭端中不問是非地一味袒護盟國。例如,美國雖然多次表示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不持立場,但是在日本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時候,又多次重申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③“美國再確認釣魚島屬于美日安保條約適用范圍”,http:// 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406/c1011-24837748.html.(上網時間:2016年5月18日)。,這等于把美國對盟友的承諾建立在犧牲中國核心利益的基礎上,反過來又刺激了日本的野心,是進一步采取破壞地區穩定的行為。
作為負有重要責任的地區大國,中國怎么能接受美國對其盟友的這種過度承諾呢?所以,正如傅瑩大使所說,并非中國在挑戰美國對盟友的承諾,而是美國需要走出舊有的思維定式和習慣,需要克服現有的所謂“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的缺陷。④“傅瑩訪美后談感想:美國對中國存在深層的失望”,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616/19849474_all.html#page _2.(上網時間:2016年5月18日)為了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是美國該反思其對盟友的過度承諾對自身和地區安全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時候了。○
(責任編輯:王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