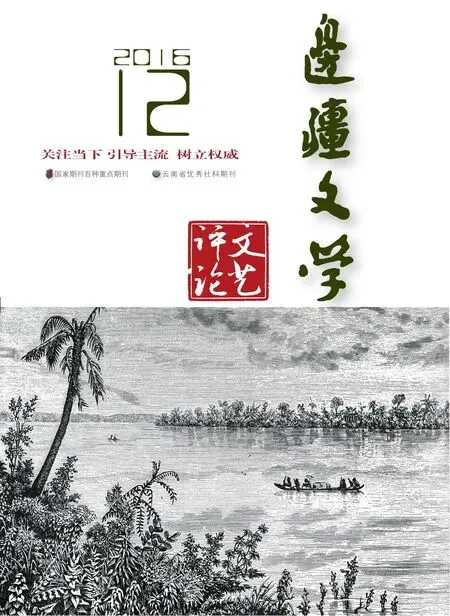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忘言書》未忘言
——談憶蘇《忘言書》的語言特色
◎茅 維
《忘言書》未忘言
——談憶蘇《忘言書》的語言特色
◎茅 維
《忘言書》是大理女作家憶蘇的又一部新作,它收錄了41篇散文,分三卷。《忘言書》擷取悄然變換的節氣、司空見慣的花草、潛入心底的親情作為創作素材,雖沒有縱橫捭闔的視野,也沒有汪洋恣肆的氣勢,卻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和溫情,把那些尋常事物描繪得充滿生機、溫婉動情。作家在創作中與節氣對話,和讀者分享天氣漸變帶來的無限驚喜;與花草對話,以多姿的形象、繽紛的色彩、夢幻的花香催促讀者步入戶外,親近自然;與親情對話,點燃讀者生活的激情,揣一顆感恩的心。《忘言書》能贏得讀者,除了作家在選材上的獨到視角,更與她藝術化的語言表達密切相關。
1.遣詞中顯形象
現代漢語中有些表具體事物的詞,這些詞“除了概念意義之外,還使人有某種生動具體的感覺,即所謂形象感。具有形象色彩的詞不限于形態方面,還可以包括動態、顏色、聲音等。”憶蘇在寫作中對那些具有形象色彩的詞情有獨鐘,總能信手拈來,刺激讀者的感官,把視覺、聽覺、嗅覺都調動起來參與到欣賞作品的活動之中,多角度增強了作品的可感知性,有效提高了閱讀的愉悅感。
在憶蘇的作品中,各種植物的色彩變化常常會給讀者帶來全新的感受。柳樹不知被古今作家寫過多少遍,憶蘇卻能另辟蹊徑,只寫柳條在節氣更替中的微小變化,“河岸上的柳條,在早春時節還只是綴著星星點點朦朧的淡綠,遠遠望去,如煙似霧的小芽在枝條上沉靜著、等待著,驚蟄一到,它們就急匆匆脫去鵝黃的小褂,換上翠綠的青衫。”(《驚蟄,夜臥早行》)這一語段用“淡綠”、“鵝黃”、“翠綠”三個表現顏色的詞,不僅把柳樹在早春與驚蟄之間的生長過程描寫得層次分明、循序漸進,同時也將季節的悄然變化映襯得合理有趣,把似乎看不見、摸不著的季節變化以可視的形式展現給讀者,達到了言此意彼的創作目的。在《初夏》中,作家不僅以各類植物的顏色同時還以外形、香氣入作,把初夏寫得姹紫嫣紅、生機勃勃、香氣四溢,令人向往。文中作家觀察到的梔子花花蕾“像一個豆莢,深綠,有凹凸不平的線條,好像誰用綠色的絲線捆扎過一樣。”開放以后卻是:“白,是那種瓷一樣的有質感的白色”,“花瓣之間,有個旋轉的空間和弧度,這讓單調的瓷白有了不一樣的韻致,讓這看似沉默的寡淡蒼白,有了一種動態的美感。”除了仔細描寫梔子花開前后的色彩由“深綠”到“瓷白”的變化,作家還將花開前后的形態變化進行了形象而精致的描述;不僅如此,作家還“沒有理由地想,梔子花那濃郁的氣息,大概就是花瓣之間那個旋轉的弧度,才擰出來的吧”,一個“擰”字,濃縮出了梔子花“香氣綿厚而濃美,有種歲月歷練而成的獨特味道”(《花香帖》)。這些文字,厘清了埋藏在讀者心靈深處對梔子花的模糊記憶,在會心一笑的同時獲得了美感。
憶蘇對大自然中各種蟲鳴鳥唱也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發現和記錄,她筆下的蟋蟀,雖然也有炎炎夏夜令人心煩意亂的鳴叫,但作家卻將觀察點放在室內與室外進行對比,用安靜平和的心態面對蟋蟀單調刺耳的鳴叫,升華出一場場好玩的游戲、一曲曲動聽的交響樂。“躲在屋內的蟋蟀,叫聲孤絕,卻自得其樂,旁若無人的獨奏,清脆高亢的歌聲顯得單調而激越,
聽久了,讓人心煩,耳朵也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所以每年的這幾日,家里總會來一場循聲而動和蟋蟀捉迷藏的游戲。”“而田野里的蟋蟀,總和叫聲渾厚的蛙們自發地組成一個樂隊,一起在夏日奏響一曲又一曲交響樂。隔著窗戶聽起來,樂隊里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盡職盡責熱愛音樂的歌者,此起彼伏的叫聲有高音,也有低音,有長音,也有短句。有時先有一聲雄渾悠長的蛙鳴,然后就接上一段齊奏,或是幾聲蟋蟀清脆的回環,讓整個合奏聽起來,音韻飽滿,層次分明。整個七月,便在這樣的合奏聲里入夢。”(《七月》)從視聽的角度來看,作家通過空間大小的轉換,聲音單調豐富的對比,把蟋蟀的鳴唱寫得具體生動而富于變化:狹小的室內空間配以“孤絕”的獨奏,突出了蟋蟀聲的單調乏味;而室外曠野中的蟋蟀聲,與曠野一般豐富遼闊,有高低音的配合,有清脆雄渾的應和,還有齊奏,充滿了立體感和層次感,這些聲音豐富多彩,富于變化,與室內刺耳的聲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把常人聽來無任何變化單調乏味的蟋蟀鳴叫聲與音樂聯系在一起,雖不算新穎,但作家借助對比的方式,增強了視聽的表現力,將死的文字變為流動的聽覺,激活了讀者的聯想力和想象力,極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藝術張力。
憶蘇在《忘言書》中除了對各種植物色彩變化的精心敘寫、蟲鳴鳥唱的形象展示,還十分注重將各種類型的花香入作,為讀者精心構建了一個個別樣的、令人心曠神怡的花香世界。《花香帖》較為集中地敘寫了多種類型的花香:薔薇的花香不濃烈,更不張揚,只是淡淡的一抹氣息,香氣淡雅而清香;含笑的香甜膩,溫柔,纏綿,花香里滿是豁達樂觀氣定神閑;梔子花的香,更像一個成熟的女子,香氣綿厚而濃美,有種歲月歷練而成的獨特味道;緬桂花的香氣散發著溫柔、嫻靜,安然與禪定,是最有見地的花兒;金銀花的香里,有種內斂的氣象,這香,開始是淡淡的,當你聞到后刻意去捕捉時,便有一股稍稍厚實的氣息自然襲來。在同一文中敘寫不同的花香,作者如果沒有深厚的生活基礎和語言功力,很容易將自己逼入絕境。憶蘇憑借著敏銳的洞察力和精確、感性的表達力,自信篤定,不經意間就隨手拈來比擬(薔薇不事張揚,含笑溫柔纏綿、緬桂花安然禪定)、比喻(梔子花像成熟的女子)、通感(含笑的甜膩)等修辭模式,不僅輕而易舉地將不同花香區別開來,更重要的是還賦予每一種花香以個性,增添了花香的靈性,讓讀者在品味花香的同時也將作者的真情沁入心底,化作揮之不去的記憶。《忘言書》中,還有清逸、飄渺、似中藥香氣的菖蒲,幽幽地、若游絲一般若有若無、淡香的水仙……這些,無不是作家長期精心觀察的積淀與細膩真情的再現。
2.引用中見知性
張乃光老師為《忘言書》作序時高度評價該作品“顯示了一個年輕的女性作家的知性”。所謂知性,大抵可以理解為一種內在文化涵養的自然外現。憶蘇在《忘言書》中的知性外現,不僅表現在她敏銳選材的眼光、細膩有趣的表達、不疾不徐的傳情、從容淡定的敘事方面,更表現在她旁征博引、信手拈來的用典能力上。
在《忘言書》中,憶蘇常引一些古典詩詞中的佳句入文,借典抒意,增強表達效果。《借水為名》開篇即以李漁《閑情偶寄》中“無此四花,是無命也”導入作家心儀的水仙花,接著引宋代詩人楊萬里之《水仙花》一詩點題,再以宋代詩人黃庭堅的傳世名句“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抒發作家酷愛水仙花的緣由,雖寥寥數語,卻事半功倍,激起了讀者的共鳴。在《白露為霜》一文中,作家引《詩經》“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之句,點名標題出處,把周而復始的“白露”節氣勾畫得清麗素美,意趣盎然。當作家面對洱海夜宿雙廊,在花下靜待洱海生明月之時,自然聯想到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那膾炙人口的詩句,清新自然,為讀者營造出具有古意和芬芳的意境,仿佛身臨其境而難以自拔(《一面湖水》),其飛揚的文采不言自明。
憶蘇引經據典,并不只以詩詞佳句入作,諺語、俗句同樣隨處可見。《小滿》用“立夏小滿正栽秧”、“秧奔小滿谷奔秋”的農諺,將小滿這一季節前后農民奔忙的日子概括得形象而生動。喜愛菖蒲,以諺語“菖蒲驅惡迎喜慶,艾葉避邪保平安”(《端午草》)為佐證,理由充分且不容分說。一句小城百姓的俗話“秋冬蘿卜小洋參”(《小寒之味》),濃縮了多少民間智慧!在《忘言書》中,如“大蒜是個寶,常吃生體好”、“寧可食無肉,不可食無豆”、“一天吃個棗,一生不知老”(《從一粒橄欖說起》)這樣的俗語比比皆是,顯示了作家處處留心的知性本色。
《忘言書》引用的范圍十分廣闊,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再到明清小說,直至現當代各類作品的佳句名段,均能為憶蘇所用。值得關注的是憶蘇作品中那些花花草草,她總是能從《黃帝內經》、《本草綱目》、
《滇南本草》、《千金方》找到這些花草的藥用價值。吃核桃“使人健壯,潤肌,黑須發”這是眾所周知的,而“樹皮主水痢。春季研皮汁洗頭,可黑發。將皮煎水,可染布。殼可治便血。”(《核桃樹的姿態》)這樣的功效卻少有人知,憶蘇在表達對核桃樹喜愛之情的同時,引《本草綱目》為讀者開闊了視野,獲得更多的食療知識。在《魚腥草與臭靈丹》一文中,通過《滇南本草》的記載,為百姓從理論上找到了臭靈丹藥用價值的依據;《從一粒橄欖說起》引一句孫思邈的“安身之本,必資于食”,把科學飲食的養生之道點撥得清楚有據。每每讀到這些,恍惚間會生出作家許是名醫者的錯覺。
除了引用修辭模式外,憶蘇在文中對各種花草、蔬菜瓜果的名稱簡介,也格外靈動有趣。作家接地氣的生活經歷和不放過每一個細節的文人氣質躍然紙上。金銀花與忍冬、雙花同屬一物(《金銀花》);魚腥草又叫折耳根、側耳根、九節蓮,臭靈丹還稱作獅子草、臭葉子、六棱菊、大黑藥(《魚腥草與臭靈丹》);旱金蓮的別名還有旱荷、寒荷、旱蓮花(《荷·旱金蓮·銅錢草》)。《忘言書》中的許多植物,學名文縐,別名形象,雅俗同章,收放自如,書卷與生活氤氳而生。恰切地引經據典,不僅能夠增強文章的說服力和感染力,也能啟迪讀者的心智,展示作家的深厚功力。憶蘇在創作中對引用修辭模式的使用總體上是十分嫻熟和自然的,但也存在極少篇目中引用稍顯過度,有些累贅,反而影響了引用修辭模式的點睛作用;也有極個別地方在使用引用時缺少過渡,顯得有些唐突生硬。盡管如此,但瑕不掩瑜,讀者仍然為憶蘇淵博而優雅的知性表達所折服。
3.變化中品節奏
憶蘇是一位用心來表達的作家,她非常清楚語言的節奏美會對讀者產生怎樣的影響,因此,她十分注重漢語音節的搭配,在她的散文中營造出強烈的節奏感,以和諧的音樂節奏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光陰記》是作家極投情的一篇作品,通過一幀幀照片,牽出了作家對至愛親情的美好回憶。文中每到用情之處,作家都十分重視音節勻稱整齊的選擇和搭配。“八月的玫瑰園。遠山,竹林。藍天。白云。花海里相依的母子。”作家以4個二二對稱的音節,構成了明快和諧的節奏,突出了悠遠而明澈的母子深情。“那時的他,多么年輕。神采奕奕,英姿勃發,眼神里滿是希望和憧憬。母親有一張照片最好,穿著花襯衫,半蹲著,長長的發辮,眼神清亮,笑意盈盈。那時,多好啊!”在以四音節為主構成的這一語段中,節奏平穩、舒緩、流暢,把對歲月流淌的無奈和滿懷的感恩表達得自然而傳神;“那時的父親,身材依舊挺拔。那時的天很藍,花正開,云很淡,風很輕。花叢中的一家人,心底,有一種情愫像花兒一樣綻放——那情愫,叫幸福。”在這三音節為主的語段中陡增了語音的急促性,節奏感鮮明強烈,幸福美好的童年時光頓時溢滿心間。
憶蘇的散文語言充滿了節奏感,但這種節奏感并非一成不變,她深知單調沉悶的語言會使人失去閱讀的耐心,會使她的散文喪失生命力。因此,憶蘇在創作中十分注重經營其語言的個性。就語言節奏而言,她不僅使用單一的節奏道出自己的情感,更在意語言節奏的變化與情緒變化的協調一致,因為,“文學語言是飽含情感的,語言節奏的聲音組合必然要受情緒的影響,體現著人的情感變化。”在富于變化的節奏中,憶蘇在宣泄情感的同時總能給讀者帶來怡然自得的審美享受。如“是啊,春來了,大地上所有的草木,都在欣然相愛,與風,與水,與陽光,與泥土,與世間的一切……”(《立春》),作家用二二、三三的音節對稱形式,讀起來清脆響亮,和順悅耳,同時,也把盼春、喜春、愛春的急切心情在快慢變化的節奏中展示出來。再如“樹干斑駁,樹皮滄桑,卻一點也不影響它一到春天就按時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家常的石榴》)把較為舒緩的四四音節對稱節奏安排在句首,以抒發作家對陪伴自己成長的石榴樹飽經滄桑的感慨和無限敬意;而以二二二二節奏收尾,字數由多到少,節奏由慢變快,表達了作家對老樹不老、仍可勃發青春充滿了熱切的期待;值得回味的是在二二二二相對的節奏中,作家沒有使用頓號,而是將“發芽、長葉、開花、結果”的植物自然生長過程以逗號做間隔,在增加停頓時間長度的同時,也增強了語言的鏗鏘感,更將石榴的成長過程定格在一個個畫面中,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懷想空間和無盡的回味。
《忘言書》中,作家在散文語言的創造上傾心盡力、苦心追求,形成了獨具氣質的語言風格。
(作者單位:大理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