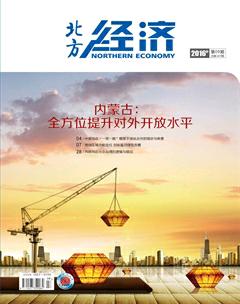內蒙古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就業特點和制約因素
張鑫
農牧民轉移就業作為“五個一批”脫貧攻堅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十三五”時期開展精準扶貧、實現全面脫貧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據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調查數據推算,2015年,內蒙古31個國家扶貧重點縣中,約有115萬農牧民工,占全區242萬農牧民工的47.5%。轉移就業總體狀況良好,但仍需在多方面加強引導和支持。
一、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就業特點
(一)外出多,本地少
通常,按農牧民工就業的地域以戶口所在鄉鎮為界,轉移到本鄉鎮以外就業的,叫外出農牧民工;在本鄉鎮內進行了非農轉移就業的,叫本地農牧民工。
調查顯示,國貧地區115萬農牧民工中,外出(本鄉鎮以外)人數達93萬人,占80.9%,比全區農牧民工外出占比高10.7個百分點。其中,約有62萬人在自治區內流動,占54%,比全區區內流動比例低約1個百分點;有31萬人跨省區流動,占27%,比全區跨省區流動比例高11.7個百分點,國貧地區的跨省區流動農牧民工占全區跨省區流動農牧民工總量的比重超過八成。
本地(本鄉鎮內)農牧民工人數約為22萬人,占19.1%,比全區本地農牧民工占比低10.7個百分點。其中,非農務工13萬人,占11.3%,比全區本地非農務工占比低8.1個百分點;非農自主創業(包括注冊企業、個體戶和小攤小販)9萬人,占7.8%,比全區本地非農自主創業占比低2.6個百分點。
(二)更多流向地級以上大中城市
從外出地域看,31個國貧地區外出農牧民工主要向地級以上大中城市集中,比例超過7成,比全區外出農牧民工流向地級以上城市比例高12.7個百分點。其中,流向直轄市、省會城市和盟市所在地城市的比例分別為16.2%、20.1%和34.3%,比全區高5.2、0.3和7.2個百分點。而流向旗縣所在地的占25%,低于全區12.7個百分點。可見,大中城市對國貧地區農村牧區勞動力更具吸引力。
(三)就業選擇更傾向于勞動密集型行業
從產業分布看,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與全區農牧民工分布格局相同,在三產的就業比重達到68.9%,但仍比全區均值低3.9個百分點;而在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達到30.9%,比全區平均高4.1個百分點。從具體行業看,居民修理及服務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制造業和住宿餐飲業等五大行業從業占比較高,分別占23.6%、16.9%、16.4%、7.9%和7.9%,合計超過七成。從行業分布與全區水平比較看,居民修理及服務業、住宿餐飲業和交運倉儲業,由于對專業技能要求較高,從業比重較全區農牧民工平均水平分別低2.2、3.3和4.6個百分點;而建筑業、批發零售業和采礦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由于技能要求較低,從業比重比全區農牧民工分別高2.3、2.4和1.7個百分點。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就業層次比全區農牧民工明顯偏低。
(四)從業收入略高于全區平均水平
2015年國貧地區農牧民工人均月收入為3253元,比同期全區平均水平高0.7%,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9%。其中,外出農牧民工人均月收入為3201元,比全區水平略低1.4%,主要受知識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多從事收入水平較低的簡單勞動所致,但遠比回家鄉務農收入要高;本地農牧民工的人均月收入為3295元,比全區水平高2.2%,這與“十個全覆蓋”項目向貧困地區傾斜有直接關系。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前提下,國貧地區農牧民工的收入仍能保持高于全國農牧民工平均水平實屬不易。
二、制約貧困地區農牧民轉移脫貧的主要因素
(一)滯后的縣域經濟限制了農牧民就近轉移就業
從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就業地域構成看,在縣域內就業(包括鄉內、鄉外縣內)的占64.3%,比全區農牧民工平均水平低9.3個百分點;而到縣外區內和區外就業的占35.4%,比全區農牧民工平均水平高9.3個百分點。在“十個全覆蓋”工程項目向貧困地區傾斜的大環境下,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在本旗縣范圍內就業的比例仍然明顯低于全區平均水平,凸顯出其縣域經濟、小城鎮和鄉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的滯后,同時也證明了靠短期的項目刺激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貧地區農牧民長期、穩定轉移就業的問題。
(二)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偏低影響轉移就業的層次
從轉移就業所從事的行業可以看出,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從事簡單勞動的就業比例高于全區水平,在需要一定技能、專業技術的行業就業比例則明顯偏低;這表明國貧地區農牧民在技術和知識方面相對欠缺。調查顯示,在全區范圍內,已有39.1%的農牧民工學歷達到高中及以上,而國貧地區高中及以上學歷的農牧民工僅有34.4%,低4.7個百分點;國貧地區接受技能培訓的農民工比例雖然比全區農牧民工平均水平略高1個百分點左右,但整體水平仍然偏低,接受農業技能培訓的不足1成,接受非農技能培訓的也不足4成。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上的差距不僅造成就業能力的欠缺,也影響著擇業方向的選擇和就業層次的提升。
(三)勞動保障不足,埋下返貧隱患
調查顯示,有55.2%的國貧地區農牧民工沒有與單位或雇主簽訂勞動合同,一旦遇到勞動糾紛,很難通過法律手段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同時,沒有參加任何養老保險的國貧地區農牧民工占比高達44.4%,比全區農牧民工平均水平高5.1個百分點。隨著年齡的增大,這些人會因喪失勞動能力而缺少生活來源,如果再沒有了養老保險的保障,他們返貧的風險將大幅增加。
(四)教育狀況堪憂,埋下貧困代際傳遞隱患
由于國貧地區學校數量少、距離遠,大量學生從初中甚至小學開始就需要住校,產生了較多的食宿交通費用。2015年,國貧地區上小學或初中的農牧民子女食宿交通費用為人均3071元,比全區平均水平高5.6%;上普通高中或以上的為人均4998元,比全區平均水平高2.7%;上中等職業學校的為人均4375元,比全區平均水平高18.1%。較高的就學成本給家庭帶來明顯的經濟壓力,使輟學和因學返貧的現象時有發生。數據顯示,在國貧地區12-15歲的農牧民子女中有13.7%的人沒有上學,比全區平均水平高7.7個百分點;而15-18歲的子女中有50%的人沒有上學。這表明國貧地區有超過一成的孩子連初中都沒有讀完就不再上學,有一半的適齡青少年只讀完初中就終止了學業。基礎教育的缺失埋下了貧困代際傳遞的隱患。
三、促進國貧地區農牧民轉移就業健康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強化重點扶持,提升轉移就業率,促就業穩增長
貧困地區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找準著力點,因地制宜,挖掘內蒙古特有的地形地貌、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等旅游資源,促進“草原游”、“沙漠游”、“冰雪游”、“民族風情游”等旅游項目發展;運用互聯網思維,嘗試“眾酬”、“網上種地”、“網上養殖”等多種模式,開發特色扶貧項目,為國貧地區農牧民在當地就近轉移就業創造更多機會,降低轉移就業成本,提高脫貧效率。政策層面,可以出臺一些用工激勵措施,借鑒過去鼓勵招收下崗職工政策,對凡招收農村牧區貧困家庭成員的私營企業和單位,通過給予一定稅費優惠等方式,有針對性地強化重點扶持;新開發的扶貧項目,在落地時應重點向貧困戶傾斜,可以由家庭單獨經營的項目要首先考慮貧困家庭,需要用工的較大項目用人時要優先聘用貧困家庭的勞動力。
(二)既“扶志”也“扶智”,促進精神脫貧
“精神脫貧”是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扶貧思想的戰略重點。精神上有力量,實踐中才有力量。在精神扶貧方面,第一應該“扶志”,第二應該“扶智”。在“扶志”方面,地方政府應組織當地成功脫貧致富的典型人物,開展示范講座,介紹勤勞致富的經驗,激勵帶動貧困戶,使其有信心、有勇氣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擺脫貧困。在“扶智”方面,發展教育是根本之舉。應從基礎教育抓起,提升整個貧困地區的文化水平。地方政府可以試行12年義務教育,完善各學習階段的獎助學金制度,建立專項教育基金精準幫扶就學困難的貧困家庭子女,尤其應在食宿及交通費用方面給予一定的補貼,預防因基礎教育缺失而造成的貧困代際傳遞現象發生。
(三)增加資金供給,做到公開透明
一方面應在財稅、金融方面想方設法進一步增加扶貧資金供給,擴大扶貧貸款使用范圍,簡化貸款流程,緩解國貧地區農牧民的資金壓力,提高他們自主創業的信心和能力。另一方面應堅決打擊隨意擠占、挪用扶貧款項行為,加強監督;有針對性地使用好扶貧資金,避免扶貧款“人人有份、人人不足”;公示精準扶貧建檔立卡戶、低保戶評定標準及流程,做到評定過程公開、透明、可追溯。
(四)簽合同,降費率,規避返貧風險
一方面,政府應嚴格規范勞動用工管理,嚴厲打擊不與農牧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行為;繼續加大新聞媒體的宣傳引導和輿論監督作用,大力宣傳勞動法律法規,提高農牧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權益的意識,從源頭保障農牧民工通過勞動脫貧致富的權利。另一方面,國貧地區農牧民工養老保險參保比例之所以低,既有客觀上繳不起費的原因,也有主觀上不愿意繳費的情況存在。可以借鑒強制車險的做法,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提高貧困地區養老保險參保率;同時,結合當地的財政轉移支付能力,在貧困地區適度降低養老保險的繳費比率,減輕繳費負擔,同時適度甚至優先提高貧困地區養老保險支付額度,調動繳費積極性,保障其在喪失勞動能力后的生活來源,規避返貧風險。
(作者單位: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
責任編輯:代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