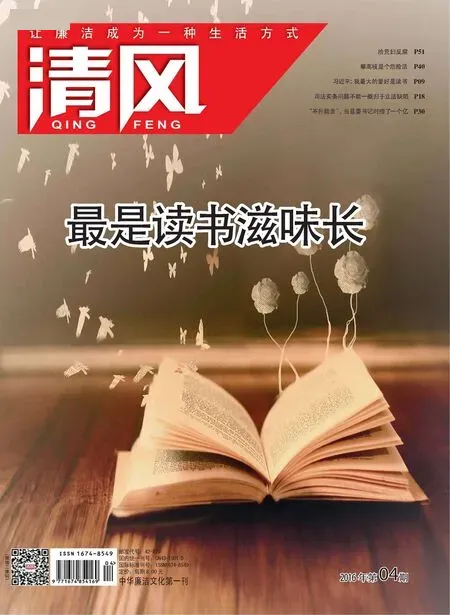清正廉潔的王騭
文_李雨客
清正廉潔的王騭
文_李雨客
康熙親政之時,清王朝立國不到30年,在他的心目中,漢臣們大多都是“燙手的山芋”,能“任事”卻未必“實心”。而有一位卻是個例外,他不是“燙手的山芋”,而是“香餑餑”。這個人,就是被清史學家們譽為“大清第一清廉之臣”的王騭。
為了百姓顧不了皇帝
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太和殿被大火焚毀后的第6年,康熙帝決定重修太和殿。這年的九月,工部議定從四川采集2663根高大楠木用于大殿維修。這個時候,王騭恰好在京城逗留,為赴任直隸口北道臺做準備。本來,四川采木的事情跟他沒有關系,可是在此之前王騭曾在四川做過地方官,對四川的情況很了解。他深知,假如工部議定的四川采木的計劃被批準,那么,四川民眾必然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會有許多民工死在采木這件事上。同時,他也知道,重修太和殿是康熙心中的一件大事,勸諫皇上否決工部的計劃,實際上是跟皇上唱對臺戲,弄不好會引起皇上的反感,對自己不利。
一邊是民眾,一邊是皇上;一邊是民眾的生命攸關,一邊是皇上的內心關切。怎么辦?怎么取舍?王騭思前想后,最后決定,不管皇上會有怎樣的反應,必須為民請命。
王騭主意已定,便寫了一分奏疏呈給皇上。王騭在疏上說:四川高大的楠木,只有在深山幽谷中才有。民夫們到峻山窮壑中采伐這樣的楠木是十分危險的。而且,就算是費盡千難萬險采伐到了,要把那樣高大的木料從大山里運送出來,也絕非易事。此外,從深山幽谷中采伐運送高大的楠木,完成這項工作須得好幾個月的功夫。這些年來,四川境內兵連禍接,荒煙百里,滿目瘡痍。全省戶口中,能做工的不過18000余人。這個數字趕不上其他省份的一縣之眾。如果再從中抽撥5000人入山采木,那么,這個省的農田耕作就全廢了。
這份奏疏呈上去以后,圣意難料,所以,王騭也是忐忑不安。好在康熙帝不愧為一代明君,向來以民福為重。他看了奏疏之后,深感王騭所言入情入理,就對工部官員說:“四川屢經兵火,困苦已極。采木累民,塞外松木,取充殿材,足支數百年,何必楠木?”他下令工部,停止從四川采集楠木的計劃,改用塞外的松木作為維修太和殿的材料。
因為王騭的犯險上疏,四川民眾得以避免入山采木的艱辛,避免了為入山采木可能付出的生命代價。
時隔不久,直隸保安州出了一樁公案。保安州有一個叫衡有林的人,此人是當地的一霸,且跟官府的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時,他跟宣府鎮的百姓之間發生了土地之爭。案情復雜,且牽扯到的百姓眾多,民情洶洶。
地方衙門把案子具呈給了內務府,內務府以“奸民盜種”報部轉奏。就是說,“內務府”認為案子牽扯到的那些老百姓屬于“奸民”,是不良百姓,而這些“奸民”在不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偷種莊稼,因而才引出了此案。皇上得知這個案子以后,派員前往查案。王騭此時已是當地的道臺,所以,他帶領同知、守備等當地官員會同朝廷派出的大員一起查案。
在這個過程中,王騭公正無私、不偏不依,將案子的真相查了個一清二楚。最后判定,涉案的二十余頃土地,屬馬端麟等八百余戶百姓所有。衡有林屬于謀奪他人資產,以謀奪他人資產罪以律論處。同時,王騭沒有放過跟案子有關的那些徇私舞弊的貪官污吏,按律將他們嚴加懲處。案子塵埃落定,百姓們怨意盡除,當地社會安定下來。
一個月治好一省的“貪腐病”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王騭要去江西主政,臨行前,“陛辭請訓”,就是臨走之前去跟皇上道個別,同時看看皇上還有沒有什么要囑咐的事項。由于前任江西巡撫是因為貪污腐敗而被革職查辦,所以,康熙帝對江西官場的現狀很清楚,他知道江西那個地方官場腐敗的程度已經十分嚴重,新任巡撫如果不能潔身自好、大膽作為,搞不好就有被當地腐敗官員拉下水的可能。于是,康熙帝對即將赴任的王騭叮囑再三。王騭說:“請皇上放心!臣到任之后,定當嚴厲禁止攤派,以防害民,定當整治司法不公等問題,定當竭力祛除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等時弊,以不負皇上所托。”
此前,王騭在四川做官的時候,“不食民間粒米,不取民間束草”。他家里只有三位傭人,而且,“于家中取給盤費”——就是自掏腰包發傭人們工資,而不是拿宮中的錢發給傭人工資。有時家里的錢不夠用了,就問同僚們去借。這些情況康熙早就有所了解,知道王騭是一位清廉自律之臣,所以,對于王騭臨去江西赴任的一番說辭,康熙帝是很相信的。因此,他一反常例,額外賞賜1000兩白銀給王騭做盤纏,另外,還賞了一套鞍馬。
康熙帝的這個舉動,顯然有著極其深刻的用意。王騭是個聰明人,皇上的用意他當然可以悟出來,無非就是讓他到江西之后,放開手腳大膽做事,讓他像戰馬一樣勇敢無畏,是期望他作為江西的一把手要把江西的事情辦好。當然,皇上的這番苦心,也同時反證了王騭將要直面的江西局勢將是很不一般的,將是很復雜的。
王騭初到江西,屬下各府衙官僚紛紛前來饋贈財貨器物,他一概拒收。按今天的眼光看,王騭拒絕收受下屬們送上門來的禮品財貨,實在是很尋常的一個做法,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一個新任巡撫到任后拒收下屬官僚的一切饋贈,那可是一種很不一般的做法。那其實是一個警告,那是在告訴他的屬僚們:你們可得注意了,我可不同于你們的前任,我可要向各種形式的行賄受賄行為開刀了。而江西的那些官員們也不傻,通過王騭拒絕收受下屬們的饋贈,以及后來王騭對政策的一系列調整,他們敏銳地覺察到這位新來的巡撫不同尋常,他們意識到再像從前那樣行賄受賄求取私利是不行了,必須老老實實地做官。如此一來,“貪黷科斂”之風在江西很快得到了遏制。
王騭主政之前,江西的攤派之風盛行,司、道、府各衙門的平常運作耗費,甚至連官差押解犯人的費運,都攤派給了老百姓,百姓負擔過重,苦不堪言。針對這種情況,王騭發布政令“自巡撫衙門起,去舊更新,官役上下大小雜費盡革,有犯必懲”。就是說,不論哪一級官府,上自主政官員,下到跟班雜役,除了按照規定領取薪水以處,統統不準再分發額外的補貼,違犯這一規定的人,將受到嚴懲。政令一下,各府衙沒有借口再向民間攤派,老百姓的負擔減輕了不少。
有些府、縣,稅糧征收被一些惡棍把持,使老姓吃虧不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得知這一情況后,王騭下令糾正。他命令各府、縣在規定的時間內,把違規多收的稅糧返還給百姓。
史書記載,王騭“履任未及一月,力行數事,積弊搜剔無遺”。就是說,王騭上任巡撫之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辦了好多大事,江西省多年累積起來的弊端全都被剔除了。
不賜金銀只賜衣帽
王騭的廉潔操守和任事能力在他主政江西短短的時間內,就再一次得到了證明。康熙帝決定進一步重用他,“擢閩浙總督”。
康熙帝之所以讓王騭出任閩浙總督,那是有明確目的的。當時,福建沿海很不安寧。原因是海盜猖獗。那些海盜假扮成漁民,隨漁民一同出海,等到了海上,遠離陸地之后,他們便原形畢露,對漁民大肆劫掠。漁民們得不到安寧。康熙派王騭去沿海任閩浙總督,意在讓這位“能臣”解決海盜害民的問題,以便安定海疆。
王騭到沿海之后,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海盜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官兵拿他們沒有辦法;而官兵拿他們沒有辦法,是因為一個“定例”。定例規定“兵船離汛不得遠洋”,就是說,在某一段時間里,兵船是不可以下海遠洋的。兵船不準下海,自然就無法追擊在大海上活動的海盜,海盜猖獗也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打破一個定例,是需要勇氣的。尤其是作為一名漢臣,要打破來自朝廷的一項定例,極有可能招致非議。事實上,前任總督以及其屬下的數位總兵之所以沒能對海盜展開攻勢,正是由于他們沒有膽量去打破定例。可王騭呢,他恰好是個有勇氣有膽量的漢臣。他以安民為要,決定打破陳規戒律。他下令屬下幾位總兵,駕船出洋對付海盜,同時,又派出人馬沿海岸搜索隱藏起來的海盜船只。結果,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捕獲海盜船大小八只,斬殺、擒獲海盜多人。“海疆一時無警”。
王騭在閩浙任上,獲得了百姓的認可和稱贊。康熙帝南巡之時,遍察輿情,得知王騭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賜予他御衣、涼帽。
為何只賜御衣、涼帽?一方面,王騭這個人不貪財貨,一心為公,勤政愛民;另一方面,南方氣候炎熱。所以,康熙帝賜王騭“御衣和涼冒”,而不是黃金或白銀。這樣的一份賞賜,充分體現出康熙帝對王騭為人的熟知程度,以及對王騭這位漢臣發自內心的那份關懷。作為一位漢臣,在當時想得到來自皇上的真心關懷,常常只是一種奢望。而王騭卻真真實地得到了。
康熙南巡之后不久,王騭便被調回京城,成為戶部尚書。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做到年近八旬,期間頗有些讓人稱頌的事跡。比如,他辦事一絲不茍;比如,他拒受商賈行賄等等。
史書記載,王騭活了82歲,死后,康熙帝下旨“賜祭葬如例”。就是說,對王騭的祭典儀式和葬禮,康熙帝親自過問,下旨命相關部門按照定例進行安排。可見,王騭非但在活著的時候能獲皇上關愛,在死了之后仍獲哀榮。
王騭早已死去了幾百年了,那么,在幾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重溫王騭的故事,又能得到哪些啟示呢?
不妨用康熙南巡時對王騭說過的那句話作為回答:“爾任總督,實心任事,浙、閩黎庶俱稱爾清廉,故特加優賚。”其實,不論哪個時代,作為官員,必須做到“實心任事”和“清正廉潔”這兩條,他才能成為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才可能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