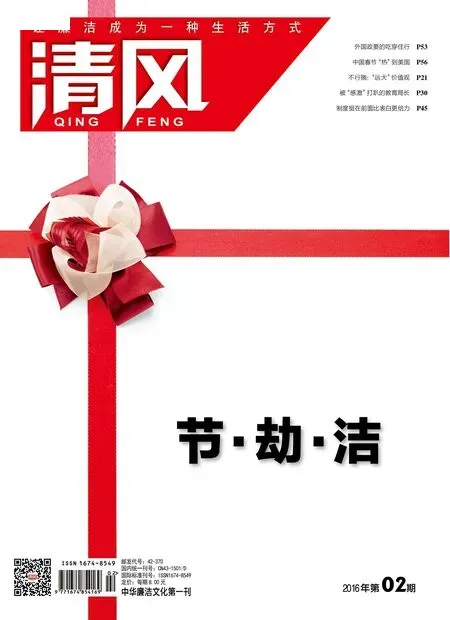『節禮競賽』何時休
文_林永芳
『節禮競賽』何時休
文_林永芳
其實,我本來想說“該怎樣體面地結束這場‘節禮牌軍備競賽’”。可又不想用太長的標題去挑戰讀者諸君的容忍度,只好簡化。言歸正傳,話說每年中秋,常見報道稱京城因送月餅者云集而導致交通堵塞。人們大驚小怪,仿佛見到“人咬狗”似的,殊不知此情此景其實古已有之。明朝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就記載,除夕前他外出訪客,見中城兵馬司衙前浩浩蕩蕩擠著一群手捧食盒的人,竟使道路堵塞。詢問才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明白了吧,送禮導致交通堵塞,這類事古今皆有。
根據《明史·職官志》,中城兵馬司不過是古代版的公安、城管,其送禮者竟能多到“食盒塞道,至不得行”,官階更高者該是怎樣門庭若市?“送禮風”之盛,可見一斑。
其實,送禮這事兒也不是一開始就如此繁榮興旺的。起初,也許只是個別聰明人為了在有限生存資源的競爭中搶占先機而把主攻目標鎖定在手握資源配置權的人物身上,尋找出一個“系統漏洞”:投其所好、用禮物開道。可別人也不傻,很快就群起效尤,競相加碼。久而久之,上司們的胃口被撐得越來越大,越來越習以為常,以致“誰送了我不知道,但誰沒送我卻記得”。于是,每到年節,便上演一幕幕“節禮牌”大戲,其情形有點像“軍備競賽”——當你以為送幾盒土特產便可攻下要塞時,別人早已開發出現金紅包、購物卡了;當你學會用購物卡、銀行卡來裝備自家禮盒時,人家早已動用房子車子之類的“氫彈”了。于是,送禮的技術細節成了不傳之秘,“送禮史”進入了“惡性軍備競賽”的泥潭階段。
在清朝,通行的“固定節目”就有“三節兩壽”(端午、中秋、春節、上司誕辰、上司夫人誕辰),以及地方官送給京官的“冰敬”“炭敬”。《官場現形記》說:“三節兩壽,孝敬上司的錢,雖不敢任情減少,然而總是照著前任移交過來的簿子送的。”這“簿子”可不是前任白白移交的,它記載著節禮的正確“尺寸”,誰掌握了它,誰就在這場“地下軍備競賽”中掌握了獨門暗器,所以,后任要用數十上百兩銀子來買它。有位候補知州,好不容易補缺上任,卻不懂這“花錢買賬”的規矩,前任官員的賬房師爺憤而給他做了本假賬,記載的尺寸都是錯的。新知州按假賬孝敬上司,一年就被參劾革職。
一些“上級”在開心享用下屬節禮之余,免不了又得絞盡腦汁考慮如何給上司送節禮,為送多少、如何送、誰送誰不送等“技術難題”而煞費苦心。所以,請允許我善意地揣測,這樣的節日已是令上級下級都身心俱疲的“劫”日,如有可能,誰也不愿生活在這樣一個靠“猜心”過日子的復雜社會。那么,該怎樣,才能體面而平穩地結束這場“節禮牌軍備競賽”呢?
平心而論,古人也不是沒有作過努力的。被康熙帝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就貼出過一份著名的《禁止饋送檄》:“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送禮者訕訕識趣而去。在古代,這樣高度自律的官員并不多見。這是官員個人的“抗禮戰爭”;那么,朝廷的禁令,效果又是如何?
康熙時,為整治節日腐敗,曾推出一紙大清版“廉政承諾”,貼在大小官員家門:“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閑,應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歲元旦為始,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有蒙賜顧者,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亦不答拜……統希原諒。”然而,事實證明,這紙“廉政公約”并沒有遏止送禮之風的變本加厲、盛行不衰。
時間已過數百年而依然有“送禮致堵”,是何故?唯有一個解釋:權力還沒有完全關進籠子。“送禮政治”的根源在于資源按權分配而又無序配置。欲徹底根治,顯然還需從改進資源配置機制上來鏟除“送禮者得利”的土壤。一是終結“按權分配”,確立公共資源配置的一整套“明規則”,決策透明、民主監督,讓公權力無法隨心所欲想把手中項目資金和烏紗帽給誰就給誰;二是改變“權有制”,不讓社會資源高度集中于“上司”之手,將公權力的含金量下降,即既無法“照顧送禮者”,也無法“冰封不送禮者”。
唯如此,才有可能讓“節”遠離“劫”的低級階段,進化到“潔”的文明狀態,免得誤了天下豪杰的一生名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