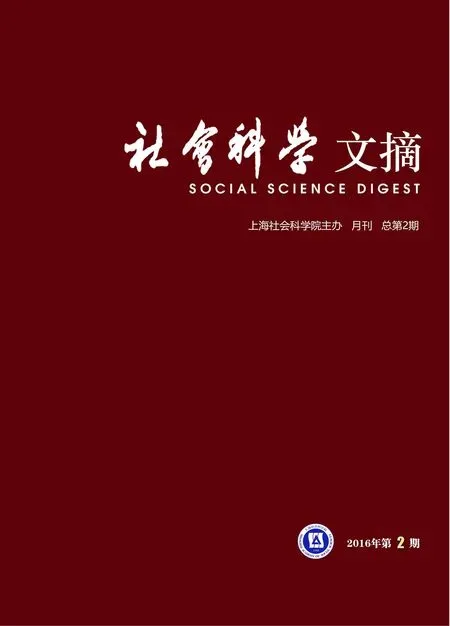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根源
——與顧鈺民先生商榷
文/劉順
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根源
——與顧鈺民先生商榷
文/劉順
復旦大學顧鈺民先生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1期的《生態危機根源與治理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不在于資本邏輯而是其他,用資本邏輯和社會制度不同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對此,筆者存疑,不揣冒昧以求教于學界前輩和同仁,共同推動該議題研究的深化。
資本邏輯何以成為生態危機的根源
“顧文”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不是資本邏輯,也并不是以利潤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制度。對此,筆者持有異議,資本邏輯恰恰成為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資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發財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因此“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逐利本性的資本邏輯是以“兩大法則”“兩種強制邏輯”和“社會權力”為建制和依托的,而三者均與生態理性相抵牾。
(一)“兩大法則”的逆生態性
1.效用法則的逆生態性
馬克思曾這樣言簡意賅地概括資本的效用法則:“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一方面創造出普遍的產業勞動,……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系的體現者。”具言之,資本欲把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生態在內囊括到“有用”的價值體系中去,只要“有用”于生成利潤,最大限度地掠奪自然資源和破壞生態環境便是其慣用手段。資本及其邏輯“永遠試圖在一段時間內,在一個地方建立一種地理學景觀來便利其行為;而在另一段時間,資本主義又不得不將這一地理學景觀破壞,并在另一個地方建立一種完全不同的地理學景觀,以此適應其追求資本無限積累的永恒渴求。對于資本家而言,沒有什么比獲取私人財富更為重要,破壞生態環境對人類來說是災難,對資本家來講往往是福祉。”增加私人財富而非投資改善自然生態才是資本所有者的價值追求。顯然,資本效用法則中所蘊含的逆生態性,已昭然若揭。
2.增殖法則的逆生態性
增殖法則直接表現為“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隨著平均利潤率的下降,資本邏輯愈來愈主張在更大的規模上掠奪資源和破壞生態,“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個自我擴張的價值體系,經濟剩余價值的積累由于根植于掠奪性的開發和競爭法則賦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進行。”因為“資本(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它必須不斷地被更新,更新的方式包括海外擴張、變革生產關系、占有更多的勞動獲取剩余價值、隨意地占有自然界以及把整個世界吸納到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去。”資本更新的上述實現方式,最終無不要依托到對自然生態的開發利用上。問題是,在資本邏輯的宰制下,對自然的開發利用不可能是友好可持續的,只能是充斥著唯利是圖的破壞性,盡管短期內資本家也可能有改善生態環境的沖動,但“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二)“兩種強制邏輯”的反生態性
1.生產強制邏輯的反生態性
資本的生產強制邏輯,是指“資本在實現了它的增值目的后決不就此罷休,資本家繼續把那些新增的剩余價值作為資本再次投入到下一個生產過程中,資本就這樣像一匹發瘋的野馬從此奔上一條不歸之路”。這種生產強制邏輯是以追求豐厚利潤和資本積累為目標的,必然要求使“自然界的一切領域都服從于生產”,“從資本價值計算的角度,自然界并不被視作有價值的東西,而是被當成某種免費的饋贈”。為了純粹的獲利,在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中,資本不可能友好地對待自然生態。
2.消費強制邏輯的反生態性
生產決定消費,資本的生產強制邏輯勢必帶來資本的消費強制邏輯。“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來為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意味著資本的消費強制邏輯制造了非真實需要的“虛假需求”,資本運動的無限性,就決定著這種異化了的“虛假需求”也是沒有終點反復循環的。但是,自然界的承載能力在一定的地質時期卻是有限的,只要消費強制邏輯持續在場,人類消費能力與地球自身的承受能力之間的“剪刀差”就會越拉越大。以此論及,資本的“消費強制邏輯”也均蘊含著反生態性。
(三)“社會權力”的非生態原則
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這就是資本邏輯之社會權力的真實圖景。生態原則需要照顧到自然生態的內在規律和可持續發展性,要求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理念,甚至要求無利潤、無功利地投資和補償自然界,且必須是長期性的。這無疑會增加資本的價格成本和時間成本,與持有社會權力的資本通過粗放地壓榨自然生態就能獲利頗豐的增長邏輯,是明顯抵牾的。反過來講,任何事物只能成為資本擴張和逐利的助推器,決不能成為其障礙物,否則就會被資本瓦解或消滅,它最后的敵人只能是其自身。在此種意義上,非把利潤置于首位的生態原則難免會觸犯資本的利潤邏輯,從根本和長遠看,必被資本邏輯所駁斥和拋棄。另外,資本邏輯“社會權力”的非生態原則與異化勞動也是互動耦合的,特別是資本與科技的聯姻合謀,“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長此下去,會帶來什么樣的生態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上述三個方面從理論上論證了資本邏輯何以成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同時,也就從正面質疑和直接回應了“顧文”的中心觀點——資本邏輯并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
如何看待所謂的“兩大理論困境”及“一個自相矛盾”
(一)所謂的“兩大理論困境”
“顧文”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邏輯”的觀點,在理論上必然而臨著兩大理論困境:一是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二是不能解釋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
1.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嗎
就“過去”而言,馬克思曾對資本主義的嚴峻生態狀況作過經典描述:“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么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來污染泰晤士河。”恩格斯也激烈批評道:“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才能把比泉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更多的糞便傾拋到海里去,……不致毒害倫敦全城。”在《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農業所造成的新陳代謝斷裂進行了充滿原則高度的本質批判:“大土地所有制是農業人口減少到一個不斷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們相對立,又造成一個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命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物質變換的聯系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不難看出,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對“生態問題的資本邏輯根源”有著深刻的思考,蘊含著高屋建瓴的生態洞察力。
就“現實”而言,表面上察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環境現狀“很令人滿意”,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望塵莫及。這一點恰如哲學中經典的“休謨問題”所透射的,我們無法從事實判斷推出價值判斷,無法從“是”導出“應當”一樣,無法從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良好的自然生態推出他們“應當”擁有良好的自然生態,因為這種良好自然生態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前提之下的,犧牲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自然生態等核心利益,是生態帝國主義在搞鬼。生態帝國主義包含著兩重含義:一是指生態范疇,即“生物擴張的生態邏輯”;二是指政治經濟范疇,即“資本擴張的政治經濟邏輯”。生態帝國主義與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并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經濟利益、生態環境和身體健康為代價來換取自身的狹隘利益,反映出國際秩序的深層不平等在當前歷史階段的時空延續,當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虛假繁榮,是建立在犧牲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常享有良好生態環境等核心利益之基礎之上的。
以此論及,“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邏輯”的觀點并不是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而是“資本主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這一“事實”掩蓋了“污染轉移”和“資本邏輯的逆生態性”這一歷史真相。
2.不能解釋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嗎
“顧文”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邏輯”的觀點也不能解釋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似是而非地看,該觀點真的不能解釋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因為目前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要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嚴峻得多,但問題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否也存在著或被動裹挾進資本邏輯呢?若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著資本邏輯,他們出現生態問題也就無法避免。“顧文”認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不存在資本邏輯的統治,是這樣嗎?這個問題搞清了,再來評價“生態危機的根源是資本邏輯”觀點就顯而易見。
資本作為一種現代的生產要素,也表征為一種社會關系,是現代性展開的邏輯中軸,沒有力量能夠改變資本的本性,無法從根本上消解資本與勞動、自然的對立關系,資本所固有的邏輯也就不是人為能消除的。而市場又是資本的“主戰場”,資本是市場的“主要居民”,沒有資本,就談不上市場,就不存在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將是一句空話。另外,從實際的生產生活來看,唯利是圖的資本邏輯無處不在,否則就不會出現甚至大規模出現影響居民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大規模的環境污染群體事件、頻發的強征強拆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的背后,就是資本邏輯在施威和發力。因此,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鮮活的實踐中,我們都不能否認當下的社會主義仍存在著資本邏輯,原因在于它是一種具有一定歷史壽命的客觀產物。
既然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也存在著資本邏輯,再加上前文已述的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各種霸權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推行生態帝國主義,那么,社會主義國家在生態問題上就面臨“雙重壓力”,生態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顯現就不足為奇,甚至有些時候會更嚴重。因此,“資本邏輯是生態危機根源”無論對于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言,都顯然成立,仍然能夠解釋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現實。基于此,“顧文”的這一論點就有待商榷。
(二)“一個自相矛盾”
“顧文”認為,“資本邏輯是生態危機根源”的觀點,面臨著“一個自相矛盾”——既然資本邏輯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利用資本力量來消除生態危機的觀點就面臨著矛盾,因為利用資本來解決生態危機的結果,就又使資本邏輯充斥于世,又生成生態危機新的源頭。筆者的疑問在于,若“資本邏輯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的觀點成立,就意味著不能利用資本及其邏輯來消除生態危機嗎?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具有歷史正當性且具有文明化趨勢,但“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資本的限制就在于:這一切發展都是對立地進行的,……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的財富的條件,而是當作他人財富和自身貧窮的條件。但是這種對立的形式本身是暫時的,它產生出消滅自身的現實條件”。馬克思認為,資本終究會“把資本推向解體”,“資本不過表現為過渡點”。因此,資本最終會成為資本自身發展的對抗體,利用資本來消解資本不是不可能,只是不到時候,在資本的正能量全部發揮出來之后,資本就會成為資本自身的掘墓人。
既然資本及其邏輯早晚將被資本自身所瓦解,我們為何不能去利用資本去消除生態危機呢?在此次意義上講,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再所倡導的“資本邏輯是生態危機根源”觀點的成立,并非意味著不能利用資本及其邏輯來消除生態危機,而是相反。所以,“顧文”這一說法也是有待商榷的。
不消解資本邏輯的宰制,“四大舉措”能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危機嗎
“顧文”的第三部分認為,消除生態危機要靠“四大舉措”:樹立新觀念、建立新模式、運用新科技和完善制度建設。毋庸多言,這些措施無論對于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固然重要,也是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致力于應對生態問題而正在做的事情。但是,“顧文”所講的是用這些舉措來從根源上“消除”生態危機。筆者的困惑正在于“消除”二字,絕不是在玩文字游戲,而是涉及生態危機根源的全球性問題。在資本邏輯大行其道的今天,對于全球范圍而非僅僅一個區域而言,倘若不最終消解資本邏輯的宰制,新觀念、新模式、新科技和制度建設只能是“治療”生態危機,而絕非能“治愈”生態危機,因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邏輯而非其他,沒有切中病灶的方案,不可能從根源上解決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只能算作不得不采取的延緩之策。
“顧文”理想地認為,樹立生態文明新觀念是消除生態危機的思想保證。我們不否認,無論對哪一種社會制度而言,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觀念對解決生態問題都是至關必要的。但是,放眼全球,在資本邏輯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形勢下,尤其是肇始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帝國主義在全球肆虐發威,即使這些觀念“再新”有用嗎?
再如,“顧文”認為,新模式也是消除生態危機的重要保障。這句話寬泛地看來,并沒有錯,但是,只要資本邏輯沒有被摧解,新模式即使“再新”,也不能從根源上消除生態危機。
對于“顧文”所倡導的新科技也是一樣,高端的科技固然是人類應對生態危機的重要手段,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改進,對自然生態的利用效率也隨之提高,盡管單位能耗在降低但需求量卻會大幅上升,其結果不是減少而是往往加大對自然生態資源的需求,這就是著名的“杰文斯悖論”。在資本邏輯的宰制下,科技創新能否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危機,并不決定于科技本身,而是取決于資本主義的積累和利潤原則對技術的制約和主宰,正可謂“科學技術并不是生態危機的核心問題,核心問題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自然之間的邏輯關系”。因此,不消解資本邏輯的宰制,欲在全球范圍內依靠新技術來消除生態危機也只是美好愿望。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摘自《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