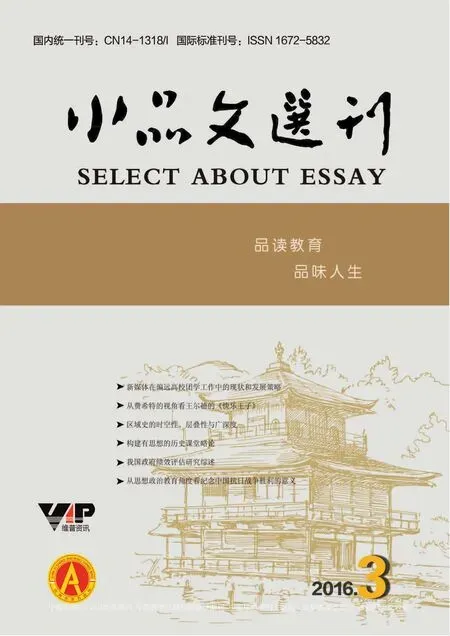論沈從文的《長河》
冷露紅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北京 100000)
論沈從文的《長河》
冷露紅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北京 100000)
沈從文是京派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寫兩類:城市;湘西。后一類主要抒寫湘西的風土民情,在他的這些作品里,我們能夠深深地感到他對湘西民眾那種淳樸善良的愛,他把湘西的景物和人物的美和善當做一種“常態”來供奉。總之,沈從文是帶著一雙搜索索真善美的眼睛去看湘西,揣著一顆大愛之心甚至是一顆頑固之心去寫他的湘西,他的湘西多是一種靜態美,這種靜態美也是“常態”的。然而,歷史的車輪在前進的途中會沖擊或者破壞那種“常態”,從《長河》這部作品,我們似乎可以發現沈從文對“常”和“變”的一種態度。
沈從文;《長河》;“常態”;“變”
《長河》是作者在1942年就開始提筆寫的,1945年第一卷寫完,以后就沒有繼續了,這部小說沒結局,這不得不說是個遺憾,雖是個遺憾,但這部小說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因為這部作品和之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也正好是作品中所體現的所描寫的“變”,這個“變”是在“常”的基礎上展開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看到沈從文對“常”和“變”的態度,沈從文好比那把頭扭向過去而腳步在向前邁的信天翁。作品是作家思想的結晶,作品內容的變化往往呈現了作家自身的變化。
1 《長河》開端誘導的錯覺
初讀《長河》的時候會覺得它是《邊城》的姊妹篇,夭夭和翠翠好似孿生姐妹一樣,老水手滿滿也能對應老船夫,還有滕老爺也能對應天保的父親,這些對應的人物是因為他們身上都有相似的地方。特別是看到《長河》的“人與地”這篇的開頭幾段我們會覺得沈從文還是在構建他的希臘神廟,還是在歌頌湘西的風土民情的淳樸善良,他的目的還是贊揚人性美。比如橘子的主人對要買橘子的人說:
“鄉親,我這橘子賣可不賣,你要吃,盡管吃好了。水泡泡的東西,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十個八個算什么。你歇歇氣再趕路,天氣老早咧。”
讀到這里我們會想湘西人太無私,他們是一談到錢就覺得俗氣么?其實當我們讀到后面就知道他們的橘子是要賣的,只不過不能在樹底下收錢,會影響來年橘子收成,在“人與地”接下來的篇幅里還提到了“革命”、“反動分子”和“五四”以及“女子教育”問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的《長河》已經有了“變”。看看《長河》里湘西人們對“常”和“變”的態度,這樣也許我們可以揣摩一下沈從文對“常”和“變”的態度。
2 人們對“新生活”的恐懼
對“新生活”,本來應該是期待的,可是大多數人卻是恐懼:那個背著剛買的豬娃回家的婦人對“新生活”是恐懼的,老水手對“新生活也是排斥的,當老水手對滕長順老爺和稅局中人提起“新生活”的時候,滕老爺和稅局中人沒有想象的那么害怕,反倒是笑將起來,他覺得新生活又不是人,又不是軍隊,來就來,派什么偵探?怕什么?稅局中人老是看《申報》的,因此把所值得的新事情說給他聽,由于老水手不怎么懂新聞的意思,就不再說了;夭夭一開始對“新生活”是抱著一種恐懼的態度,只不過在父親的言行中那種泰然,她看到了信心,所以也就不恐懼了。在末尾,當三黑子在罵到鄉下來的官都是欺善怕惡,什么事都做得出來,而下面的士兵和同學一樣,斯文老實得多,從不敢欺侮老百姓。此時夭夭瞥到橘子園樹叢邊有個人影子在晃動,以為是保安隊上的人,因此制止住了哥哥:“那么莫亂說,新生活快來了,凡是都會慢慢的變,慢慢的轉好的!”夭夭說這句話也許是給外人聽的,但是也許是給自己安慰的,人畢竟是活在希望中從快樂的,她希望“新生活”能夠帶來一種“變”,當然這種“變”是往好的方向。
夭夭對新生活的態度,也許某種程度反映了作者對“變”的態度,作者在描寫“變”的同時他也描寫了很多“牧歌式”的生活,可謂“變”中有“常”,“常”中有“變”,當然“變”包含的內容當然不僅僅是“新生活”還有更多是湘西目前那種不好的“變”,這種“變”對那種“常”是一種褻瀆和毀滅,眼下的湘西也許不再是以前的湘西。
3 “常”和“變”共存
在“秋”的章節里,作者描寫了呂家坪和楓木坳以及蘿卜溪的美麗民風民情:
“狗咬你,瘋狗咬你!”
“是的,狗咬我。我舌子就是被一只發了瘋的母狗咬過!在一棵大桐木樹蔭下……”
因為說到婦人不想提起的一點隱秘事情,女的發急了,紅著臉說:“悖時砍腦殼的,生福,你再說我就當真要罵了!”
看完這些,聯想到小時候看到大人們之間開的黃色玩笑。這也是湘西的一個小傳統,是一種“常”的延續,雖然外界的“變”在漸漸輸入湘西,可是有些東西已經進入了湘西人的骨髓和夢境。當然有些不變的“常”未必就是好的,比如湘西人對違禁的童養媳進行非人般的折磨,對于童養媳的態度,《長河》與《蕭蕭》有很大的區別,這也證明沈從文在某種不過程度上更客觀來看待湘西文化中的“常”,而不是憑借著對家鄉的愛去完全美化。
結合沈從文以前的作品我們在《長河》里仍然可以看到他對湘西牧歌式的生活的熱愛,他舍不得它們被破壞,但是他明白歷史的車輪總體是向前的,他的作品也要與這個時代接軌,他不僅寫“常”也關注“變”,他的愿望是把“常”到“變”這個過程呈現給讀者,寫出“常”與“樂”交匯處的喜怒哀樂,《長河》雖然只出了第一卷,但它給我們呈現的就是作者愿望的,雖不完整,但是它好比維納斯,有一種殘缺的美。
[1] 沈從文.《長河》[M],北岳文藝出版社,2005年4月.
[2] 金介甫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傳》[M],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年10月.
[3] 趙園.《沈從文》[M],中國和平出版社,2001年10月.
[4] 張德成.從《長河》中看沈從文的鄉土情結,[J],赤峰學院學報,2014(4).
[5] 嚴淑芬.喧噪中的平靜——評沈從文《長河》,[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1997(5).
[6]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M],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5月.
[7] 吳宏聰.沈從文的鄉土情節[J],海南師院學報,1996(4).
[8] 雷啟達.淺析沈從文《長河》創作主題[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1(10).
[9] 周仁政.沈從文的現代憂懼——《長河》縱論[J],武漢大學學報,2014(1).
I108
A
1672-5832(2016)03-006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