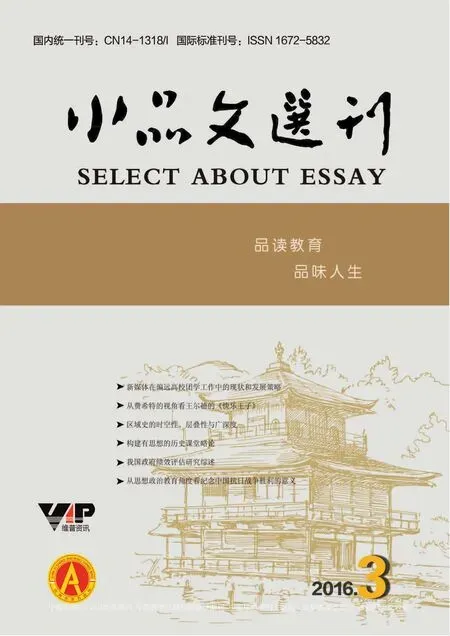論析新成長小說中成長關系的建構
王曉紅
(暨南大學 廣東 廣州 510632)
論析新成長小說中成長關系的建構
王曉紅
(暨南大學 廣東 廣州 510632)
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始終伴隨著兩種關系:“我——我”的關系和“我——社會”的關系。在新成長小說中,它們呈現出新的建構模式:從傳統的融入社會成長轉變為與社會分離的個體成長,從自我的無意識演變為“反成長”的個性書寫,成長關系在解構社會成長本位的同時又試圖重新建構個體成長本位。
新成長小說;成長;關系;建構
成長何為?這是一個永恒的命題,無論是對于個人的成長或是作為文學的母題。個人的成長“不僅意味著生命個體性的成熟,有能力承擔起種族繁衍的職責,而且意味著穩定個性的形成、自我概念的同一;意味著脫離家庭步入社會;意味著第二次降生”[1],這也就意味著個人成長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的兩種關系:“我—我”的成長關系和“我—社會”的成長關系。這兩種關系在文學的表征中,盡管形態不同,但成長儀式的中心卻始終指向:我是誰/我正在走向何處,以及我如何/才能發現和實現這兩者。事實上,它是指向“我”和“社會”,以及如何實現這兩者。在新成長小說中,這兩種成長關系的建構過程變得十分的微妙復雜。
成長主題或原型在文學中較早可以追溯到:神話、悲劇、《圣經》等,但成長小說最終成為一種文學樣態卻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時期,這其中伴隨著思想史、教育觀的發展和演變。
一般認為,“成長小說作為一種類型肇端于西方啟蒙時期,盧梭《新愛洛伊絲》就是最早的成長小說之一。一個少年或青年的成長歷程,他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這個世界如何對他進行教育,這些就是成長小說的基本主題。所以成長小說也可以說是教育小說,它表達了啟蒙時期對人的社會化過程的特殊關注,是人文主義價值觀建構過程中的一部分。成長小說在18,19世紀臻于極盛,特別在德語文學中,通過歌德的《威廉·麥斯特》、凱勒的《綠衣亨利》,這個類型得以發展完備。”[2]這類成長小說往往“展示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歷了切膚之痛的事件后,或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自己的性格,或兩者兼有;這種改變使他擺脫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終把他引向了一個真實而復雜的成人世界。在成長小說中,儀式本身可有可無,但必須有證據顯示這種變化對主人公會產生永久的影響。”[3]因而,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成長模型,其一,在結構上:迷惘—頓悟—成長,經歷一系列苦難,最終進入成人的世界;其二,在人物關系上:主人公——引路人/陪伴者,無論這引路者是長者或是同齡人,還是自然或者動物,陪伴始終存在。經典成長中的主人公,無論經歷了什么,最終都指向成長,或主動或被動的融入社會的成長,代表作品有《湯姆·瓊斯》《霧都孤兒》等。
“但是,到了20世紀,我們己經很難找到一部重要的、比較純正的‘成長小說’了,根本原因在于,人文主義的理想在20世紀己經破滅,這個時代的主題不是社會如何正確地教育人,而是人如何反抗資本主義物化社會。”[4]可以說到了20世紀,成長小說已然發生了變異,我們暫用“新成長小說”來命名這種文學現象,當然,這樣的命名并不只是因為出現了新的因素,重要的是成長的內涵和呈現的模式發生了質的變化。社會環境、思想觀念、時代精神、文學藝術的不斷變遷,為新成長小說注入了永恒的新意和活力,事實上,從成長小說到新成長小說,兩種模式的轉變與人文思潮的演變有密切關系,“從文藝復興開始,‘人的發現和個性解放’使得新發現的‘人’和‘世界’的形象都是光明的、正面的;但是,從19世紀后期以來,以非理性主義為特征的社會思潮的發展,使人們對‘人’、對‘世界’有了與過去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認識。”[5]“上帝死了”的宣告使得人們依賴的精神偶像和支柱傾然轟塌,人們進入了精神的跋涉狀態,隨之種種關于“人”的傳統信念卻被現代社會和現代思想發展無情地摧毀了,現代社會非但沒有提高人的價值和尊嚴感,反而粉碎人的精神家園。這樣,人與世界的關系開始變得模糊,個人再也無法找到一個順其自然的方式與自我和他者和諧共處,在新成長小說中體現為,迷惘的自我成長和分離的社會成長。如果說,傳統的經典成長小說注重的是與他者——社會的關系,那么在新成長小說中,由于人文理想的破滅,這種主流的社會本位成長關系發生了動搖,甚至是轉向,從某種程度上說,新成長小說更加關注以個人為本位的自我成長,但由于與社會的分離,失去依附的個人成長往往是混亂和迷惘的狀態,甚至會產生一種自我身份的焦慮感,在對待與社會分離的關系上,則呈現出一種叛逆的社會成長現象,拒絕融入社會:“在20世紀,‘成長小說’作為一種類型依然活著,它在許多作品中被從反面運用、被戲仿。如果說在經典成長小說中,我們看到一個人被錘煉出健康、正確的人格,他長大了,滿懷信心、朝氣蓬勃地走向社會,那么在‘現代’作品中基本的情節是一個人拒絕長大,或者怒氣沖沖地逃到了路上。”[6]
每個時代都有困擾年輕人成長的不同主題,而不同的時代精神又為人們面對困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和路徑。聚焦20世紀,社會環境、思想文化以及文學藝術發生了巨大變化,多元化的背景中,年輕人的成長道路已然出現了新的方向。
“迷惘的一代”就是20世紀出現的第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年輕群體,雖然在最初,它是指稱一戰之后出現在美國的一個文學流派。在文學表征中,這些年輕一代在巨變的社會環境里,滿是幻滅感,他們迷惘、游蕩、又不知所措。人文理想的破滅、戰爭的爆發,打破了以前一種相對和諧的關系狀態,個人再也找不到一個順其自然接納他們的港灣。于是,在迷惘中,迷惘的一代將他們自我放逐,正如置身于霧中,晨起迷路,迷惘中探索記憶中的方向:他們相信,現實才是真理,可現實是殘酷的,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明確的反社會行為和意圖,只是對一切事物不感興趣,擺出一切事物都與己無關的姿態,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找不到成長的方向,一大批極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如《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等就是當時年輕一代的成長寫照。
二戰后,出現了瘋狂的“垮掉一代”。從最初的文學流派轉變成為一種社會成長現象,垮掉的一代不再期望社會的回歸和信仰的拯救,相反,他們一開始就對社會不抱任何幻想,一開始就看透了社會,毫不妥協,他們甚至采取偏激怪異的行為引起社會的注意,以不能為常理所接受的行為表現他們的成長姿態。“我看見我們的一代精英被瘋狂所摧毀了最好的思想……”與社會的格格不入導致了社會和人的異化,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武器來對付那個不給青年一代成長余地的社會現實。他們砸碎了現存的價值觀,卻無力建立起新的來支撐自己”,只能選擇反抗,而這種反抗卻又是無向度的,最終他們徹底拒絕了經典的成長模式,只能永遠的在路上……
在新成長小說中,成長儀式再也不像經典成長小說中那樣順其自然的完成了,成長失范和成長反叛成為年輕一代的常態。社會再也不是溫和的接納和拯救這群不聽話的“壞孩子”了,更多的時候,社會隱性的成為了年輕一代成長的某種阻礙。與社會的分離成長勢必會帶來某種隔閡,社會期待年輕一代接受現實,按照形成的社會規范和價值理念行動成長,而社會境況的變化讓這種教育再也不起作用了,標新立異的行為一方面表達了個性,另一方面卻是對社會的反叛。事實上,“反成長”成為與“我——社會”成長關系的實質特征。表象之一:拒絕成長,君特·格拉斯《鐵皮鼓》中的奧斯卡形象極具代表性。表象之二:反英雄、反歷史,英雄成長神話不再出現在新成長的言說中了,關于歷史、家族的成長記憶也漸漸消失了,類似于《大衛·科波菲爾》經典成長模式已經銷聲匿跡了,在新成長小說中,主體的呈現開始更加廣泛化、平民化和私人化。表象之三:反“文化”,這里僅僅將其限定為新成長小說中那些不符合社會常規文化、價值觀念的成長意識,也包括移民文學中的成長文化沖突。如果說羅曼蒂克和冒險是上一代人的成長范式,那么在新成長小說中,性、同性戀、暴力、父母離異、種族隔離、戰爭等等構成了新一代年輕人生活的新圖景。當然,這些場景或許正是當下社會的某些文化現象,但即使是在多元的文化社會里,對年輕一代的成長期待仍舊是符合常規的主流的文化價值理念。
綜上分析,這種“我——社會”的“反成長”關系表面上是因分離帶來的直接后果,本質上代表的卻是是一種成長的渴求,期待社會包容和接納迷惘的、個性的成長,只是求而不得,種種的反叛行為只是想引起更多的關注和引導,社會給予的卻是不理解、不滿足的態度。因此,在這種循環中,成長的社會關系建構變得復雜、艱難而漫長。
事實上,這種社會成長關系的建構往往與“我—我”的成長身份認同密切相關,成長中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沖突往往會產生自我同一性的危機,如果危機不能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無歸屬感、為人冷談冷漠、甚至是出現攻擊性等極端行為。同時,這種自我成長在新成長小說中往往體現為個人化的書寫表達,即傾向于內心獨白或私人隱秘生活的呈現,這顯然與傳統經典成長小說中的社會本位成長有很大的差別。20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生活在萬物都有可能被解構的時代,自我的主體性和唯一性也受到的了質疑和動搖,這種“我——我”的自我成長關系無論是在現實環境中,還是在文學表象上,都顯得十分的混亂,成長的身份焦慮上升為一種時代病:年輕一代焦慮的成長著。本質上,我們渴望獲得個人的同一性,渴望能從信賴的他者那里獲得所期待的認可和支持,求而不得的失望和失落讓成長的歸屬變得遙遙無期,其結局往往或是繼續的在路上尋找,或是回歸——回不去的童年、不受染指的自然、走向絕望的死亡……光明的長大似乎只是過去的童話故事。
成長永遠沒有終結,在“長不大的孩子”和“自以為不需要成長的孩子”那里,成長之痛依舊存在,并且在當下社會中,成長的樣貌又呈現出奇特的景觀。互聯網的時興讓成長的秘密不復存在,那些難以言齒的欲望和心理似乎只需要輕輕點擊鼠標就可以解決,我們耳濡目染的受到這不設禁區的信息爆炸影響。一般認為,“傳統社會中人的成長是傳統引導型 ,引導人們行動的是常規和習俗,是公認的正確方式,甚至在早期社會中,倡導內在引導,即人們相信自己的判斷和創造力,膜拜自我內在權威。而在新媒體時代,成長是他人引導型,媒體時代的關鍵詞是時尚,一種集體參與的生活狀態,又是一種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潮流,一種誕生和消亡都很隨意的東西。時尚抹殺了原創性生活,每個人都自以為是自我個性,但個性很可能不過是流行新款。他人引導的實質是整一性,如何與別人存在差異,便會感到莫名其妙的焦慮”[7]。互聯網一代似在拒絕成長,又似在虛擬的世界中完成了青春,只是當這種個性成長變成了流行成長,成長的意義也便不復存在了。
現在習慣用代際來劃分群體,青春成長的一代在當下定格為90后和00后,時代迅猛的發展讓90后也成為“落伍者”,還沒有長大,追憶便開始。“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系列青春回憶成為熒屏時尚,我們被裹挾在青春濫觴中無處逃離。成長在當下中國的小說和電影中被包裹成愛情的模樣在肆意的兜售,這是誰的青春?這是誰的成長?我們不滿,卻又無法證明和反抗。似乎表現出的鏡像就是只停留在談情說愛的朦朧青春成長階段,這樣的刻板印象和社會的成長期待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大,個人成長的速度跟不上社會發展的速度,“無法斷奶”的成長被無限期“延長”了,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于自我內心中,成長身份都始終找不到一個立足的地位。不談信仰,沒有歷史,毫無經驗,遠離根土,互聯網時代的“90后”“00后”成為了“無根的一代”,表面上似乎只關注個人的吃喝玩樂,事實上,他們的內心是十分惶恐和焦慮的。“長不大”或者說是“不想長大”,在不愿意過早承擔社會成長身份責任的同時,自我的成長身份也在焦慮中無法形成。
在21世紀中國文學中,并沒有形成或者是表現出西方新成長小說中嚴格意義上的“我——社會”的“反成長”關系。“無法斷奶”的成長似乎還得依附社會或者是社會的縮小版——家庭,“不聽話”的叛逆表象是炫富、暴力和性。
吐槽,成為“我”與“社會”的溝通方式,這也是互聯網的產物,并且一直在繼續著。無法形成共同的對話場域,也沒有形成一個真實的群體鏡像,新世紀的成長中,在與社會關系上,總有一種無法言說的糾結存在著。成長中,我們在焦慮著,社會也在焦慮著。
說不清的成長,說不完的青春,或許,這也就是它的精彩處。每個時代、每個人都會經歷成長,只是成長的色彩各不相同罷了。與社會分分離離,自我或自然、或清晰、或迷惘、或逃離、或焦慮的成長著,終極目標指向的都是社會中的自我成長,無論這種成長儀式最終是否完成。破繭成蝶,成長必定是“在清新的空氣中飄散著少許血腥氣味” 的過程。
[1] [7]李學武:蝶與蛹——中國當代小說成長主題的文化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頁、第227—228頁
[2] [4][6]李敬澤:紙現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88頁
[3] 張國龍:成長小說概論.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第13頁
[5] 田廣文.困惑的張望——新潮成長小說論,碩士論文,2002年,25頁
王曉紅(1991.10-),女,湖北武漢人,暨南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影視文學方向。
I247
A
1672-5832(2016)03-008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