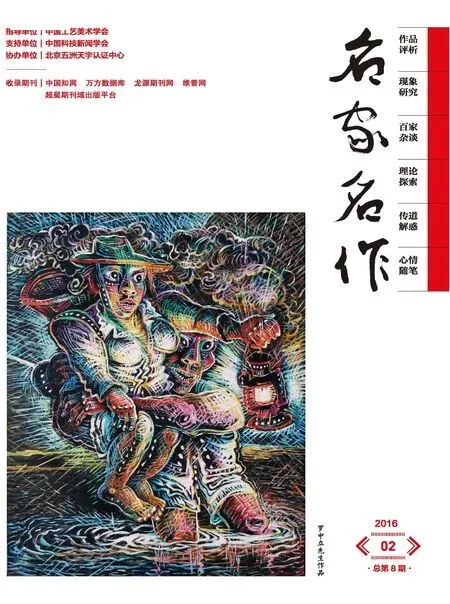論蕭紅小說“散文化”形式中的深刻意蘊
張鳳渝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常州衛生分院,江蘇 常州 213002)
?
論蕭紅小說“散文化”形式中的深刻意蘊
張鳳渝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常州衛生分院,江蘇 常州 213002)
[摘 要]蕭紅小說在語言文字、敘述結構、敘述方式和抒情方面都表現出鮮明的“散文化”特征。這種形式表現了她對生命的深刻理解,深化了悲劇的審美意義,使作品的悲劇意義超出了個體和時代,更具有普遍意義。
[關 鍵 詞]小說;散文化;意蘊;情感
一、“散文化”的小說風格
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雖然算不上一位大家,但卻是最善于建立自己藝術風格的作家之一。她惜才如珠,并以開放的胸襟把藝術才華的生命更新建立在探索精神上,勇于打破藝術的陳規,她對文壇的貢獻在于憑借出色的才情越出傳統小說法規的軌道,以明麗新鮮的筆觸、細致的觀察和感受,將小說散文化、詩化和繪畫化。而其中“散文化”是其小說風格最突出的特征,表現在稚拙清新的語言風格,場景式的結構方式與漫不經心的敘述方式三個方面。
首先進入讀者的感官,觸發讀者感覺的是蕭紅的文字。她作品中一切情緒、意念等等,無疑是借諸文字而訴諸讀者的審美感情。散文相對于詩歌來說,賦予語言表達更大的自由,也更便于負載某些情感。“散文”不只是情韻,不只是結構,也是一種語言形式。
蕭紅的文字,是一些用最簡單,以至于稚拙的方式組織起來,因而常常顯得不規范。比如:
呼蘭河這小城里面,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三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八十歲,祖父就死了。
從前那后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園里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依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1]
幾乎是無以復加的稚拙,單調又重復使用的句型,同義反復,在語言學家眼里似乎是費話,然而讓人驚異地感到,這種最樸素俗白的文字,經蕭紅的靈性,而具有某種感人的情調,這也許就是魯迅所說的“越軌的筆致”。她的文字樸素、平淡,而又新鮮明麗,處處散發出蕭紅特有的醇厚美。這種語言風格,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樣是刻苦追求提煉的結果,而似乎完全出自她天才般的藝術直覺,出自于她對事物的獨特感受,一切都是自然流出。她的語言絕對難稱“精美”,它們只有構成整個句段篇時,才顯示為美;它們不具備修辭學的典范性,甚至出于文法的規矩之外。
與稚拙的“文字”組織相適應的是作品“無結構的結構”。她以自己的美學追求,借助自己的文字組織,有效地使戲劇性淡化了,使情節淡化了,使小說化解為散文。她通常不是依“時”序,而是直接用場景結構小說。如,對于事情的發展過程顯得漫不經心,只肯把氣力用在一些富有情致的場景上。久貯在記憶中的印象碎片,就這么信手拈來,嵌在“過程”中,使作品處處洋溢著蕭紅特有的氣息,溫潤的、微馨的。蕭紅的敘述中永遠有情境,完整地滿溢著生活味的情境。這些“情境”散化了情節,濃化了情致韻味。
情致韻味正是散文化的又一個特征,即情緒化。蕭紅的小說并不以“抒情性”為特征。“抒情”應當是以抒情主體存在為前提的。蕭紅作品的情緒特征在于那浸透了文字的“感情”,這是一種與文字、與內容不可分離的元素。蕭紅并沒有刻意要抒情,然而,我們讀她的作品總能透過她的文字、結構、敘說感覺到一種情感的力量。蕭紅作品特有的情緒特征、情緒力量主要不是經由主體的發“抒”,而是經由她特殊的文字組織來實現的。
富于魅力的更有蕭紅的講述。無論使用怎樣的人稱,那都是她的講述,一派蕭紅的口吻,因而本質上都是第一人稱。她最成功的幾部作品,如《小城三月》《牛車上》《呼蘭河傳》,都是由一個獨特的“兒童視角”來完成其藝術創作。兒童看世界、思考世界的特有方式,不是訴諸經驗與理性,而是訴諸生動的直觀,所以才有蕭紅稚拙清新的語言風格、場景式的結構方式與漫不經心的敘述。
二、“散文化”形式中蘊含的深刻意蘊
評價一種形式的優劣,必須看這種形式是否更好地表現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如果我們認識不到形式中蘊含的深刻內涵,也就不能對她的風格做出公正的評價。
《生死場》初現文壇,“給上海文壇一個不小的新奇和驚動”。[2]因其出現在東北淪陷后的1935年,作者為東北流亡青年,作品又是涉及抗戰題材較早的作品,于是人們遂將其作為三十年代抗日文學的奠基作品之一 ,并據此批評它描寫人民斗爭不夠堅定,未寫出革命主流和黨的領導,有悲觀情緒。《呼蘭河傳》的出現,已完全遠離了“火熱的斗爭”生活和“大時代”“血淋淋”的現實。于是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個“不可否認的退步,是個人寂寞情懷的寫照”。[3]
《生死場》《呼蘭河傳》在表層的“散文化”敘述之外,隱藏著深刻的主題。《生死場》在將人推到非人的境地,思考其生命活動的同時,也將“生”推到“死”的境地來考察其生命價值。《呼蘭河傳》是這一審美思考的深入與延伸,寫出了為死而生,生不如死。人的生命活動讓位于“鬼”的禮儀、祭俗及其陰森統治的種種病態人生相,從而發展了“國民性”思考的歷史主題。由于作家著眼于整個民族靈魂的改造,她所關注的中心,就不再是脫出社會常規的個別的、奇特的、偶然的事件和人物,而是民族大多數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最一般的思想,是整個社會風俗。瞬息萬變的生活現象,特別是人的精神現象,不是沿著一條或數條情節線的傳統敘述方式所能載負的。蕭紅出生于一個開明的地主家庭,在哈爾濱受過現代教育,受著“五四”新文化的深刻影響,后來直接受到魯迅這位思想巨人的影響,這一切都使她更多地接受了世界近代的人文主義思潮、民主精神以及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文化覺醒意識,成為一個根植于現實土壤的“現代文化”追求者和思想先驅。表現在藝術創作道路上,她不囿于傳統,勇于探索新的表現手法。她曾說過:“有一種小說家,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4]
《生死場》著力思考的并不是正面對敵斗爭等現實生活的外部關系,也沒有戲劇性的英雄樂章般大起大落的藝術情節,而是對民族自立的潛在障礙及其封閉落后而又愚昧陳腐的文化心態進行歷史反思。這使其最終舍棄了以情節取勝的新舊藝術傳統,而用散文的筆法、“內化”的結構完成其獨特的審美思考。她的作品有著細膩悲惋而又敏銳曲致的女性“陰柔美”。不過這已不是傳統女性溫柔典雅或“猶抱琵琶”的“楊柳岸曉風殘月”,而是“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新女性敏慧、犀利、悲惋而又深邃的審美選擇。
蕭紅小說散文化的風俗畫卷曾多次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和責難。這是由于其不符合被尊奉一時的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審美信條所致。“對于題材的組織力不夠,全篇顯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著中心的發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應該得到的緊張的迫力。”[5]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作者從沒有硬去按其臆想的因果邏輯關系編織一個完整故事,或是一定讓幾個貫穿首尾的人物做結構上的行動線索或藝術銜接,而是來去自如,將“環境”當作一個結構線索,一個具有某種性格的主體來描寫。使諸多的人物故事只作為這一環境的點綴。使環境成為悲劇的深層內因,從而喚醒人們對于所處環境的自覺認識。蕭紅小說是深刻的,這深刻性在于她把“環境”的意義從一種襯托性的背景和靜態的客體發展為具有主體品格的文化現象。
蕭紅小說的時空結構里寄托著她對于歷史文化的理解。時序的概念對于理解蕭紅作品的結構有時全無用處。那些作品的各構成之間,往往不是依時序,而是由一種共同的文化氛圍焊接在一起的。蕭紅更注意的,是歷史生活中那種看似凝固的方面,歷史文化重壓下的普遍而久遠的悲劇,她用比當時許多作品寬得多的時間尺度來度量這種悲劇。《生死場》寫了四時的流轉,卻沒有借時間“推動”情節。占據畫面的是信手展示的一個個場景。《呼蘭河傳》的前半部,更索性使時間帶有更大的假定性:是今天,也是昨天或者前天,是這一個冬天,同時也是另一個冬天,是世世代代無窮無盡的呼蘭河邊的日子。這種時間意識在于強調歷史的共時性,強調文化現象、生活場景的重復性。從而由這種歷久不變的生活現象發掘民族命運的悲劇性。這樣的“時間”當然構造不出通常意義上的“情節”。小說特征在這里也就沖淡了。
時間的假定性勢必造成敘述內容的假定性。出現在《呼蘭河傳》開頭的,無論“年老的人”還是“趕車的車夫 ”,甚至于“賣豆腐”的,都是特定的個人。因而,即使“個人命運”,在這里更帶有共同命運的意味。時間的假定性,使特定的空間范圍(呼蘭河)在人們的感覺中延展了。是“呼蘭河”的“傳”,又不僅僅是呼蘭河的。蕭紅作品中的情境在虛實之間,在具體與非具體、特定與非特定之間,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寫實與寓言之間。《呼蘭河傳》首章中關于大泥坑的故事,就是“呼蘭河生活方式”的象征,“意味”又更在呼蘭河外,同時也是中國歷史、民族命運的象征或者寓言。敘述方式、時空結構又不僅僅是形式,其中更有深刻的內涵。蕭紅以“兒童視角”出發,平靜地、漫不經心地,甚至用一種溫和的略帶調侃的語調來敘述悲劇,讓人感覺不到那種由災難性的生活變異帶來的刻骨銘心的痛苦,而是因年深月久而“日常生活化”了的漫無邊際的痛苦。后者比前者在美學的天平上也更有分量。
蕭紅是寂寞的。寂寞地苦苦追尋,寂寞地死在從異鄉到異鄉的旅途中。她的作品也始終浸透著寂寞情懷,因而有人為作品中無處不在的悲涼氣氛,一再惋惜。“在這一心情投射在《呼蘭河傳》上的暗影,不但見之于全書的情調,也見之于思想部分,這是可以惋惜的,還像我們對于蕭紅的早死深至其惋惜一樣。”[6]
蕭紅并沒有沉浸在自己的身世之感,她把自己對于生活的悲劇感受集中在人類生活中如此“尖銳”的“生”與“死”的大主題上。她尤其一再地寫死亡,寫輕易的、無價值的、麻木的死和生者對于這死的麻木。
在蕭紅看來,最可痛心、最驚心動魄的“蒙昧”是生命價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費。
生、老、病、死都沒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長去;長大就長大,長不大就算了。[7]
恬靜到麻木,殘酷到麻木的,是鄉間的生活。這“麻木”在蕭紅看來,是較之“死”本身更可悲的。流貫蕭紅創作始終的激情正是關于這一悲劇現象的激情。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熱望,構成了蕭紅小說有關“生”“死”描寫的主要心理背景。
并不尖銳痛徹卻因而更見茫漠無際的悲涼感,如淡淡的霧、寂寂的霜,若有若無,無處不在,而又不具形色。它正是蕭紅所特有的文字組織、敘述方式,也無法由字句間,由敘述的口吻中剝出。
強烈的生命意識,使蕭紅寫“生”寫“死”,寫生命的被漠視,同時寫生命的頑強。蕭紅是寂寞的,卻也正是這寂寞的心,最能由人類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領略生命感,一派天真地表達對于生命的欣悅,寄寓她對于美好人生的永遠的憧憬和期待。正是這兩面的結合,才更見蕭紅的深刻。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飛上天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8]
如此親切體貼富有生命力的自然描寫,在蕭紅的作品里比比皆是,她把“生命感”注入她筆下那些極為尋常的事物,使筆下隨處有生命在勃發、涌動。并非有意的“擬人化”,卻一切都承有著自己的生命意識,活得蓬蓬勃勃、生機盎然。蕭紅并不大聲呼喚生命,生命卻流淌在她的文字里。
天真無邪的生活情趣與飽經滄桑的人生智慧,充滿歡欣的生命感、生命意識與廣漠的悲涼感,都碰在一起,也才有蕭紅的淡而有厚味,稚氣而有深度,單純而有智慧。
蕭紅以自己獨特的生命感受和藝術天才突破了藝術表現的常規,選擇了最有利的角度切入生活,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個性、最有利的方式來表達她深刻思想,奠定了她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位置。
參考文獻:
[1]蕭紅.呼蘭河傳[M].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05:265.
[2]許廣平.追憶蕭紅[A].張毓茂,閻吉宏.蕭紅文集[C].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07:376.
[3]葛浩文.蕭紅評傳[M].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03.
[4]聶紺弩.蕭紅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2.
[5]胡風.生死場(后記)[A]張毓茂,閻吉宏.蕭紅文集[C].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07:327.
[6]茅盾.《呼蘭河傳》序[A].張毓茂,閻吉宏.蕭紅文集[C].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07:12.
[7]蕭紅.呼蘭河傳[M].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05:39.
[8]蕭紅.呼蘭河傳[M].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05:90.
張鳳渝,女,漢族,江蘇盱眙人,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常州衛生分院講師,南京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碩士。
On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Xiao Hong’s Novels in the form of “Prose Features”
ZHANG Feng-yu
Abstract: Xiao Hong’s novels show distinctive features of“prose features”in the language, narrative structure,narrative style and lyrical aspect. This form shows her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fe,and deepens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tragedy, so that the tragedy of the work is beyo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times,but also ha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novels;prose features;implication;emotion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8854(2016)02-0008-03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