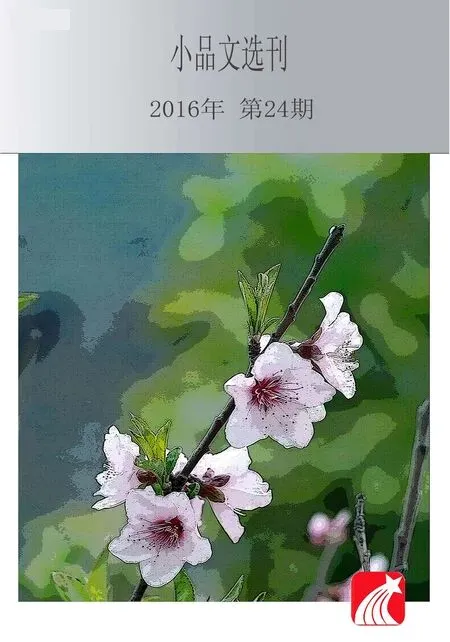《<三國志>知意》評介
李嘉悅 秦 平
(1.西華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四川 南充 637009;2. 西華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三國志>知意》評介
李嘉悅1秦 平2
(1.西華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四川 南充 637009;2. 西華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三國志>知意》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研究《三國志》十分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作者劉咸炘在充分閱覽古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不拘泥于前人思路,而以自己獨(dú)到見地寫成該書,對于進(jìn)一步推動《三國志》的研究有著重要價值。
劉咸炘;《三國志》;《<三國志>知意》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全面總結(jié)學(xué)術(shù)的時期,由于統(tǒng)治者大興文字獄,諸多學(xué)者受制度之禁錮,不能悉心鉆研己好,只得轉(zhuǎn)向?qū)糯墨I(xiàn)的整理與研究。其中,《三國志》作為我國歷史上重要的史學(xué)典籍,清代學(xué)人對其極為推崇,著述頗豐,劉咸炘《<三國志>知意》就是代表作之一。
劉咸炘(1896-1932),字鑒泉,號宥齋,四川成都人,清光緒丙申年生于純化街“儒林第”祖宅。其祖父劉沅、父親劉枘文、堂兄劉咸滎,均為蜀中近現(xiàn)代知名學(xué)者,門徒遍及巴蜀。劉咸炘家學(xué)淵源極深,自幼便有“神童”之譽(yù),五六歲時就業(yè)于其父,九歲便可日覽群書,二十歲即任教于從兄劉咸焌之尚友書塾,遍涉經(jīng)、史、子、集與西學(xué)著作,是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與目錄學(xué)家,他歷任成都大學(xué)、四川大學(xué)教授,被譽(yù)為“中壘文章堪名世,實(shí)齋著述有傳人!”
出生清末、成名民國的劉咸炘一生雖僅有短短三十六載,但其著作之豐,涉獵之廣,令人稱奇。他所著之書共計(jì)235部、475卷,總名《推十書》,《四史知意》是他史學(xué)研究的代表作。《<三國志>知意》是《四史知意》中的一部,也是民國“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三國志>知意》由劉咸炘在《讀<三國志>記》的基礎(chǔ)上加工而成,該書脫稿于民國十九年(1930),刻成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是研究《三國志》不可或缺的資料。因劉咸炘去世較早,其學(xué)術(shù)成果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揚(yáng),專門研究該書的專家學(xué)者不多。筆者不揣淺陋,擬對該書作一簡單評介,以就教于方家。
劉咸炘在文前指出:“既撰定《<后漢書>知意》,體例亦如前三書,唯是書意旨更少,可說不及前三書之詳耳,近人申雪承祚多為曲說,今悉一一辯證之。”簡言之,就是說清代一些學(xué)者在《三國志》的研究上犯了很多學(xué)術(shù)錯誤,需要當(dāng)代學(xué)人悉心考證。劉咸炘不僅認(rèn)為“自朱元晦沿習(xí)鑿齒之論,正成承祚帝魏之失,儒者相沿譏”,而且“自朱彝尊《陳壽論》、何焯《讀書記》后,此學(xué)者益不喜宋儒”。關(guān)于這些問題,劉咸炘并沒有追隨當(dāng)時學(xué)界大流,在他眼里“壽自有不忘舊國之心,而非有魏邪漢正之見,雖小例不以蜀劑吳,而大體帝魏自不可掩”。劉咸炘認(rèn)為《三國志》雖未尊蜀,亦未尊魏,“且承祚雖以《三國志》名統(tǒng)三書,而三書之中未嘗不有主從之別”。
以此為突破口,劉咸炘列出《三國志》中四個方面的問題,并一一進(jìn)行論證。“一則魏稱紀(jì)而吳、蜀僅為傳也。”他指出尚镕“承祚之紀(jì)操非猶史遷之紀(jì)羽乎”中存在的錯誤,認(rèn)為:“尚氏所引又有謬者,項(xiàng)羽紀(jì)未用漢年,太史之紀(jì)項(xiàng)羽乃通史之等觀,承祚之紀(jì)操乃斷代之追溯,亦不可混為一談也。”其二,“稱漢為蜀,直以地名事其為偏方,而不用本名,以敵魏也”,劉咸炘認(rèn)為“魏稱受禪于漢,自不容更有漢,指西為蜀”。劉氏以敏銳的目光捕捉到陳壽著書的心理,因?yàn)闀x承魏必不會容漢,承祚又是依時人之意,并不是陳壽有心貶抑。其三,“以《二牧傳》列《蜀志》之首,示其為偏方也。”劉咸炘認(rèn)為凡是斷代史皆列所因所勝,或在列傳之首,并未冠于帝王之前,從而批評何焯“二牧不從董、袁群雄之例”的觀點(diǎn)。其四,“蜀、吳二書,書法皆不與魏為敵國之詞也。”劉咸炘站在先輩趙翼的角度,同時大篇幅引用《廿二史札記》中有關(guān)《三國志》的內(nèi)容,以進(jìn)一步批判尚镕“魏文、明諸記不書蜀,吳二主即位及沒,不以魏統(tǒng)蜀、吳也”的觀點(diǎn),并舉例加以證明,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劉氏認(rèn)為以上所列四則理由“實(shí)紼相因”,既然當(dāng)中以魏為紀(jì),所以應(yīng)該稱漢為蜀,列《二牧傳》于《二主傳》之前,并且史為一書的綱領(lǐng),不能容有兩紀(jì),以史紀(jì)實(shí)是大勢所趨。劉咸炘說道:“后世乃以紀(jì)與否為褒貶,以立紀(jì)為承認(rèn)其正統(tǒng),而所謂正統(tǒng)之辯乃由是紛然。”這種見地非一般學(xué)者能有,劉氏的史學(xué)研究與史學(xué)評論是極負(fù)責(zé)任的,他認(rèn)為研究前人的成果要站在客觀的角度與立場,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及“疑古”的習(xí)慣。
劉咸炘《<三國志>知意》中有諸多值得我們當(dāng)代學(xué)子學(xué)習(xí)的地方。首先,我認(rèn)為該書文約義豐,字字珠璣。劉氏在分析陳壽《三國志》中有沒有“貶蜀尊魏”這一問題時,就用“古人樸直,不以名亂實(shí)”表達(dá)了自己的觀點(diǎn),一目了然;“古人”應(yīng)是指當(dāng)時的治史之人,樸直的含義應(yīng)該是治史者考證要有真憑實(shí)據(jù),要保持一個治史者的歷史責(zé)任感。其次,治史的嚴(yán)謹(jǐn)與“史德”。為論證張照因《三國志》版本知識的缺乏而造成的著述錯誤,劉咸炘廣泛查閱唐宋時期的相關(guān)史料對此進(jìn)行反駁:“古書每篇皆有書目,是為小題,書寫之式在頁首,唐前書皆如是,宋世刻本或妄移之。”劉咸炘是目錄學(xué)、校勘學(xué)大師,他為了證明自己發(fā)現(xiàn)的問題而大量查閱原始史料,這種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是我們學(xué)習(xí)的榜樣。再次,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上,要以事實(shí)為依據(jù),保持客觀的態(tài)度,不夾雜過多個人看法。由于陳壽是譙周的學(xué)生,學(xué)者們批判譙周是勸降后主的始作俑者,指斥其為“無心之人”、“駑臣”,王夫之曾曰:“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而解散人心,實(shí)在可惡。”陳壽在書中也有著明顯貶低諸葛亮的話語,因而兩人都受到不少批判。劉咸炘并沒有人云亦云,他認(rèn)為評價歷史人物應(yīng)當(dāng)實(shí)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史學(xué)研究不能脫離當(dāng)時的歷史環(huán)境。
劉咸炘在書中還將《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后漢書》進(jìn)行了明確比較。“承祚之于史有才學(xué),而己見識頗淺,非特不及馬、班,且視蔚宗猶遜,”他認(rèn)為過去學(xué)者評論古人言論多沿習(xí)班超寫書之體例,褒多貶少,鮮有自己的觀點(diǎn)。劉咸炘指出:“承祚誠善敘事,然其佳乃在遣詞,而非去取,每載問答恢嘲之瑣言,稱謂冗雜書人字而不名。”可見陳壽著述之中有諸多欠缺,《三國志》一書并非完美,承祚雖然長于敘事,史學(xué)去取略顯不足,劉氏告誡做學(xué)問之人一定要遍觀其書,不能人云亦云。
總而言之,劉咸炘的一些治史經(jīng)驗(yàn)、治史方法與史學(xué)觀點(diǎn)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他的著作也應(yīng)得到史學(xué)研究者們更多的重視,這對于進(jìn)一步推動《三國志》的研究起著重要作用。
李嘉悅(1996-),女,四川綿陽人,西華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秦平(1992-),男,湖南零陵人,西華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K092
A
1672-5832(2016)12-003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