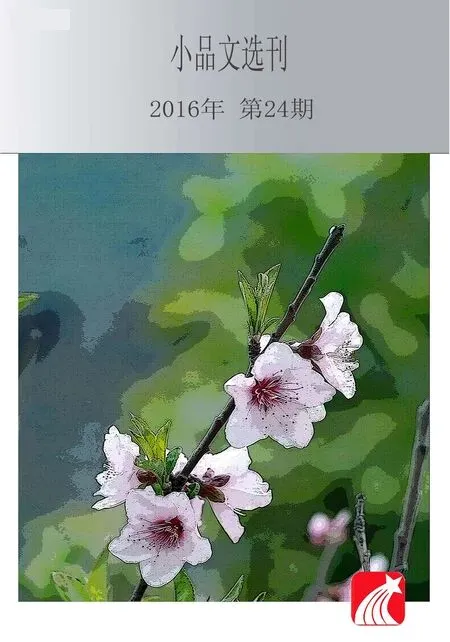《塵埃落地》與《八月之光》的文化語境解讀
劉琳瑜
(西安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00)
《塵埃落地》與《八月之光》的文化語境解讀
劉琳瑜
(西安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00)
文學經典的產生離不開文化語境,文化語境對作者的創作具有深刻的影響。要想充分理解文學作品的內涵與意義,就需要將文本置于作者所處的文化背景當中去。通過對《塵埃落定》與《八月之光》的文化語境的解讀,除了能夠深刻地認識兩部作品的文化內涵,還能夠理解兩位作者的思想觀念以及創作原則。
文化語境;福克納;阿來
文學作品的創作離不開歷史文化語境,作家創作的文化語境是指作家從事文學活動期間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具體的文化環境。巴赫金認為文學史一種社會審美文化現象,他主張詩學研究應當從文學內部結構入手,從文學體裁和形式切入,但又不應脫離社會歷史語境和文化語境。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說道:“偉大的小說家們都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人們可以從中看出這一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從它的自我連貫的可理解性來說它又是一個與經驗世界不同的獨特世界。又是,它是一個可以從地球的某區域中指劃出來的世界,如特羅普斯筆下的州縣和教堂城鎮,哈代筆下的維克斯等。”
福克納與阿來二位的創作語境一直都是研究的焦點,這是因為兩位作家的作品都深深根植于自己的故鄉。福克納以自己的家鄉密西西比州拉法耶特縣為背景,虛構了約克納帕塔法縣和杰弗生鎮,他的作品基本都圍繞著這兩個地方展開,福克納一共創作了17部長篇小說,除了《寓言》,他的其他作品都屬于“約克納帕塔法體系”。阿來出生在四川省西北部藏區馬爾康縣的一個藏族村寨,他的《空山》、《格薩爾王傳》以及《塵埃落定》等作品都以自己的家鄉馬爾康縣為背景。阿來與福克納的文學創作所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于特定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等。
1 《八月之光》中的文化語境
福克納在自己家鄉度過了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光,并以自己的家鄉小鎮為原型虛構出約克納帕塔法縣,創造出了屬于自己的南方藝術王國。福克納曾在接受采訪時說道:“我發現我自己的那像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是最值得書寫的……它向我打開了一座埋藏著豐富人性的金礦,我用它創造了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宇宙。”作為一名南方作家,福克納在《八月之光》中對種族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通過講述莉娜、克里斯莫斯、海托華三個人的故事,福克納揭示了南方種族隔離的罪惡。通過克里斯莫斯與莉娜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對比,福克納表達出自己南方社會兩種截然不同的感情。正如戴維·敏特所指出的,福克納生活在兩個世界里,一個是他想象的世界,另一個是他生活其中而有永遠無法改變的家鄉地區。首先,克里斯莫斯是一個深受種族主義和清教主義雙重迫害的人。這兩個問題一直深深根植于南方社會,雖然南北戰爭廢除了奴隸制,但黑人實際上并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利。清教主義控制著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而且清教主義還從神學角度支撐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隔離政策,以上種種社會現實都通過克里斯莫斯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來。
同克里斯莫斯的命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莉娜·格羅夫這一人物形象,莉娜未婚先孕,獨自一人離開家鄉來到杰弗生鎮尋找自己的愛人。在思想觀念如此保守的美國舊南方社會,莉娜卻得到了杰弗生鎮的人們的幫助,她對待命運的態度也顯得平靜與超然。這兩個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克里斯莫斯的悲慘命運揭示了南方社會的罪惡與丑陋,而莉娜卻代表著南方人民所擁有的勤勞、勇敢、堅韌、富有愛心的高尚品質。福克納通過這兩個人物形象表達出了自己對南方社會的復雜情感。福克納所處的時代,南方社會正走向衰落,南北戰爭的失敗,再加上北方資本主義工商業對南方傳統種植園經濟和價值觀念的沖擊,福克納就處在這樣一個充滿矛盾、新舊思想交替的社會中。福克納描寫克里斯莫斯的殘忍與冷漠,以此來揭露南方社會的罪惡與黑暗。然而,正如福克納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的演講中所說到的,“我相信人類不僅能延續,而且能戰勝一切而永存。他是不朽的,不是因為生物鐘唯有他的聲音永不衰竭,而是因為他有靈魂,有能同情能犧牲能忍耐的心靈。”
2 《塵埃落定》的文化語境
阿來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這是一個漢藏羌等多個民族的聚居地,這種多元的文化背景對阿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阿來的家鄉并不處于藏文化的中心地帶,同時,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又處于漢文化圈的邊緣,又受到漢文化的浸染。處于這樣一種文化地帶,人們很容易產生一種中心疏離感和孤獨感。阿來是熱愛西藏的,他說:“我寫《塵埃落定》、寫《格薩爾王》就是要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西藏,要讓大家對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達拉宮,還要能讀懂西藏人的眼神。”同福克納一樣,阿來也在自己的作品當中虛構出一個神秘龐大的康巴土司家族,《塵埃落定》以傻子二少爺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家族的興衰史。雖然阿來并未大量描繪自己對故鄉的喜愛之情,但他用了大量的筆墨來講述藏區的文化和風景。例如在第十章鐘,作者寫道:”這年的春天來得快,天上的風向一轉,就兩三天的時間吧,河邊的柳枝就開始變青了。又過了兩三天,山前、溝邊的野桃花酒熱熱鬧鬧地開放了。短短幾天的時間,空氣里的塵土就叫芬芳的水氣壓下去了。”然而阿來筆下的這片土地卻被等級森嚴的土司制度所統治,人性卑劣的一面也暴露出來,因此這種野蠻和落伍的制度終將走向滅亡。
在《塵埃落定》中,濟嘎活佛和門巴喇嘛身上宗教原本的莊嚴和神圣都受到了褻瀆,宗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被卷入了權力的混戰,濟嘎活佛和門巴喇嘛為了爭得麥其土司的賞識,想方設法諂媚惑主。在當時那樣一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波翁意西卻堅守了自己信仰,由于自己的坦誠和執著,先后兩次被麥其土司割去了舌頭,他未能成功地傳播新的教義,似乎藏傳佛教文化也隨著土司制度的崩潰那樣塵埃落定了。黃特派員為麥其土司帶來了現代軍隊,幫助麥其土司鞏固政權,同時也帶來了罪惡之源—罌粟。這種外來文化的突然入侵,破壞了這個家族原本應有的秩序。麥其家族開始發動更多的戰爭,掠奪更多的財富。所謂的現代文明沖擊著這個古老的藏區,然而以罌粟花為代表的所謂的文明實際上卻比土司制度更加野蠻。《塵埃落定》中的麥其土司、土司太太、以及大少爺都在權利和欲望中迷失了自我,喪失了人性。作為一個出生在文化邊緣地帶的人,阿來很渴望自己的民族文化能夠得到認同,盡管小說的最后麥其家族最后被時代吞沒,但進步、發展的過程韌勁造成了原有文化、秩序以及信仰的改變甚至是缺失。
通過考察《八月之光》與《塵埃落定》的文化語境,可以看出福克納與阿來的作品都包含著兩位作者對人性的關注和對時代的思考。
[1] 陳思廣.阿來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p119
[2] 陶潔.福克納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p65
[3] 威廉·福克納.八月之光,譯林出版社,p91
[4] 阿來.塵埃落定,人民文學出版社,p55
劉琳瑜(1992—),女,漢族,陜西安康人,碩士,西安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中西文化對比。
I207.42
A
1672-5832(2016)12-00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