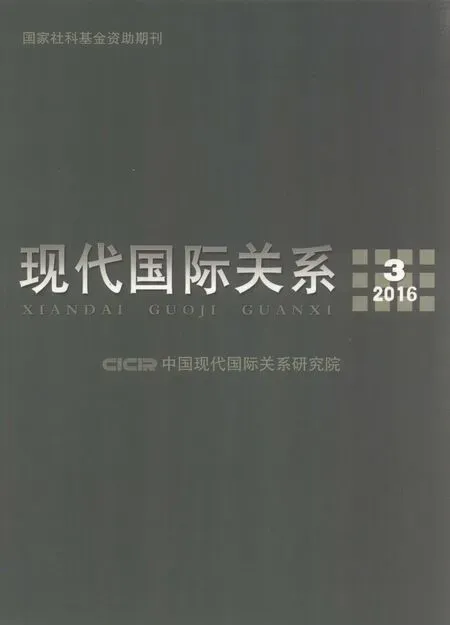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社會組織風險及對策
孫海泳
?
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社會組織風險及對策
孫海泳
[內容提要]近年來,隨著中國對海外能源及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東道國的社會組織風險對投資項目造成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社會組織風險緣于東道國內政、社會組織的環保和維權訴求、外部勢力的影響以及中國企業自身不足等因素,不僅會造成投資損失,還會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實施及國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中國企業需通過強化項目前期準備、重視與當地社會組織的溝通等方式,保障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與對外經濟戰略的穩步推進。
中國 對外基礎設施投資 社會組織風險 “走出去”戰略
[作者介紹]孫海泳,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在站博士后,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美國問題、對外投資問題等。
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重要途徑。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對外投資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特別是近年來,伴隨著“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企業加大了對海外大型能源及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規模。此類投資項目資金投入大、建設周期長、社會影響深遠且易受對象國政治、法律與政策因素的影響,因此相關投資項目往往面臨諸多風險因素的制約。其中,各類社會組織基于環保訴求、群體利益等因素對中國企業投資項目的制約效應日益凸顯。因此需要分析中國企業投資海外基礎設施項目所面臨的社會組織風險的原因及影響,并探尋應對之策。
社會組織日益成為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環境的重要因素
對外投資中的風險可分為商業性風險和非商業性風險。非商業性風險主要包括政治、安全、法律、環境與社會風險。社會組織的訴求與相關活動會直接引發社會風險,并可能間接產生政治、安全等類型的風險,最終導致企業投資失利或產生額外損失。本文研究的社會組織風險主要是指中國在投資海外基礎設施類項目時,因對象國環保、原住民權益、勞工權益等問題,導致當地及境外社會組織對項目的施工、運營所造成的風險因素。
社會組織在不同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中存在不同的稱謂。*中國國內將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統稱為社會組織。國際上對社會組織的提法較常見的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志愿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地方性或草根社會組織(Local or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LOs)、社區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以及部分獨立性智庫和非盈利基金會等機構。本文以“社會組織”統稱上述機構。雖然這些名稱在具體內涵方面存在一定差別,但與政府、企業相區別,不同名稱的社會組織均具有非政府性、非營利性、獨立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從20世紀80年代起,非政府組織(NGO)開始進入發展的快車道,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后,NGO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崛起,各類NGO從事提供公共服務、促進民間經濟發展、防止環境退化等此前無人負責或由政府負責的大量事務;其參與公共事務的范圍之廣、規模之大,使得人類社會正處于“社團革命”之中,有人甚至認為其意義之重要堪比19世紀民族國家的崛起。*Lester M. Salamon, “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994-07-01/rise-nonprofit-sector. (上網時間:2016年1月26日)自21世紀初以來,社會組織已成為許多國家國內議程和全球議程的重要參與者。在組織理念上,NGO一般都宣稱以促進人道主義及為弱勢群體代言為己任;通過自身網絡,NGO能相互聯絡并協調共同立場;通過從事一系列的倡議和游說活動,NGO能夠影響主權國家政府以及諸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等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議程和決策。*Hans Holmén and Magnus Jirstr?m, “Look Who’s Talking! Second Thoughts about NGOs as Representing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Vol. 44(4), 2009, pp.429-430.
在此背景下,企業在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僅和東道國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并不能確保投資項目獲得成功,因為企業的營運經常會受到環保類NGO(簡稱環保組織)、人權類NGO(簡稱人權組織)、社區組織等不同種類的社會組織的影響,這些社會組織維護或代表地方、國家乃至全球等不同層次的利益訴求。因此,企業對外投資的商業環境主要包括三個要素,即企業、社會組織和東道國政府。*Mika Skippari and Kalle Pajunen, “MNE-NGO-Host Govern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Escalation of an FDI Conflict”, Business &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Vol.49(4), 2010, p.620.其中,社會組織已經成為推動跨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壓力來源。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環境與發展智庫——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認為,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控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獲取社區同意,即遵循“自由、事前和知情同意的原則”。單純依靠所在國政府來處理環境與社會風險是不可靠的。政府往往無法調節投資者和當地居民的關系,且政府的職能本應代表和保護本國國民,而非代表外國投資者利益。在出現問題時,政府迫于國內壓力,往往會向外國投資者施壓,要求賠償甚至終止投資項目。*胡濤、趙穎臻、周李煥、Denise Leung: “對外投資中的環境與社會影響案例研究:國際經驗與教訓”,世界資源研究所(WRI),http://www.wri.org/sites/default/files/managing_environmental_impact_international_experience_and_lessons_in_risk_management_for_overseas_investments.pdf. (上網時間:2016年1月2日)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地方性或草根社會組織對于大型公共工程和地區經濟發展議程的影響日益明顯。草根組織(grassroots organizations)與 NGO有所區別。草根組織通常基于成員的訴求而建立,關注社區事務與可獲利項目,而NGO往往更強調公益性,并設法影響公共政策。同時,在發展中國家,草根組織一般存在于農村地區,而NGO多以城市為重點活動區域并與發達國家的NGO存在一定淵源;草根組織開展活動的受益人是其成員,而NGO行動的受益人是其委托方或幫助對象;草根組織缺乏對政府的影響力,一般規模小而分散、缺乏專業能力、難以持續運行。*Hans Holmén and Magnus Jirstr?m, “Look Who’s Talking! Second Thoughts about NGOs as Representing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Vol. 44(4), 2009, pp.431,433.這類草根組織往往成為企業對外投資時直接面臨的風險來源。
在國家類型和地理分布上,中國企業對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所面臨的社會風險主要來自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一些迫切需要改善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擁有較為豐富且具有商業開采價值的自然資源,但其政治、經濟局勢動蕩,外國投資企業,特別是涉及資源開發、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企業往往成為各種勢力解決其內部矛盾、與政府博弈、吸引國際關注的工具。第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貧窮落后、環境惡化和民族宗教矛盾等問題,均給西方大國利用社會組織等途徑影響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動力、借口和活動領域。*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課題組:《外國非政府組織概況》,時事出版社,2010年,第213頁。第三,許多發展中國家環境社會標準較低或缺失,且政府并不鼓勵投資企業與社區溝通,導致一些問題在初期往往難以被及時發現和應對,一旦爆發就已相當嚴重。*蔣姮:“海外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應對盲區及誤區”,載于査道炯、李福勝、蔣姮主編:《中國境外投資環境與社會風險案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5頁。
中國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面臨社會組織風險的主要原因
能源、交通基礎設施項目不僅將對自然環境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往往涉及土地征用,還可能涉及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居民遷移以及勞工權益等問題。特別是在東道國國內政治轉型期間,政治與社會形勢復雜,更易導致社會組織風險不斷積累和快速發酵。綜觀近年來中國的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遇挫歷程,其社會組織風險主要緣于以下五方面。
第一,東道國國內政治因素。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處于政治轉型過程之中,其政治生態與社會利益日趨多元化、復雜化,加之西方國家的影響和滲透,其國內社會組織迅速發展。以緬甸為例,2010年大選之后,緬甸由軍人政權轉型為民選政府,國內的公民社會空間進一步開放,社會組織的數量、活動人數不斷增加,其活動范圍亦不斷拓展,一些非政府組織還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和復雜的政治背景。這些社會組織往往對中國的大型投資項目進行歪曲評價和不實指責。如“克欽發展網絡集團”(Kachin Development Networking Group, KDNG)是由緬甸國內外克欽族人組成的非政府組織,其聲稱的目標是“推動在克欽地區構建基于平等和正義的公民社會”,關注“緬甸軍政府對克欽地區自然資源的開發”,“收集包括地區礦業、水電等大型發展項目的信息”;“與地區社會組織一起評估村民需要和地區性發展措施”;該組織還致力于緬甸的司法與社會改革,參與包括克欽邦在內的緬甸的政治變革進程等政治與社會事務。*Kachin Development Networking Group, http://www.kdng.org/about.html. (上網時間:2016年1月24日)該組織與緬甸其他具有明顯政治背景的社會組織一起,發動基層民眾,反對中國投資的密松(Myitsone)水電站等項目,成為緬甸政府暫停該項目的重要原因。同時,東道國國內政治選舉等事態也會導致社會組織的訴求成為阻滯外部投資項目的重大風險因素。如中遠集團(COSCO)在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項目中所遭遇的波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希臘在野黨迎合選民(工會組織)意愿的選舉政治的影響。*2008年,中遠集團在比雷埃夫斯港(以下簡稱比港)集裝箱碼頭私有化招標中中標,獲該碼頭35年的特許經營權。在薩馬拉斯(Antonis Samaras)任希臘總理期間,比港嘗試出售67%的股權,中遠是重要的潛在買家。期間,希臘工會組織批評中遠規定的所謂“中世紀勞動條件”缺乏公平性和社會責任,反對向中企出售港口控股權。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提出“戰略性國有資產”不會被私有化等政治主張以迎合民意,并在一定程度上由此獲得選舉勝利。2015年1月27日,新政府就職當天即暫停比港私有化計劃。但出于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在2015年9月的大選中再次當選后,齊普拉斯政府放棄原有立場。2016年1月,希臘政府批準中遠購買比港67%股權的計劃。
第二,環保因素。完善基礎設施條件是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在項目建設及運營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給生態環境與當地居民生活帶來一定影響。在環保組織等相關社會組織的影響下,全球范圍內的許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水電站、油氣管道、鐵路等項目的建設進程往往面臨諸多障礙,甚至因環保壓力而導致項目進展不順利。其中,水電及水壩項目面臨的環保爭議最為尖銳。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基本是以承包商的身份參與國際水電開發項目,但近10年來中國企業先后在東南亞等地開展水電與水壩項目投資;中國的建工企業和融資機構參與了世界在建水壩項目的75%,其中大部分涉及水電項目。*Tao Hu and Yiting Wa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orld Wildlife Fund, July 20, 2015, p.3, http://www.wwfchina.org/content/press/publication/2015/Yale-WWF_final.pdf. (上網時間:2016年1月19日)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推進,在強大的資金支持下,中國企業已經成為全球水電站建設的主力軍。中國在參建或發起建設全球巨型水壩的同時,也將自身推入環保主義者詰難的漩渦。*李福勝:“中國境外水電工程的環境與社會影響風險”,載于査道炯、李福勝、蔣姮主編:《中國境外投資環境與社會風險案例研究》,2014年,第197頁。以密松水電站項目為例,從該項目啟動之日起,當地的社會組織就強烈反對大壩項目。該項目的主要反對聲音來自于緬甸國內的NGO,包括“生物多樣性與自然保護協會”(BANCA)、“克欽發展網絡集團”、“克欽新聞組”(Kachin News Group)等。*Hu Tao, Chen Min, Wu Yanyang, “Analysis of Key Players i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atrix”, In Tao Hu and Yiting Wa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World Wildlife Fund, July 20, 2015, pp.96,102, http://www.wwfchina.org/content/press/publication/2015/Yale-WWF_final.pdf.(上網時間:2016年1月19日)同時,緬甸境外的NGO也對密松項目的中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成立于2007年、總部位于泰國清邁的“緬甸河流網”(Burma Rivers Network)一直以水電項目破壞環境等為由,反對密松項目,并認為中國對緬甸水電產業的巨大投資擴大了緬甸政府與地方勢力的隔閡。*Jonathan Watts, “Aung San Suu Kyi: China’s Dam Project in Burma is Dangerous and Divisive”, August 12,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1/aug/12/suukyi-china-dam-irrawaddy-conflict. (上網時間:2016年1月6日)此外,中國在海外投資的油氣管道、鐵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也往往面臨巨大的環保壓力,而環保組織等社會組織的介入則會進一步增大項目推進的風險。
第三,原住民群體或人權組織的“維權”訴求。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重新安置當地居民,或征用農地和森林等問題,結果可能影響個體土地所有者或社區的公共利益。在此背景下,相關維權訴求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項目啟動或建成后,當地居民遷移后可能失去賴以生存的經濟資源。這是大型項目面臨的普遍問題,當然中國企業會在經濟補償、提供就業機會等方面做出相應安排。二是東道國中央政府與項目所在地就項目收益的分配所產生的矛盾,會導致相關社會組織抵制項目開發。如密松水電項目的中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克欽獨立組織對項目收益分配的不滿。三是境內外人權組織的干預。如埃塞俄比亞的吉布3號大壩(Gibe III Dam)項目總投資約17.5億美元,于2008年開工建設。中國工商銀行為該項目提供了部分融資。該電站建于肯尼亞北部圖爾卡納湖(Lake Turkana)的生命線——奧姆河(Omo River)上。專事保護原住民生存環境的非政府組織“國際生存者”(Survival International)認為,大壩將破壞雨季和旱季周期,可能導致湖水鹽度增加,由此在電站建成后,河谷8個族群的20萬居民及牲畜將因失去飲用水源而被迫離開家園。*“The Omo Valley Tribes”, http://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tribes/omovalley/gibedam.( 上網時間:2016年1月5日)“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也發表報告,批評埃塞俄比亞軍方強制搬遷村民,導致村民失去生計來源而被迫接受大壩項目。*“Human Rights Watch Letter to 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 on South Omo”, November 16, 2011, In “What Will Happen if Hunger Comes?”- Abuses agains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Ethiopia’s Lower Omo Valley, June 2012, p.77,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ethiopia0612webwcover.pdf. (上網時間:2016年1月2日)人權組織及環保組織的反對在很大程度上遲滯了項目工期,使得該電站直至2015年10月才開始發電。而在中緬油氣管道項目的建設過程中,“瑞區天然氣運動”(Shwe Gas Movement)、“國際地球權益組織”(Earth Right International)等緬甸境內外社會組織曾多次發布報告,指責該管道項目在征地、環境、強制移民和勞役方面損害了民眾權益。2012年3月初,來自20多個國家的130多個社會組織在緬舉行示威,并向緬甸領導人吳登盛遞交公開信,以人權問題及社會、經濟及環境影響為由,要求推遲中緬油氣管道項目的建設。*“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hein Sein: Postpone destructive Chinese pipelines in Burma”, Worldwide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January 3, 2012, https://www.fidh.org/en/region/asia/burma/Open-letter-to-President-Thein. (上網時間:2016年1月22日)社會組織反對中緬油氣管道項目,以及可能由此引發的政治風險,對作為投資與運營方的中石油(CNPC)形成巨大壓力。
第四,外部勢力的介入及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與渲染。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外基礎設施類投資增速下降,而中國此類投資的增速大幅上升,這體現了中國經濟實力的相對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固有的戰略思維,明里暗里干擾中國的對外投資進程,其NGO和媒體亦對中國對外投資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大加渲染和毀謗。
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多種渠道資助、支持相關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對中國的海外利益拓展形成制約。如致力于反對中緬油氣管道等中緬合作項目的社會組織“瑞區天然氣運動”,即是由曾在泰國等國流亡的緬甸流亡人士組成并回到緬甸發展重組,“美國之音”、路透社、《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都曾為該組織的活動做宣傳。*“Rights Groups Call for China to Halt Construction of Pipeline in Burma”, November 11, 2009,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a-13-2009-10-28-voa14-69781572/367533.html;“RPT-China pipelines threaten Myanmar economic security-NGO”, September 6, 2011,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myanmar-china-pipelines-idUSL3E7K51NN20110906; Jane Perlez and Bree Feng, “China Tries to Improve Image in a Changing Myanmar”, May 18,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5/19/world/asia/under-pressure-china-measures-its-impact-in-myanmar.html?_r=0. (上網時間:2016年1月5日)緬甸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且處于政治轉型進程之中,而這主要是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正因為此,中國在緬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社會組織風險才會頻繁出現。另一方面,西方媒體對中國對外投資政策及項目狀況進行片面報道,“抹黑”中國的對外投資活動。如中國已不斷完善綠色信貸政策,而且中國金融機構也努力促進與之合作的企業在項目建設與運營過程中消減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但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媒體對此往往極少關注與報道,*Richard L. Harris ,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A Peaceful Panda Bear instead of a Roaring Drago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ssue 205, Vol.42,No. 6, November 2015, p.158.而是突出報道或渲染中國對外投資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如西方主流媒體對厄瓜多爾科卡科多—辛克雷(Coca Codo Sinclair)水電站項目的報道即是一例。*科卡科多-辛克雷水電站項目位于厄瓜多爾的納波(Napo)和蘇昆比奧斯(Sucumbios)省境內。2009年10月,中國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厄瓜多爾科卡科多-辛克雷公司正式簽署水電站工程總承包合同,金額為23億美元。該電站總裝機容量為150萬千瓦,年發電量88億千瓦時,建成后將滿足厄瓜多爾全國1/3人口的電力需求。參見“厄瓜多爾科卡科多-辛克雷水電站工程”,中國水利水電第十工程有限公司三分局網站,2012年12月18日,http://3fj.10j.sinohydro.com/shownews.asp?Id=592. (上網時間:2016年1月19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該項目提供大部分融資,這也是中國在拉丁美洲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壩。《紐約時報》批評該水電項目會對當地環境造成嚴重影響,還強調該項目的厄瓜多爾工人時常就其工資、醫療、飲食及工作條件提出抗議,并借當地員工之口指責“中國人傲慢、態度粗魯”及“員工薪資不高、工作條件惡劣”等。*國際河流組織:“中國介入拉丁美洲的大壩項目”,《國際河流簡報》, 2010年3月,第5頁,https://www.internationalrivers.org/files/attached-files/worldriversbulletin0310.pdf; Clifford Krauss, Keith Bradsher: “中國輸出貸款和工程改變世界格局”,《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7月22日,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50722/c22chinalend/. (上網時間:2016年1月19日)類似報道不勝枚舉,對中國海外大型投資項目的國際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第五,中國企業自身原因。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由于自身局限也會引起當地社會組織的批評和抵制。中國企業過于依賴于東道國政府協作,在項目評估、征地拆遷等環節與當地社會組織及媒體的溝通與協作不足。同時,中國投資海外基礎設施項目的企業以包括央企在內的國企為主,雖然央企或大型國企在資金實力、施工技術、專業人才、國際市場經驗與知名度等方面具有優勢,但其政府背景不可避免地引發外界對企業投資意圖的臆測,甚至會招致不實指責。由此,包括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在內的中國對外大型投資項目,往往成為西方國家所謂“中國威脅論”、“新殖民主義論”的重要素材,并被大加利用以影響東道國的輿情民意,進而滋生中國大型投資項目的社會組織風險。
社會組織風險對中國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影響
社會組織因素有可能引發政治、社會甚至安全等風險,并可能最終造成企業的經營損失。能源與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屬于資本密集型投資,項目前期的資金投入規模巨大,一旦項目停滯或夭折,將會帶來巨大損失。不僅如此,如因社會組織因素導致社會與政治風險,將會遲滯中國對外經濟戰略,還有可能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首先,導致中國部分對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夭折或延擱,并由此造成項目投資方前期投入資金無法回收及資金使用成本等損失,以及東道國政府的就業機會、稅收等方面的損失。以密松水電站項目為例,該項目的暫停使中緬都遭受了巨大損失。主要投資方“中電投”前期投資達70億元人民幣,資金成本等費用將每年增加3億元;公司還面臨供應商、施工單位等合同方的巨額違約索賠。而緬方損失亦相當嚴重。第一,密松項目的停工使得當地損失了3萬人參與項目施工的就業機會,導致許多移民生計無著。第二,外商對緬投資信心受創。緬甸外商投資由2010至2011財年的200億美元陡降至2012至2013財年的14.9億美元。第三,經濟增長受挫。密松水電站每停建一年,緬國內生產總值將損失50億美元,約占2013年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8。*“密松水電站停工 中緬兩敗俱傷”, http://www.zgdlxw.com/html/xinwenzhongxin/shichang/20140110/28206.html.(上網時間:2016年1月19日)
其次,通過干擾中國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推進,在一定程度上會對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產能合作進程造成阻礙,從而遲滯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實施進程。如緬甸是中國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國家,中國在緬甸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進展,將直接影響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海上絲綢之路乃至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順利實施。緬甸社會組織對中國投資的水電站、油氣管道、鐵路等大型基建項目的干擾,已經并將繼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這些項目的實施進度,由此掣肘中國在印度洋及東南亞方向的戰略拓展步伐。而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區國家的社會組織風險,也將對中國與地區國家之間產能等諸方面經濟與戰略合作進程造成負面影響。
再次,國外社會組織對中國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批評、抵制還會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造成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社會組織尤其是草根組織往往與其活動區域的民眾存在緊密聯系。一旦社會組織對投資項目的抗議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礎,則不僅會影響項目的推進,而且經由媒體的傳播,特別是西方主流媒體的渲染,在很大程度上將催發與中國有關的所謂“新殖民主義”等不實論調,并將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某些社會組織甚至會利用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作為發聲平臺,抵制一國的公共工程計劃,由此會給投資方和東道國的國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如巴西原住民社群領導人曾于2015年6月在日內瓦的第29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講話,批評巴西政府在建設貝羅蒙特(Belo Monte)水電站前未與受到影響的原住民團體協商,并認為此舉違反巴西憲法和國際法。*Bruce Douglas, “Brazilian Indigenous Leader to Address UN Council in Effort to Stop Dam”, The Guardia, June 24,2015.當前,中國正在參與橫貫亞馬遜雨林的巴西—秘魯“兩洋鐵路”的可行性論證,并有望為該項目提供融資。南美地區的許多大型公共工程都曾因環保、原住民權益等問題引發爭議甚至沖突,加之當地環保組織、相關原住民社群已開始關注巴西—秘魯“兩洋鐵路”項目,若該項目在開工前及建設期間遭遇相關社會組織的掣肘,不僅會增加項目本身的風險,而且可能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對策思考
當前,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進程正在全面推進,鑒于中國過去在東南亞、非洲和拉美等地區國家因應社會組織風險的教訓,未來中國企業、本土社會組織等相關方面需在投資項目的前期準備和建設進程中予以妥善應對,以保障項目的順利啟動和推進。
第一,海外基礎設施項目的社會組織風險主要產生于透明度、環保、居民或勞工權益、當地社群的利益訴求等問題,因此中資企業需強化對生態環境、人文特征、社區利益的綜合考量。一是企業在投資項目中除了要履行與東道國中央政府的協議,還需對項目所在地的社會與自然環境進行評估,要自覺采用高標準對投資項目進行環境評估,在項目選址、環評等方面多聽取當地專家的意見。要廣泛、詳盡、有效地評估投資項目的環保問題,并全面做好因環境問題可能引發的各種問題的預案,促進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的規范化,擴大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的透明度及公眾參與度等。二是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方面發達國家企業有許多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 如國外一些大型企業近年來開始實施“社區持股”措施,將待開發的投資項目至少1%的股權無償轉讓給周邊居民,該股權紅利每年劃入一個專門設立的“社區投資基金”賬戶。這種普惠于民的海外社會責任戰略無疑對海外投資項目的順利進行大有裨益。*李鋒:“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海外社會責任戰略”,《國際經濟合作》,2014 年,第6期,第36頁。這些舉措對于中資企業進一步完善社會責任措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第二,中國企業應強化與東道國環保組織、原住民團體等組織的溝通、協調工作,著力防范此類團體對項目的沖擊。一是宜在項目論證期間即與當地原住民和環保團體保持溝通,包括與對項目懷有敵意或將受到項目影響的社群進行深入溝通,摸清其具體的利益訴求,發現各方可能的共識。二是在與社會組織的溝通過程中,應強調項目對促進當地發展的積極意義,強化項目的環保措施;通過提升項目的透明度,不斷完善項目規劃的相關細節,以爭取社會組織的理解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環保組織并非一味地反對大型公共工程,而是更加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若能在大型公共工程的規劃和施工過程中,將項目的經濟價值和環保考量充分結合,有可能獲得許多環保組織的支持,至少可以減少來自環保組織的大量阻力。 第三,通過資金扶持、人才培養等措施,鼓勵中國本土社會組織“走出去”,為海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順利推進創造有利氛圍。目前國內已經或正在進行國際化的社會組織數量較為有限,且多數具有官方背景,如中國紅十字會、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和扶貧基金會等,其工作議題多集中于扶貧、醫療與教育項目,而較少關注到環境保護、社區發展和勞工權益等議題。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規模的擴大,顯示了本土社會組織“走出去”的必要性,并為之拓展活動空間創造了重要契機。在此過程中,中國需培養、發展本土社會組織,并鼓勵其“走出去”與外國社會組織對話、溝通,紓解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中面臨的社會風險。相關中資企業可設立用于鼓勵國內社會組織“走出去”的專項基金,搭建海外中資企業與中國社會組織的溝通交流的平臺,促進其形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使得中國本土社會組織在海外基建項目中發揮化解當地社會組織壓力、監督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及改進中國企業的行為等功能。同時,中國需完善社會組織從事海外業務的相關支持政策。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國門之后的活動規則,諸如物資出關、稅收減免、資金募集方式、在海外設立辦事處或分支機構的依據等都需要依照國內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但中國尚無關于社會組織參與對外事務的法律法規,這是中國社會組織普遍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中國社會組織可通過調查、咨詢等方式為海外中資企業提供各項關于社會責任的規范和建議,幫助其搭建履行社會責任的平臺。①楊義鳳:“中國NGO國際化的現狀、挑戰與對策”,《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3期,第78頁。
第四,充分利用當地社會資源尤其是媒體資源,降低項目的實施風險。中國企業與相關機構可借助東道國的智庫、媒體的力量,用當地語言講中國的故事,更好地宣傳中國投資項目及相關技術的可靠性、經濟性乃至環保性,以及投資項目對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同時中國企業也可以主動與媒體合作,通過媒體來加強項目信息的透明度,避免不必要的沖突,爭取當地居民和國際社會的理解。
鑒于在全球范圍內,社會組織在社會、經濟乃至政治議題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特別是投資于基礎設施等大型項目的過程中所面臨的社會組織風險因素將長期存在。隨著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日趨成熟、中國本土社會組織國際化程度逐漸上升以及中國對全球發展的促進作用日益增強,中國企業對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所面臨的社會組織風險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這些都將為中國的國際經濟戰略的實施、國家形象的提升乃至與各國關系的改善、深化創造有利條件。○
(責任編輯:王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