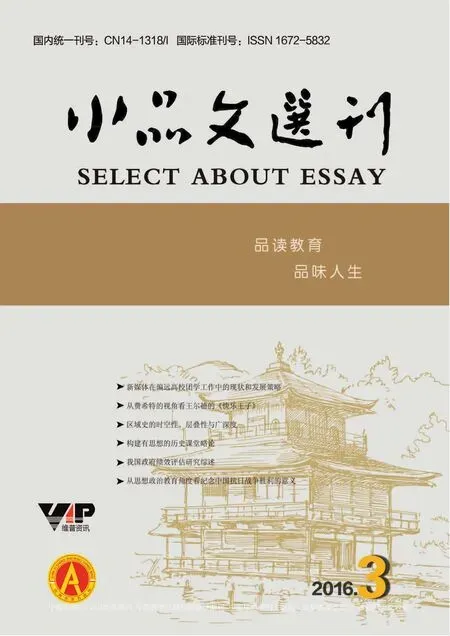海島帝國中“他者”的反抗
——以《暴風雨》中凱列班為例
張 穎
(寧波大學 浙江 寧波 315211)
海島帝國中“他者”的反抗
——以《暴風雨》中凱列班為例
張 穎
(寧波大學 浙江 寧波 315211)
本文通過細度《暴風雨》,從以賽義德為代表的后殖民批評理論的視角來研究普洛斯彼羅在海島上的帝國建構,并對凱列班的“他者”身份進行分析,重點討論凱列班作為“他者”形象的反抗精神和尋求自由之斗爭。以此警醒我們在世界一體化浪潮下,更要注重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保留與傳承,增強主體意識。
《暴風雨》;后殖民批評理論;凱列班;他者;反抗
1 引言
后殖民主義理論家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把文化看作舞臺,上面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勢力:“文化決非什么心平氣和、彬彬有禮、息事寧人的所在;毋寧把文化看作戰場,里面有各種力量嶄露頭角、針鋒相對”。(賽義德,18)因此對具體文本的分析不僅要關注主體的霸權行動,還要關注被客體化的“他者”的反抗。
米蘭國王普洛斯彼羅被野心勃勃的弟弟趕到了孤島上,接著他搖身一變,靠著書本里的魔法,掌控了島上的一切、奴役凱列班、掌控愛麗兒為他復仇。普洛斯彼羅的法力是殘酷的暴力,是殖民者的技術優勢的轉化。(Schmidgall ,88)同理,在米蘭王國的敗者在海島上可以成為一島之主,就是荷米·巴巴講的殖民文學中的“次品轉正”現象,即:“能力最低的白人也可以在殖民地有所作為,這是顯而易見的種族優越論。”(Homi K.Bhabha,30)
普洛斯彼羅能統治海島還因為海島文明的落后性。海島本是一個荒島,沒有政治、經濟現象。在普洛斯彼羅看來,接受他的統治是小島的最佳命運。海島真的一無所有、一文不值嗎?相反,它豐富的自然資源為他提供生存之本,為他的復仇奠定物質基礎,但普洛斯彼羅對海島不以為然。因為當時的歐洲人已經形成“世界在歐洲腳下”的觀念,他們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斯塔夫·里阿諾斯,565)
凱列班Caliban和單詞Cannibal很像,其源頭為吉普塞語Cauliban(黑色),他信仰塞提柏斯神(Setebos),“是南非土著居民崇拜的宗教偶像。”(華全坤,47)由此可以推定,凱列班是一個黑人、與歐洲人相對的“他者”。
米蘭達第一次見到腓迪南時說:“……這是我一生中所見的第三個人”。(莎士比亞,22)這三個人是普洛斯彼羅、凱列班和腓迪南。普洛斯彼羅也對米蘭達說:“……除了他和凱列班之外你不曾見過別人”。(莎士比亞,23)這里說明父女倆很清楚凱列班屬于人類。 另外,人與野獸的區別在于有自己的語言,凱列班有他自己的語言,所以他只能是人。
賽義德在《東方學》中有關于歐洲殖民者對“他者”形象的描述:野蠻、落后、腐朽。歐洲人扭曲“他者”形象的目的是要反襯自己的強大,保持自己的權威。《暴風雨》中普洛斯彼羅對凱列班異化、貶損的目的就是為了突出自己主人、統治者和殖民者的地位。潛意識里他承認凱列班人的身份,而這種潛意識恰恰是真實的;同時,他迫使凱列班放棄土語,逼迫凱列班成為他“沉默”的“屬下”。
雖然凱列班失去了一切,但他同時是有反抗精神的“他者”。他的反抗首先體現在語言上。凱列班在第 1 幕第就對普洛斯彼羅說:“這島是我老娘傳給我而被你奪了去。你剛來的時候……我把這島上的一切富源都指點給你知道……本來我可以自稱為王,現在卻要做你的唯一的奴仆。”(莎士比亞,18)在上述一段話中,凱列班一針見血地抨擊普洛斯彼羅,揭露了普洛斯彼羅殖民統治的本質。凱列班拒絕被奴役,他堅持認為自己同普洛斯彼羅德是平等的,他是海島真正的主人。
他還從行動上對普洛斯彼羅進行反抗。凱列班一直蓄意對普洛斯彼羅進行謀殺,當他遇見特林鳩羅等人時,他主動拜倒在他們的腳下“我要吻您的腳;我要發誓做您的仆人。”(莎士比亞,42)并許諾“我要指點您最好的泉水;我要給您摘漿果;我要給您捉魚;給您打很多的柴。”(莎士比亞,42)。即使謀殺未遂,凱列班也未真正的屈服,只是得到了更多的經驗和教訓:“從此以后我要聰明一些,學學討好的法子”。(莎士比亞,78)可見凱列班只是表面屈服了普洛斯彼羅,他內心深處從未喪失尋求自由的理想。
2 結論
普洛斯彼羅通過身為歐洲白人的身份、掌握當時歐洲先進的文明知識的優勢,占據海島,構建了他的海島帝國。但是,被奴役的凱列班,作為歐洲中心文化中的“他者”,即使在被剝奪了活動自由、信仰自由、語言文化自由的情況下,仍不甘心被白人驅使,想方設法為追尋自由、獨立而斗爭。對于我們當今啟示是,在世界一體化浪潮下,更要注重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保留與傳承,增強主體意識,不可迷失了自我。
[1] 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 Homi K.Bhabha,Signs Taken for Wonders, The Post Colonial Studies Reader[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29-35.
[3] 愛德華·賽義德. 《文化與帝國主義》[M]. 李琨譯, 北京:三聯書店. 2003.
[4] 華全坤,張浩. 《暴風雨》—莎士比亞后殖民解讀的一個個案[J]. 安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5).
[5] 斯塔夫·里阿諾斯.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M]. 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6] 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VIII》[M]. 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張穎,女,漢族,寧波大學。
I106
A
1672-5832(2016)03-023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