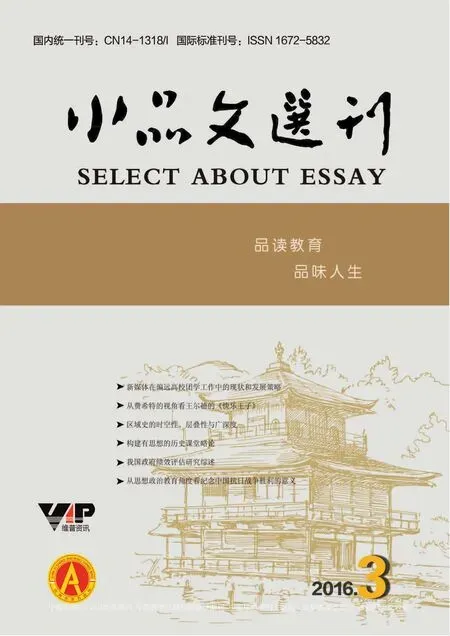學衡派的悲劇性命運
李 靜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學衡派的悲劇性命運
李 靜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學衡派作為五四時期的重要流派足可折射出新文化運動大潮中一批獨具人格魅力的知識分子群體形象,而吳宓作為貫穿學衡派發展始終的代表人物,又可反映學衡派這一同人團體的某些共生特色。以吳宓作為切入點,窺視學衡派在新舊文化沖擊的文化困境中展開身份追尋,卻又因執拗于“他者”視角展開而陷入自身發展的悲劇,然而學衡派依然在與新文化運動派的博弈中成為共生共長的重要力量。
吳宓;學衡派;身份追尋;悲劇性
學衡派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初重要的同人團體,以獨特的面貌出現在現代文學史上。學衡派以自己的方式在新文化運動中扮演著某種角色,主觀上作為新文化運動者的對立面存在,但在客觀上的確為新文化運動乃至其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帶來了豐富而復雜的影響。吳宓作為學衡派的關鍵人物,在梅光迪、胡先嘯等人紛紛退出《學衡》雜志編撰之后,仍然在苦撐學衡派,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從吳宓的身上,可以窺視以學衡為代表的一部分被冠以“文化保守主義”之名的知識分子如何在新舊文學交鋒的潮流中追尋身份特征,找到存在價值,并如何在新文學的浪潮中固守獨立的聲音,勇敢地承擔起現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責任。處于時代轉折點的學衡雜志極盡可能想要在受沖擊的傳統文化與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之間尋找到平衡點,力圖彌補根植于他們文化背景之中卻正在坍塌的古典文學大廈,然而學衡派一直試圖從他者的視域中追尋身份確證,這種志業和理想很快被殘酷的現狀批駁地體無完膚,伴隨著現實與想象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學衡派的身份追尋注定被涂抹上悲劇色彩,無論這種悲劇被解讀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不思進取的復古行為,還是被高歌為童話式的英雄悲劇,但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時代中的探索與追尋成為了不同文化群體參與文化建設浪潮中的獨特風景。
1922年1月,伴隨著《學衡》雜志的創辦,拉開了學衡派的序幕,隨即迎來了學衡派黃金時期。面對《學衡》掀起的反對聲浪,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如胡適、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都迅速地予以回擊。然而《學衡》創刊的第二年,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所發起的批評,很少能再引起新文化倡導者的回應。這一年,梅光迪因對《學衡》不滿,退出《學衡》,胡先嘯于是年秋再度赴美留學,主力干將與學衡派的距離越來越遠,學衡派的黃金時期落寞之后開始走上掙扎前行的衰落之路。就學衡派發展過程來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1922年以前為準備階段,1922年1月《學衡》創辦到1923年是學衡派發展的黃金時期,從1923年到1933年《學衡》雜志停刊是衰落時期。
1923年3月,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宣告:“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經破產了。”①這一聲吶喊預示了學衡派的輝煌時期已經逝去,在身份追尋的路上走向了強弩之末。如果說開始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尚能通過批判《學衡》來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而后來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熱烈地開展起來,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自信的勝利者姿態,使他們認為不再有與“學衡派”論爭的必要。來自對手的冷漠,使得“學衡派”通過《學衡》所發出的聲音,漸漸變成一種無謂的“獨白”,這樣的自說自話昭示了學衡派悲劇性的開始。
從《學衡》雜志創辦前就已經埋下學衡派的悲劇性伏筆,關于學衡派身份追尋悲劇性的淵源,嘗試從學衡派與白璧德人文主義的關系、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者的關系等角度分析。
學衡派同仁企圖從西方視域中為中國傳統舊文學的合理性尋找注腳同時,試圖將這種合理性運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新文學建設,這樣的意圖雖然是好的,可是學衡同人卻忽略了兩個重要方面的問題。其一:白璧德人文主義學說論證的背景性。白璧德是在工業革命經濟蓬勃發展,西方現代化快速發展背景下展開的。在吳宓的《白璧德之人文主義》一文中:“白璧德曰:‘今相鄰之各國各族,以及一國中各階級之間,各存好大喜功,互相嫉忌之心,更挾殺人之利器,則無論或遲或速,戰爭終不可避免。若輩犧牲人生萬事之價值,但求積累物質之富。既成,乃復自相殘殺,并所積聚者而毀滅之,吁,可憐哉!’”②膨脹的物欲撼動了人們的精神和道德,白璧德于是重新審視傳統文化與哲學,綜合東方與西方,追求個人道德修養的進步和人格的完善,“具博愛之心而能選擇并循規矩”。③很顯然比之西方,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截然不同,而學衡派將人文主義溫情的想象不加思考地移植到中國:
夫欲杜絕帝國主義之侵略。而免瓜分共管滅亡。只有提倡國家主義。改良百度。御誨圖強。而本尤在培植道德。樹立品格。使國人皆精勤奮發。聰明強毅。不為利欲所驅。不為瞽說狂潮所中。愛護先圣先賢所創立之精神教化。有共生死之決心。如是則不惟保國。且可進而謀救世。④
這種依靠少數精英分子自我道德完善的方式來救國不過是學衡派知識分子的想象而已,學衡派人士未能真正意識到理論移植過程中變化了的歷史環境背景,未能正確認識到自己的歷史命運和社會責任。
其二,白璧德人文主義學說論證方法的合理性。《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里意大利學者翁貝爾托·埃科的《他們尋找獨角獸》一文中,曾闡釋到:“兩種不同文化的相遇,由于相互間的差異,會產生文化間的沖撞。”⑤而實際上,兩種文化的相遇,是攜帶著兩種文化背景的人的相遇,于是就會出現帶著“背景書籍”的文化種群,帶著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預設與其他的文化相碰撞,異域文化永遠是作為某一審視的視角出現,作為某種致力于本土文化的方法而存在。帶著根據自己理解和想象的“背景書籍”去做出某種服從于先見觀念的解釋,其中自然有很多先入為主的異國他鄉不切實際的描述,會出現埃科所說的臨時性定義“錯誤認同”(False identification)。學衡派縱然尋找了人文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支撐,然而這些理論是為了預設好的結論而出現,這種自我循環的圈套和盲目的想象注定了身份追尋過程中的悲劇性。
另外,學衡派與新文學運動之間的論爭實際上是話語權的爭奪,想要通過話語權來確立自身的主體性。薩義德的《東方學》中提出了純粹知識和政治知識的區分:“關于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或華茲華斯(William Wordworth)的知識是非政治性知識,而關于當代中國和蘇聯的知識則是政治性的知識。”⑥薩義德審視東方的獨特視角對于看待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的批駁給出了一定啟示。在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中對新文化者進行四個方面的反擊: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彼等非創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在梅光迪的這些批評觀點固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籠統性,但是透過學衡派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定位可以看出,學衡派在自我身份認知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不同于新文化運動強烈的政治色彩和現實特色,學衡派將焦點放在純粹的文化學術,對現實與政治因素的考慮關涉相對較少。于是兩派交鋒的問題似乎不僅僅是舊文學合理性和新文學合法性這類問題如此簡單,這種話語權“是在與不同形式的權力進行不均衡交換過程中被創造出來并且存在于這一交換過程之中,其發展與演變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制于其與政治權力(比如殖民機構或帝國政府機構)、學術權力(比如語言學、比較解剖學或任何形式的現代政治這類起支配作用的學科)、道德權力(比如‘我們’做什么和‘他們’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們’一樣地理解這類觀念)之間的交換。”⑦這種話語權的復雜性是縱身于傳統文化中的學衡派所沒能認識到的,他們所批駁的新文學者這種在現實權力中博弈的激情正是學衡派本身所缺乏的。于是,梅光迪曾經給新文化運動設下的斷言“提倡方始,衰象畢露”一語成讖,似乎早早地變成了學衡派的墓志銘。
總體來看,學衡派的身份探尋是建立在其傳統文化與西學交鋒的過程中,與中國二十世紀初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系。20世紀初的中國面臨著西方權力的威脅,西方和東方之間是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與霸權關系同樣位移到文化方面。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傳統知識人亟需重新彌補文化上的自信心。這樣的身份追尋折射出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文化危機心態,以及力圖調和新舊文學、發揚傳統文學的擔當。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也反映出民族國家在面對身份困境中的掙扎。
同樣屬于在新舊文化中抉擇成長起來的同仁群體,學衡派選擇了與新文化運動者不同的道路,卻在文化多元的抉擇中品味出相似的無奈與困境。化用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論王國維之死中的一段話:“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愈甚。”面對新文化大潮的沖擊,懷有深刻危機感的學衡派通過取經于白碧德的新人文主義、與新文化運動派抗衡等方式力圖追尋自己的身份標識,然而這種囿于他者視域中的身份追尋最終將其導向困境,潛藏下悲劇命運的伏筆。從這個角度審視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可是窺視處于時代轉折點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和相似命運。
注解:
①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② 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吳宓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
③ 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吳宓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
④ 吳宓譯:《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譯者按),《學衡》第38期
⑤ 樂黛云,勒·比雄主編:《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⑥ [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北京三聯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⑦ [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北京三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李靜(1991-),女,漢族,文學碩士,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I206
A
1672-5832(2016)03-02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