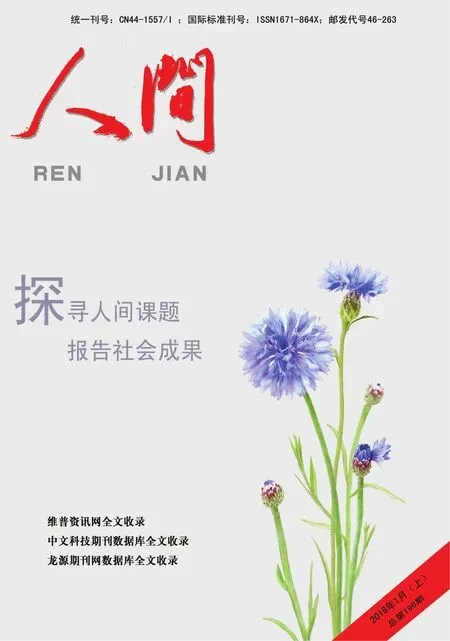“西學”之于王國維
王明輝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0000)
?
“西學”之于王國維
王明輝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0000)
摘要:王國維是國學巨子,他西學并學能“中學為體”,是“革命浪潮”中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捍衛(wèi)者,是個人“理念”的堅守者與殉道者,以其對學術的純粹和認真值得我們學習。
一、王國維與“西學”各派
王國維是我國近代享有國際盛譽的著名學者,近現(xiàn)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有關王國維的生卒事跡我無需啰嗦,我在想康有為、和陳獨秀等這些所謂“改良派”和“改革派”對于國學的研究要是有王國維的純粹和嚴謹,歷史或許會重新書寫。“識時務者為俊杰”,康有為、陳獨秀,“新青年”與“左翼”諸如此類者當屬“識時務者”。但他們是不是識歷史,有沒有站在高角度的學者心態(tài)去衡量中西文化,這些另當別論。西方列強的入侵,“救亡圖存”成為主旋律,為學術而學術變成為生存而學術,不管是“改革派”、“改良派”或“國粹派”還未深入研習和反思、相互交流,便以各自維護的立場登上了政治舞臺。“新青年”之與中共,“守古派”之與徐世昌,尤使對戰(zhàn)更為激烈,各不相讓。學術若以政治為依托和武器,學術自身勢必貶值。救亡心切的民國精英,西學的的目的不是為學問本身,而是以草草西學來求得救亡圖存的思想武器。而這種草草西學的“德、賽先生”,“馬列”以及它擁護的政治體系,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侵襲在當今看來是相當嚴重的。為此,守舊固有守舊的道理。
王國維是國學和西學的集大成者,縱觀東西,博覽古今的學者。他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美學等著論頗多,他的死和有關“殉清”說、“文化殉節(jié)”說,的確證實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和維護,但把王國維草草定義為守舊派,有失偏頗。相比其他“西學”各派而言,王國維的偉大在于為學術而學術。他的學說是更為純粹的融合了中西的文化。為此我們要將他的“境界”說,做以細談。
二、叔本華與王之“境界”說
叔本華哲學是在康德哲學和印度哲學、佛學相結合形成的。他認為意志的支配最終只能導致虛無和痛苦,以及藝術之美使人能從意志那里得到暫時的解脫。而王之思想:“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無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tài),苦痛是也。……一欲即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可以看出叔本華對王國維的影響很深,儒學是重生活且重群體利益的,是在生活的點滴中達到“仁”,以小見大,以通觀宇宙蒼生。叔本華的意志悲觀主義,沖擊了儒學,為國家為蒼生的入世欲求。也突出了近代個體情欲解放思潮所帶來的終極問題。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王國維一介儒學名士,自然的以“藝術”為慰藉良藥,取得暫時陶醉,并在陶醉中超然得道。所以“境界”說孕育而生。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將這三種“境界”理解為更高格局的立志,苦索求學和頓悟。單純的看待“境界”說,我們會覺知王的儒學思維方式和具有的積極進取意義。但這三種“境界”,用詞表達,格調卻是悲憫,沉郁的,為何?王國維最早接觸叔本華、康德是二十三歲,二十八歲通讀了叔本華等著作,《人間詞話》是其后刊于《國粹學報》的,并在其中提出“境界”說。所以“境界”說受叔本華哲學等西方哲學的影響是毋容置疑的。我們在回顧叔本華的哲學,盡管整體上是悲觀主義的意志學說,但里面也不乏樂觀積極的因素,而這因素便是藝術的作用與陶醉于藝術的美感。縱使它是短暫的,但不代表人們只能消極觀望。我認為,在王國維那里把這種對藝術墨守成規(guī)和消極觀望的星火,轉化為積極求索的曙光。歸根結底的看,是叔本華哲學沖擊了儒學,但王國維最終以儒的精髓融解了叔本華哲學。王國維把叔本華的“藝術之美”,轉化為“興觀群怨”的思維或甚是恍然頓悟。
三、“文化殉節(jié)”說與王國維之死
王國維正職清華國學教授,辭職且自溺與頤和園魚藻軒,一代大師巨子隕落。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后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這就是陳所持的“文化殉節(jié)”說,我基本上贊成。王國維一代國學巨子,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理解甚深,深知其中之奧妙,他雖然研究西學,融西學且不為西學所制。不像陳獨秀和“左翼”諸家那樣的極端,不像“守古派”那樣的頑固不化,也不像“調和派”做表面文章。總之傳統(tǒng)文脈在“新青年”、“五四”、“馬列”和共產主義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tài)下逐步斷裂。王國維是最后的國粹驕子,更是真才實學者和愛國者。
還有王國維的自溺,是不是像他所說“境界”中的已到達了第三層呢?我們先看第二層“境界”,王國維飽讀詩書,縱覽先賢,通曉歷史,融匯西學。從某種程度上他以冥思苦學達到功德圓滿了,我認為他達到了第二種“境界”。他的自溺是否是在他達到第二種“境界”后,破生死利害,有“大舍”之心,即所謂的第三種頓悟“境界”呢?若是由此境界,“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中暗含的埋怨之情當如何解釋?把他對“境界”追求和“文化殉節(jié)”聯(lián)系起來看其死因,似乎是成立的。
當今社會,在中國幾乎找不到王國維這樣的學術巨匠,能稱為大師的也是勉為其難,為何?我們不能歸罪與誰,歷史車輪不可倒轉。歷史的進程是盲目,隨機的還是理所當然的,還有待探究,但王國維給我們留下巨大的智慧,人格財富是毋容置疑的,他永遠是我們指引、建樹人生的楷模。
參考文獻:
[1]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李澤厚《華夏美學》
作者簡介:王明輝1896年生于甘肅省白銀市,男,漢族,甘肅省白銀市人,碩士研究生,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油畫(研究方向)。
中圖分類號:G65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1-0202-01
關鍵字:守古;西學;“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