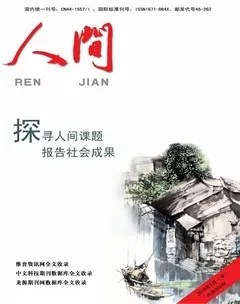對于兩種異質文學之間影響發生的思考
——以中國近現代文學開端為例
趙曉穎(天津開發區國際學校,天津 300457)
對于兩種異質文學之間影響發生的思考
——以中國近現代文學開端為例
趙曉穎
(天津開發區國際學校,天津300457)
中國現代文學的變化、文學淵源問題在現代文學研究中一直眾說紛紜。本文從兩種異質文學之間的影響發生出發,通過對近現代文學發生的內因和外因關系角度,進行思考和梳理,提出一些思考和看法。
近現代文學;異質文學;近現代文學開端
在馬克思的兩大歷史性偉大貢獻之一的唯物史觀中,有論及社會存在于社會意識的關系,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是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其中主要的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和生產方式。社會意識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應,指社會生活的精神方面。而社會意識的構成中的高級層次是指思想體系,它包括兩類,一類是屬于意識形態的思想體系,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學等大部分社會科學,是反映經濟基礎的,屬于思想上層建筑,為特定的經濟基礎服務。另一類則是屬于非意識形態的思想體系,包括自然科學、語言學等,與第一類相對,不反映經濟基礎。由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可以得知,文學,這個屬于意識形態類的高級層次的社會意識,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并反映經濟基礎的。因而我們可以說,文學,不是一個獨立發展起來的事物,也不是簡單的由個人或者某些人所決定的,它有決定其發生和發展的因素。
既然這樣,可以推知,在中國近現代文學發生的時期,中國是處于一個遭受外來入侵的情況之下,當國人發現自己較之入侵者是那樣的落后和弱小的時候,在向自身尋求力量和不得的時候,目光自然的便轉向了西方。雖然在這樣的過程中在起初是伴隨著西方文化入侵性質的,是不平等的,但這并不是最主要的使中國近現代文學向外轉的原因。我們最先注意到的當然不是文學和文化,而是與我們關系最近的軍事、經濟等給我們造成最大打擊的方面,隨之而引入的才是文學和思想文化等等。我們可以說,這樣伴有“闖入”和自覺“引入”眾多西方思想的過程,能夠那樣產生重大影響,非常關鍵的一個方面在我看來就是“需要”。我們需要在自身陷入困境的時候借助于先進的軍事、經濟等我們覺得那些可以幫助我們的東西,這當然包括思想文化在內,它們是這些我們當時所“需要”的東西的精神表現。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的發生時期,我們更是需要這樣的“新”的思想文化來與我們“封建傳統”文化來對抗,在那些倡導者的努力下,吸收有益于我們“新文化”的東西。擺脫舊思想的束縛,而使得國民覺醒,使得國家強大起來。
可以說文學在這樣的發展環境中是不得不,但又自然而然地呈現出對西方的依賴。或許可以直接一點來說,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其文化、文學上的影響是很難不占重要地位的,這其中要包含一個文化影響力和文化關注程度有關,當然作為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文學是一個國家文化、歷史等多方面最好的反應,因而我們在急于發展和變革的時候,就必然的會向先進的占主導地位的一方投去更多關注了。雖說對西方是多有依賴,但這樣的源自需要的“引入”也是在傳統限制的基礎上而進行的。從魯迅、胡適等人身上便可看出。至于之后的無所篩選的“引入”是因為缺乏清醒的認識而盲目所造成的。
因而,正是這種近現代的中國自身求新、求變而使得近現代文學呈現出了這樣的發展特點,在這樣的背景和環境中理解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能夠讓我們更深刻的理解其發生的原因和發展的軌跡。甚至于現在我們可以逐漸明顯的發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地位上升,世界影響力擴大的同時,中國文化、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也隨之在擴大。這樣的例子自古便有,經濟實力強盛繁榮的唐朝,雖有文化傳播的功勞,但各國的朝拜和對中國文化的渴求是相當強烈的。日本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學習和借鑒、之后對美國的轉向不都是很好的例子么。在蘇聯文學曾一度影響世界,但隨著蘇聯解體和當今研究對其的冷漠更是強烈對照。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生,不光是由“影響”這個外來的力量,更有其自身“引入”這個內在的力量共同作用而實現的,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因而要看到其發展的特殊環境、條件和目的,可以客觀的評價。中國近現代文學在短短的三十年內,獲得的成績是顯著的,也出現了頗有影響力的作家,但文學的社會價值的重視而使得過多政治力量的介入,難以自然的發展,相對而言成就當然也就少了很多。
在以前我們更多的提到“影響”,我們希望找到屬于自己本身“純凈”的文化、文學,渴望在某些方面占有主導地位,獲得某種優越感。這在諸多國家,法國、美國都曾有這樣的明顯的表現。比較文學中法國的影響研究、美國的平行研究便是出自各自文化、文學特點的考慮。其實,現在大家也是一直在追求這樣的一種優越感。不過,還是有一部分人是越來越提倡文化的“交流和對話”的,這樣便使得眾多參與者以一種平等的姿態,提供更多渠道的傳播和理解,而追求一種世界文化、文學的理想狀態。
就文學而言,借用對評論克萊齊奧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世界性的視野、人類的目光、普世的價值、全球化的倫理,是當代作家反映當代世界或對當代是做作出反應的一種‘品質’意義的要求”。這確實是“全球化”作家的特質,是諾貝爾獎所追求的目標。但具備這樣特質的作家在何種文化與文學環境下能夠產生呢,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寬容。
[1]魯迅:《文化偏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
[3]陳子平:《 “中國視角”與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
[4]程文超:《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現代性問題》,中山大學出版年社,2004.
I054
A
1671-864X(2016)05-0006-01
趙曉穎,現任職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際學校,語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