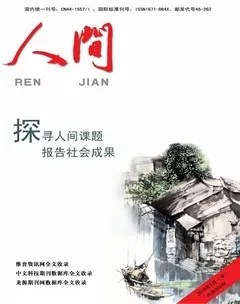“直訴”依賴現象的法文化探析
王冰清(武漢大學法學院 2013級法律史專業,湖北 武漢 430072)
“直訴”依賴現象的法文化探析
王冰清
(武漢大學法學院 2013級法律史專業,湖北 武漢430072)
當今中國社會信訪事件頻發,有人將之歸結為法制建設不健全,人民群眾信訪不“信”法。筆者認為,群眾信訪不“信”法現象,不能簡單的歸結為是法制建設的問題,這種現象與中國人千年沉積下來的訴求表達方式相關。從當前文獻記載來看,早至西周時期統治者就在常規的訴訟制度之外建立起一種非常規的可以直達天聽的制度,稱之為“肺石”。歷史連綿,直訴制度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直至清末改革直訴才在法律制度上暫時消弭。而此后當代信訪制度的建立以及群眾信訪不“信”法現象,與其說是制度模仿,不如說是傳統文化慣性帶來的結果。本文筆者將這種現象總結為,“直訴”依賴,其中既有統治者治國方略方面的依賴,也有群眾訴愿表達上的依賴,并試圖從法律文化的角度對這種現象進行分析。
直訴依賴;法律文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紛繁復雜,而其中法律文化的概念問題最有代表性的爭辯便是法律文化成果觀和法律文化規則觀。成果觀,把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作為文化進行定義,認為法律文化也就是法律思維、法學理論、法律制度及物質設施的創新成果之積累與匯集。而規則觀,則將文化總結為,是由一定的觀念系統所決定的行為規則。[1]這種將文化表達為行為規則的定義,使法律文化的進一步研究成為可能。規則觀學者進一步提出法律文化作為一種由觀念系統所決定的行為規則,其具有層次性和結構性,在不同的層面上決定著我們的行為選擇。[2]
二、歷史上的直訴
中國古代的直訴制度是法律規定的一項特殊訴訟制度,為了保證司法公正性以及最大限度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如果有案情重大和冤獄莫伸者,他們可以超出一般訴訟管轄和訴訟程序的范圍,打破審級的限制,直接向皇帝或欽差大人或者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申訴的一種司法制度。[3]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直訴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路鼓和肺石制度,所謂路鼓,《周禮?夏官?大仆》記載:“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邃令,聞鼓聲,則速逆御仆與御庶子”。所謂肺石,即《周禮?秋官?大司寇》中記載:“以肺石達于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在此之后,漢朝曾有上表制度,關于這一制度的經典案例為“緹縈上書”。晉朝武帝時期“路鼓”改稱“登聞鼓”,此后登聞鼓便成為歷代直訴制度的主要方式。唐朝的直訴制度發展較為完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國古直訴相關制度的最高水平,當時主要有五種方式,即登聞鼓、邀車駕、立肺石、上表和武則天時期增加的投匭狀。唐朝以后的直訴方式便沒有多大的變化,到了清朝,直訴制度已經發展到頂峰,限制也越來越嚴格。同時還需注意到另一個與直訴相伴而生的問題,即在設置了直訴的同時,統治者還設置了一套禁止越訴的禁令。這種準訴又進行限制的配套設計,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其制度設計的初衷和目的。當然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沒落和清末法制改革的推行,直訴制度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而新中國信訪制度的設立,似乎可以解釋為,直訴制度在某種意義上的復活。
三、直訴長存與法律文化
直訴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筆者以法律文化的規則觀為理論基礎,解析直訴作為一種法律文化現象為何能夠經久不衰。就“直訴”依賴現象,可以從不同主體的角度進行解析。
1.統治者的角度:治國方略上的依賴。
首先,直訴制度的長期存在是受中央集權和權力一元封建體制影響的。在中國古代皇權至上,皇帝掌握著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各方面的大權。在司法方面,皇帝當然是控制著最高的司法權,是最高的審判官,對其臣民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因而是最高權威,中國古代的直訴制度正是這種最高權威體現的一個方面。[4]在我國古代,皇帝親自參與審判的情況時常出現,皇帝參與審判的情形給直訴制度的出現和存在提供了實現的可能。直訴的存在,使得某些必須要依照審級限制逐級上訴而得不到公正裁決的案件,通過直接上訴于最高統治者有了獲得公正裁決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對于被統治者來說是一種生存的希望,甚至是救命的稻草,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使被統治者在遇到極端困境的時候能夠將理性維持到最后一刻。此外,由于是皇帝親自參與受理或裁決,一旦這些案件得到了公正的裁決,其影響力巨大也往往使同時期的其它類似案件也可能得到公正的處理。這種因皇帝的特殊權力而得以放大的表層制度利益,使百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受恩惠,而統治者又能通過這種制度傳揚其仁政愛民、以德治國的仁君形象。直訴制度之所以長期被各個時期的統治者所采用,除以上提到的因素之外,更該歸結于其深層次的原因,即這種制度設計能夠幫助實現維持社會穩定,鞏固和彰顯皇權的目的。
其次,中國古代直訴制度是為統治者提供實現民聲上達的途徑而設計的。中國歷史上比較英明的統治者一般都能認識到,民情能否上達是關系到國家安定與否的重要因素。中國古代司法的制度設計中并不缺乏上訴制度,而正規的上訴制度往往因為官員之間的官官相護,一手遮天而難以發揮效果。古代吏治也可稱為官員之治,這種百姓有可能直達天聽的制度設計,一定程度上威懾了官員的互相包庇以及貪污受賄的本能。此外,英明的統治者也確實依賴此制度設計以希望能夠獲悉民情民意,從而使那些有冤情而得不到伸張的人擁有一個獲得公正裁決的途徑,以盡量防止民眾積怨而影響社會穩定。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古代各朝對直訴制度都采取過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始終沒有哪一個朝代廢止這在很大一個程度上是由于統治者對此持有默許的態度,而這種默許當然也是從有利于維護其封建統治的角度出發的。
2.民眾角度:“青天”情結引發的“直訴”心理依賴。
人治抑或法治,兩千年前的儒、法兩家的爭論雖然以法家的暫時勝利為結果。但是最終成為統治方略的是“為政在人,得人政存,失人政亡”,人治的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這一結論和“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相結合,成了使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千年的政治經驗。以人治國,人便成為了治理國家的決定性因素,當官員個人道德素養成為國家治理優劣的關鍵時,被統治者在祈求獲得社會公平正義時自然就轉向尋求其認為道德高尚者的幫助。而被認為官員職位高低與道德素養成正相關關系的政治設計,同樣驅使百姓在遭遇社會不公時,向上尋求更高級別的處理和關注。這種相伴人治、德治而生的直訴傾向培育了百姓在困境下尋求解決問題之道的思維習慣。在這種自古以來的“青天”、“清官”情結的影響下,民眾寧愿放棄其他更為實際和經濟的冤案救濟方式而選擇直訴這條不尋常卻又有成功案例可尋的上訴之路。當然,清官情結的產生表明古代中國民眾政治力量的極度薄弱,百姓大眾時常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個人權利或權益無以保障,在此情景之下,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能有一位體恤民情和為民做主的清官出現,希望清官具有全知全能、明察秋毫的超凡能力,來為他們伸張正義。
3.“直訴”依賴的法律文化根源。
無論是大一統的政治理想還是鞏固中央集權的需要,古代中國社會穩定國家統一是歷代統治者的政治追求。因此,秩序是作為其最高的價值追求而存在的。為了實現這一價值追求,統治者對于直訴制度可謂不離不棄。始終將其作為緩和社會矛盾的方式之一納入制度設計之中。然而,傳統中國文化中存在的“告御狀”、“找青天”說明了民眾對于直訴這種訴求表達方式的依賴。往往在民眾們認為告狀無門或者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冤屈時,便不再信任常規的訴訟途徑,以纏訟、自殘等極端行為方式為內容的直訴之路成了民眾的希望和救命稻草。而在當代,人民群眾更喜歡用信訪的方式向統治者,執政者表達自己的意愿,反映自己的冤情。就是到了新時期新階段人民群眾的這種觀念依然存在。隨21世紀市場經濟在我國的確立,改革向縱深發展,許多新的問題和矛盾的出現,現實與意愿的沖突必然存在。信訪案件廣泛存在,亦時常出現在新聞中,除了說明人民群眾對黨中央,國務院的信任,同時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基層管理者的不滿。[5]
以上這些在古往今來的社會生活中以不同卻相似的方式而存在的現象,筆者將之統稱為“直訴”依賴。而這種現象用法律文化結構理論可以將其長期存在的原因進行有效說明。法律文化的結構具有層次性,法律文化由表層結構、中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組成。[2]本文中所提出的這種法律文化現象,其表層結構表現為在歷史上以各種形式存在的直訴制度。中層結構,表現為統治者以及民眾對這種制度有效性的認同,統治者認為這一制度能夠實現民意上達的需求,而百姓信賴這一制度能給他帶來公平正義。深層結構,則是中央集權,權利一元的實質,決定了統治者要采取一切有利于維護其統治的方式。而百姓也同樣信仰和認同這種中央集權及權力一元,在遭遇困境時趨向于信賴權威能夠帶來公平正義。深層內核決定了統治者選擇適用這種治國策略,被統治者選擇這種訴愿表達方式,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其受同一種文化內核的預決。
四、結論
文化是一種由觀念系統所決定的行為規則,以文化規則觀來定義法律文化使解釋紛繁復雜的法律文化現象成為可能。每一種被認為合理的現象背后都有其存在的自身邏輯。無論是民眾信訪不“信”法還是其他不利于法治建設發展的法律文化現象,都有待于我們去尋找到其根源。順藤才能更快的摸到瓜,溯源才能更好的做出符合社會預期的制度設計。信訪制度本身并不是不好,但是引導群眾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利用,無疑是政府部門應該做的工作之一。此外,法律的信仰不是刻在大理石上,而是刻在公民民心中。由信訪到信法,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注釋:
[1]陳曉楓:《法律文化的概念:成果觀與規則觀辯》,《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2]陳曉楓:《法律文化:顯型、隱型及結構析論》,《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3]李玉華:《我國古代的直訴制度及其對當今社會的影響》,《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1期。
[4]王茂娟:《中國古代直訴制度研究》,山東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
[5]張春熙:《中國信訪制度的歷史及現狀分析》,《政治與法律》,《新西部》,2009年第22期。
D920.4
A
1671-864X(2016)05-0046-02
王冰清,1988年12月,籍貫:江西上饒,武漢大學法學院,專業:2013級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