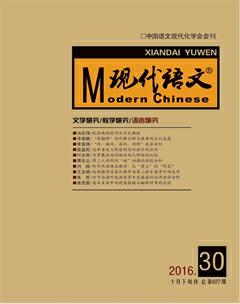簡論漢賦創作在主題上對后世小說的影響
○宋 蕓 蔡庸禮
?
簡論漢賦創作在主題上對后世小說的影響
○宋 蕓 蔡庸禮
摘 要:文章從事物的發展、演變及其特征方面入手,探討漢賦與小說之間的微妙關系及漢賦對小說發展的影響。文章簡要論述了漢賦和小說的地位,以及它們在主題上的相似之處。
關鍵詞:漢賦 小說 主題
一、漢賦與小說的地位比較
清代文人焦循在《易余龠錄》卷十五中說道:“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漢代是賦體文學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后世文學在賦體文學創作上不能超越的時期。辭賦的創作,已經是漢代文學的標簽。兩漢時期的政治背景是賦體文學興盛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描繪了漢賦在西漢的盛況:“至于武宣之世……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1]可見,賦體文學的創作在西漢時期已經達到與“三代同風”的狀態。
魯迅先生說:“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莫出于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偽作,至宋明尚不絕。文人好逞狡獪,或欲夸示導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晉以后人之托漢,亦猶漢人之依托黃帝伊尹亦。此群書中,有稱東方朔班固撰者各二,郭憲劉歆撰者各一,大抵荒外之事則云東方朔郭憲,關涉漢事則云劉歆班固,而大旨不離乎言神仙。”[2]與魯迅先生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王瑤先生,他說:“漢人所謂小說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3]由此觀之,漢賦和小說不能算是同一時代的產物,也不能算是同一階層的產物。創作目的和作品功用也不同,那為何要將其兩者聯系起來做比較呢?
其實漢賦與小說之間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從文體上說明中國文學之演變趨勢,同時說明無論何種文體都有幾種共同的傾向,即是(一)自由化,(二)語體化。而(三)散文化又是這二化的關鍵。”[4]我們都知道漢代大賦的創作是由枚乘所作的《七發》作為其開端的,同時期這類文體創作的代表作家還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等。鐘嶸在《詩品·總論》中提到:“自王(褒)、揚(雄)、枚(乘)、馬(司馬相如)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見,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失。”其實這已經說明了漢賦的特點,就是在極力描寫各類事物,長篇巨制,氣象壯闊,文辭富麗,好用典故,多用難字,表現出一種典雅堂皇、肅穆凝重的風格,在章法上則多采用主客問答的形式,句式上參差錯落,如此一來,詩的風氣便開始缺失了。
“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概念,最早是由東漢的桓譚、班固提出的。“袖中有短書,愿寄雙飛燕。(注: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5]“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6]從上兩段文字來看,都能體現郭紹虞先生說的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趨勢。當賦缺失了詩的風氣,其實它便開始走向自由化和散文化的狀態,而從小說的發展來看,明清小說是作為古代小說興盛和成熟的時期,它也體現了文學的語體化和散文化的特點。
之前已經闡述了辭賦作為漢代文學的標簽,在兩漢時期辭賦創作相當活躍。而小說的創作在兩漢也比較活躍,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錄“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7]漢代文學家雖然創作出了很多的作品,而且作品也相當受歡迎,但是作為創作者,他們的地位卻并不高。兩漢時期,賦家被視同倡優,賦作被一些統治者視為娛情怡性的享受品。賦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一種技藝。《漢書·枚乘(附枚皋傳)》:“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優,為賦頌,好嫚戲(褻狎戲謔)……皋為賦善于朔(東方朔)也。……(指漢武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毀謗)東方朔,又自詆娸。”[8]而小說的地位就更不用說了,它們正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產物,它們是野史稗官或是街巷黎民口耳相傳的產物,不用經過什么特別的訓練,也不用作為進爵封侯的橋梁,它的功能只停留在娛樂大眾的層面上,所以很多文學史家并沒有將小說列入正統文學行列,當然也不會那么重視。
二、主題方面的“諷”的意義
有學者已經看到了漢賦的主題在于“諷”,“漢賦把反對最高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作為自己的創作主題——幾乎所有賦家都圍繞這個主題做文,是有現實意義的。”[9]小說則“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勝,尤其在人情小說中。”[10]
雖然漢賦中的“諷”多帶有“諷諫”的含義,所以諷諫的對象自然是最高統治者,而小說中的“諷”多帶有“諷刺”的意義,但其諷刺的對象就不單指向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有指向官僚縉紳或是社會現實封建禮教,等等。兩者在側重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其重點也是在“諷”這個層面上。且看古籍中記錄漢賦“諷”之意義的章句: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11]
“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于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12]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與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13]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侍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14]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盬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需,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15]
“(下)……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16]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髠,優孟之徒,非法度之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焉。”[17]
《后漢書》本傳所說張衡《二京賦》的動機:“永元(漢和帝年號,公元89-105年)中,(衡)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五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因以諷諫。”[18]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見于漢賦作家的傳記中。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明清時期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使得此時的帶有諷刺意味的文學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功用。如清代小說《聊齋志異》,從它的內容上來判斷,它是屬于傳統的志怪小說。蒲松齡筆下的那些花鬼狐妖雖然是異類,但是她們卻比有些衣冠楚楚的人要正直善良得多。在一個個故事中,有對封建社會的黑暗政治和帝王官紳的無情揭露與諷刺,有對科舉制度的強烈控訴與諷刺,也有對封建婚姻的辛辣批判和諷刺,等等。且看《聊齋志異》中的《司文郎》,這則故事是對科舉制度的諷刺:
因命歸取文,遇馀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癥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余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馀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19]
不采取科學的方法選取有用之才,卻用焚燒作品以嗅氣味來判斷文章的優劣,可笑之極。這是小說中諷刺社會現狀的經典情節。
同時代小說《儒林外史》,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魯迅先生曾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有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20]《儒林外史》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儒生的形象,辛辣地諷刺了科舉制度和社會現狀。其中迂腐呆板的范進,中舉后的那一連串表現,是諷刺中的極致顯現。
綜合上述文字,漢賦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也在影響著后世文學,古代小說是通過對人物的塑造,來完成作者意圖的。在上述的例子中,人物的表現都能反映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作者想要傳達出來,就是對現實的不滿,然后對其進行諷刺批判。可見,漢賦和小說在歷史地位上、創作主題上都有相似之處。從中也看得出來,賦對于小說的創作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本文為校級課題“漢賦與小說的關系”成果,項目編號為[ASC15-12]。)
注釋:
[1][漢]班固:《兩都賦序》,[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第22頁。
[2]魯迅:《今所見漢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第15頁。
[3]王瑤:《小說與方術》,《中國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8頁。
[4]郭紹虞:《試從文體的演變說明中國文學之演變趨勢》,《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9,30頁。
[5][漢]李陵:《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第444頁。
[6][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1745頁。
[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1745頁。
[8][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2366頁。
[9]龔克昌:《中國辭賦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3頁。
[10]魯迅:《清之諷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第137頁。
[11][漢]班固:《兩都賦序》,[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第21頁。
[12][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3002頁。
[13][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第2999頁。
[1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3522頁。
[1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3535頁。
[16][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3557頁。
[1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版,第3575頁。
[18][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5月版,第1897頁。
[19][清]蒲松齡,《司文郎》,《聊齋志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1頁。
[20]魯迅:《清之諷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第137頁。
參考文獻:
[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6][清]紀昀等.文津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清]劉熙載撰.藝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阮忠.漢賦藝術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9]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A].戲曲論文集[C].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
[10]魯迅.今所見漢人小說[A].中國小說史略[C].北京:中華書局,2010.
[11]錢鐘書.管錐篇[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2]龔克昌.中國辭賦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
(宋蕓,蔡庸禮 四川阿壩 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637002)